
楊雪霏,父母親所賜的名字,取自《詩經》:「今我來思,雨雪霏霏」。
7歲意外接觸結他而愛上,不知多少個雨雪霏霏的北京嚴冬,她穿着三層毛衣外加羽絨褸,蜷縮着苦練結他,小指頭僵硬如冰棒,在鋼絲上游動。
「第一」明明讓人驕傲,她是中國古典結他第一人,少數蜚聲國際的女結他手,這條演奏家之路卻一直踽踽獨行。如東坡先生所言「萬人如海一身藏」,她不只是隱世小眾,而是孤獨。10歲決定以彈結他作為職業,旁人認為匪夷所思,更遑論古典結他,她冒着沒老師、沒工作、沒文憑的「三無」風險下,反一場不能逆轉的叛。
「我是對抗着父母進音樂學院的,記得每次交學費,家裏的氣氛都非常緊張。但最難捱還是周圍的老師、同學都不了解我的樂器,甚至看不起我的樂器。他們覺得,彈結他能進音樂廳嗎?甚至有人會說你還灌錄了唱碟,結他能錄唱碟嗎?」22歲她就灌錄了第一張CD,談昔日青春的熱病,楊雪霏一臉無奈又無悔。

結他各有名字 摟抱如親人
世態人情,可作書看。
她的故事,也像一首抑揚頓挫的敍事曲。
雪霏來港,小島也煙雨淒迷,惹人愁懷。
紅裙一襲的她迎來,步履輕快洋溢着北方人的率性,說話也快。甫坐下,她就顯得不自在,直至抓起擱在一旁的結他Greg Smallman,抱着結他如抱着親人,這是她認為最安全的姿勢。她的十支古典結他各有名字,傳遞着每位結他工匠有質感的性情。1995年,18歲的她就獲英國著名結他手John Williams送她另一支珍藏Smallman。連結他套她都賜予小名,例如一隻黃色的叫「檸檬」,另一隻新做的叫「香檳」。
訪談開始前,她急不及待彈起伴奏,是抑揚頓挫的《彝族舞曲》,這曲邰正宵多年前改編成流行曲《九百九十九朵玫瑰》,現場聽她用西方結他奏出古箏的味道,時而細膩如繡花,時而豪邁似奔馬。
「結他對於我像伴侶的感覺,以前有人問我結他是你小孩嗎?是武器嗎?我說絕對不是,怎能會是武器呢?它是我的伴侶,它跟其他樂器不同,因為在演奏時,你需要用身體去抱着它,用手指直接觸彈它,感覺很親密。」楊雪霏認真道。我懷疑自己是否應用「他或她」來稱呼其手上寶貝。西班牙文萬物都有性別,結他稱為「La guitarra」,是女性。「哈哈,結他葫蘆形曲線不是很女性化嗎?」楊雪霏笑說。
「這支結他2003年出生,今年13歲了,是我現場演出最常用的。」近距離不難發現楊雪霏這結他花痕纍纍。「我是太肉緊了。」每條愛的花痕都是回憶,她猶豫是否要打磨掉這些點滴曾經。
雨後滿地積水,攝影師請楊雪霏到酒店露天的竹林拍照,沒有半點架子的她索性脫下高跟鞋,赤腳示範輕功水上飄,任由裙襬沾濕冷得發抖,面無懼色。請她演奏Sergio Assad的一曲《Farewell》時,伊人堅持上房換上黑長裙。「我覺得這樣比較尊重。」此曲是作者寫給亡妻的道別曲,奏出一種遺世孤本的悲情,如泣如訴。
心思細密如塵、不拘小節又具同理心,就是楊雪霏。所以說,成功失敗都有原因,世界沒甚麼是無緣無故。
楊雪霏笑說,未出國前,她是個孤獨精,結他是她唯一朋友,自己在朋輩中是怪胎;出國後,她嫌自己太平凡。
「一個亞洲人演奏西方音樂而在國際得到肯定,是一件很困難的事情。」楊雪霏卻相信是結他選了她,命運安排。「如果不是當初手風琴班滿額,如果不是小學老師喜歡結他而成立結他小組……我已經無法想像生命裏沒有音樂有多枯燥,如果已經沒有如果了。」
記得最難忘一次,90多歲的西班牙失明音樂大師Joaquin Rodrigo來聽楊雪霏的演出,就在她奏出大師一首名曲後,全場震懾,掌聲如雷。
Rodrigo由女兒摻扶往後台,當知道奏曲人是位14歲的中國女孩,他無限驚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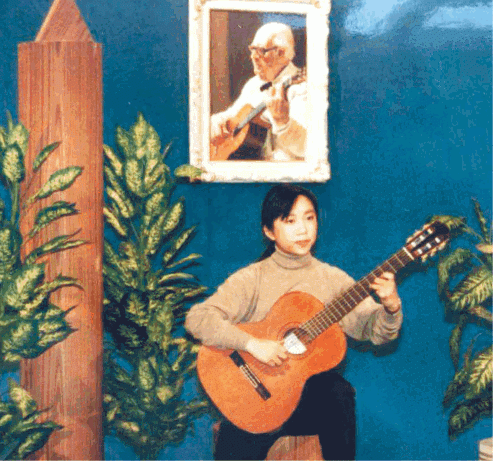


巴西不只森巴舞
2000年6月楊雪霏成為中國中央音樂學院第一個取得學士學位的結他本科畢業生,之後她負笈英國皇家音樂學院,跟幾個音樂家租一個房子,人家寄一百封信給音樂公司,她在倫敦一次演出就被看中,一星期後和百代唱片(EMI)簽約,後來又被英國古典音樂電台Classic FM評為「時代最傑出的一百位古典音樂家之一」。她把外界認為僅作街頭或酒館伴奏和助興的結他,周遊列國帶到最堂皇的世界級音樂廳,原不理解她的父母終於引她為傲,她形容自己很幸運。
2006年出道,楊雪霏推出第一張專輯《Romance de Amor》,奏大路的結他作品,第二張專輯《40 Degrees North》,以北緯40度貫穿北京與墨西哥,來個中西crossover。之後每張專輯她都希望重新編排,而非老調重彈,更會親自撰寫隨CD附送的唱片導賞文章。
從此,楊雪霏不再孤獨,演奏成為了她的日常,其餘時間她享受在英倫近郊的小屋外草地曬太陽,一年只回國兩三次看望父母。除了表演和在大師班分享經驗,楊雪霏更樂意透過實驗尋求更多可能性,例如以古典結他彈奏中樂《漁舟唱晚》、與英國男高音Ian Bostridge合作演出藝術歌曲、以古典結他彈奏流行曲,早前參與陳奕迅演唱會與郎朗同台,今年底她更會與香港管弦樂團合作,近期楊雪霏更與環球唱片合作推出新專輯《多彩巴西》(Colours of Brazil),讓大眾看到這奧運之城的古典音樂面貌。
「其實巴西不只有強烈節奏的森巴舞,巴西音樂與古典結他向來關係密切。」楊雪霏侃侃而談,談及寫下《巴西流行組曲》的巴西偉大作曲家Heitor Villa-Lobos、把森巴和爵士完美融合的裘賓(Antonio Carlos Jobim),他為戲劇《狂歡節的奧費羅》作曲後揚名國際電影界。
楊雪霏還透露,13歲童年時就彈奏第一首巴西音樂,來自南美的夫妻二部合奏的一曲《鐘聲》(Sons de Carrilhoes),生動的旋律吸引她。新專輯中亦有收錄此曲,原本的二重奏,由楊雪霏一人分飾兩角,懷荳蔻年華的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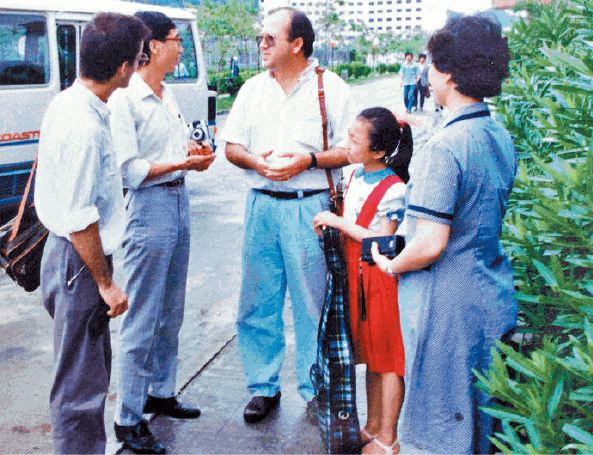
未到頂峯 彈不好就會退下來
生於1977年,明年便步入不惑之年的楊雪霏,絲毫沒有抗拒變「中女」的忸怩,甚至頗期待。「你會願意回到18歲或23歲嗎?應該很多人跟我一樣不願意,我信人生新一章在40歲開始。隨着年齡增長你會更清楚自己愛甚麼厭甚麼,你就不會浪費時間在無謂事上,我渴求中年這種成熟睿智。」
「很多人問我女與男演奏家有何分別?我可以告訴你體力是有分別,結婚生孩子後更困難維繫事業。外出演出真的很累,又要面對時差和思鄉病,郎朗就沒受時差之苦。」談到女演奏家之苦,楊雪霏正色道。
指顧倏忽,回望過去楊雪霏很理解當年父母阻止她追夢的心情。「內地家長很瘋狂,學生考上音樂學校,父母會放棄工作,在學校附近租個小房子做打掃工作,但我父母卻不是。父母都是教師,他們原安排好我入名校,我堅持要讀音樂學校,畢業後,單位會給你安排工作,入樂團不愁出路,但我偏偏選異類的結他專業,畢業就是失業。」以前要走大路,不過,時移世易,如今選偏鋒樂器卻成了坊間家長的另類策略,有家長更迫繁忙兒童自小學習多種樂器,最好懷胎時已懂得特異功能,她並不認同。
「你13歲長這高度和20歲長這高度,最後其實是一樣的。西方很多人沒有失去童年,他們反而成為真正音樂家。內地和香港在內的小孩很早表現便很突出,因為是逼出來的,只是一個假象,他以後不一定能真正成家。」楊雪霏告誡各一廂情願的怪獸家長「態度決定高度」,種瓜得瓜。「你要名要利,爭取到的就是名利,不會得到快樂,惟有出於熱愛,音樂也好嗜好也好,才會令你的孩子產生無敵的幸福感。」
像楊雪霏,年輕對音樂的熱情像天花,是青春的熱病,無藥可救。她甘願活在古典世界,追求鏗鏘頓挫、已入化境的琴音,樂與巴哈、柴可夫斯基等神交。
「應該來說,我覺得自己還未到頂峯,也估計不到是甚麼歲數。我只知道如果有一天我不能彈得夠好,就是我選擇退休的時候。」楊雪霏說話,從沒有國際巨星般的鋒芒瀉地,眉宇間還流露一種沉澱的實在感。
訪問完畢,我打着傘走在大街上,《Farewell》一曲不斷縈迴腦海,還有雪霏在結他線間游走的纖秀手指,像此刻迷濛雨粉飛快滑流,淅瀝淅瀝……
記者:鄭天儀 攝影:潘志恆
(部份圖片由被訪者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