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紅二代太子黨當中,楊紹明是個異類。他是已故新中國第四任國家主席楊尚昆二公子,沒從政或從商的興致,12歲孭起相機,一孭就六十多年,誓要影相影到入棺材。
對他而言,按下快門「咔嚓」一聲,比演奏廳天籟之音更悅耳。「其實我的志願是當文學家唄。」74歲的老人展露返老還童式嬌嗔。父親當年見楊紹明興趣廣泛,送他一部相機,從此改寫他一生。
1942年生於延安,北京大學讀歷史,文革後當上新華社攝影記者。因為近水樓台加身份特殊,他不用洪荒之力就能抓拍中共領袖的非常時刻,毛澤東游泳後赤腳和農民攀談、周恩來穿着水泡學游泳、鄧小平叼着煙打橋牌、朱鎔基與孫女爭玩公仔,都是一般攝影師求之不得的神秘瞬間。他口中如隔籬鄰舍的「毛伯伯、鄧伯伯」,統統是我們在歷史書或電視上所見的2D人物。
楊紹明不喜歡別人稱他「鄧小平御用攝影師」,因這頂高帽太封建。不過,他的確曾經在鄧小平身邊12年,更與毛澤東的女兒李訥由細玩到大,父親和叔伯輩都叫這位主席的二公子做「小二,小二」。
小二拿着相機登堂入室,領袖們沒太大戒心,展露最縱容、不為人所見的人性瞬間。「領導們知道我懂攝影,於是鄧家、周家等有家庭聚會都會請我去。」鄧小平晚年身體情況足以左右股市,有人說笑要巴結楊紹明,以便得到最新資訊在股海撈一筆。他的《退下來的鄧小平》便於1987年獲得荷蘭世界新聞攝影大獎(WPP),成為中國「零的突破」。
「他兩腿蹬在凳子上看報紙,退休老人基本上就是這個模樣。旁邊是他最喜歡的男孫鄧卓棣,嚷着要跟爺爺玩,嫲嫲跟他講故事來引開他,現在這孩子在廣西省有公職。起居室是鄧伯伯最能放鬆的地方,反映他很多生活細節,例如地上還有痰盂表示他仍抽煙。」楊紹明莞爾一笑,飛越時空來解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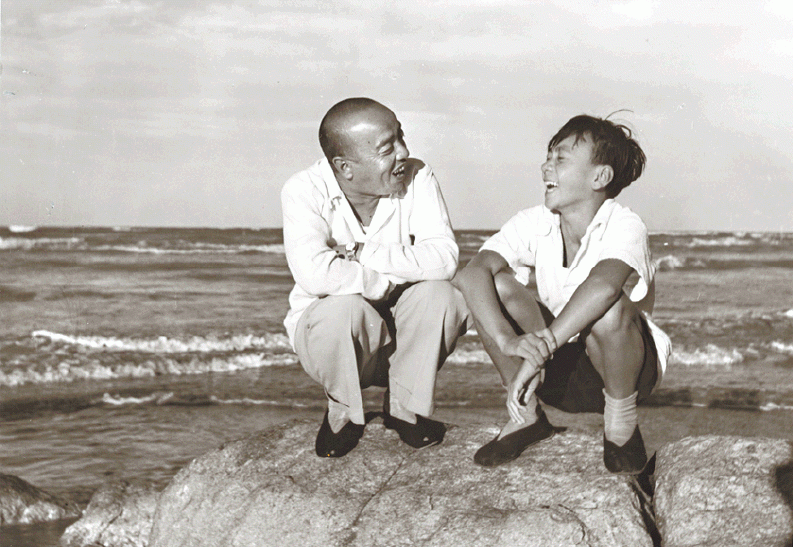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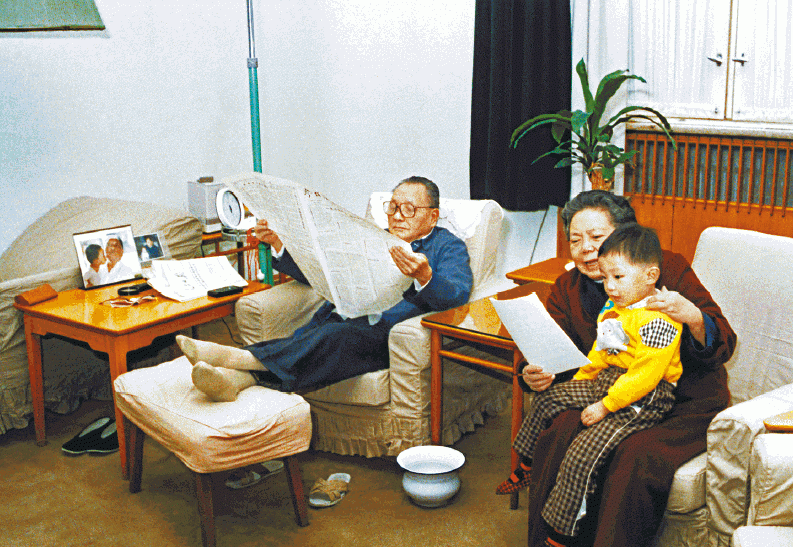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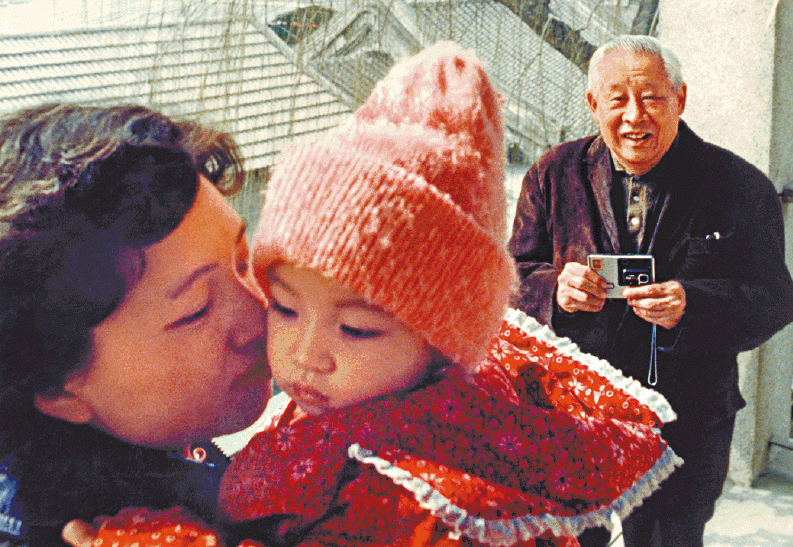
鐵面朱鎔基 逗孫為樂爭毛公仔
平時鐵面嚴肅的前國務院總理朱鎔基反差更大,一張他坐在小板凳與孫子爭毛公仔的照片,萌得有點過份。「大家很服氣他都叫他朱老闆,我拍過他打電話和開會,都是一臉緊張嚴肅的。但在他家裏的花園,他自己端了小板凳來,一邊曬太陽,一邊逗孫女,他說給姥爺,孫女撒嬌說不給不給不給,這就是生活的幽默。」這些經典作品,正在今屆香港國際攝影節重點展覽「千戶」中展出至九月初,楊紹明特意從北京來港,這個他熟悉又陌生的城市。
「其實我早就拍過香港,在1997年中英兩國政權交接之時,我拍港英政府最後三天,加上回歸後新的特區最初的三天,出版過《香港六天》攝影集。」楊紹明樣貌有七成像成龍,尤其那撮吹得妥貼烏黑的動L髮型。可能是藝術家氣質深入骨髓,古稀老人仍注重儀表,坐梳化拍訪問照時,雙腿平放好還是擱起,他會問助手意見。「我想,喜歡藝術的人都看來較年輕。」問養生秘方他興奮地說,他一點不像古稀的人。
楊紹明是最早得到國際攝影大獎的中國攝影師,得獎自然興奮,但談起這獎項他反而更記得領獎之旅最大的收穫,是得見偶像一面。「得到中國駐法國大使的幫助,我跟偶像著名攝影師布列松(Henri Cartier-Bresson)碰了面,布列松是個性格有怪癖的人,他看不中的事他不一定會接受,我很崇拜他,很想聽他的『決定性瞬間』理論,結果他給我私人上了一課,他和我也很高興。」替名人和普通人拍照,有甚麼不同?「其實區別不大,每個人有每個人的人性,年輕的時候人總會這樣,你崇拜誰肯定喜歡拍誰。不過,拍熟悉的人與陌生人就不一樣,所以盡可能我會跟被訪對象聊聊天才對焦。」
然後,他跟我談到經典照片《憤怒的邱吉爾》,那是攝影師Yousuf Karsh的成名作。攝影師覺得作為戰時首相邱吉爾未免太紳士太慈祥,不足以威懾敵膽,就搶了他叼在口中的雪茄,邱吉爾覺得被侵犯就優雅蕩盡,怒髮衝冠,記者按動快門,誕生了傳世照片,反映他與希特勒等法西斯決戰的決心。「這太戲劇性了,我告訴你在中國、東方國度,這方法行不通的。」楊紹明苦口婆心道。
攝影講求傳神攝髓,除了全家福他拍攝從不擺拍,那是周恩來教他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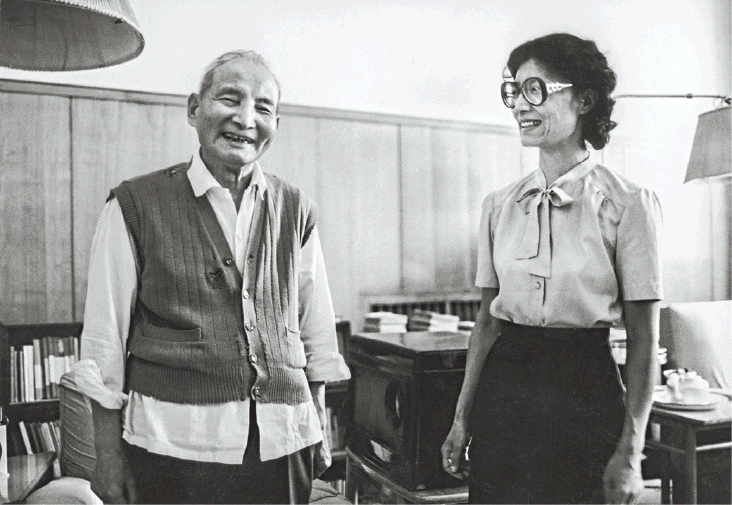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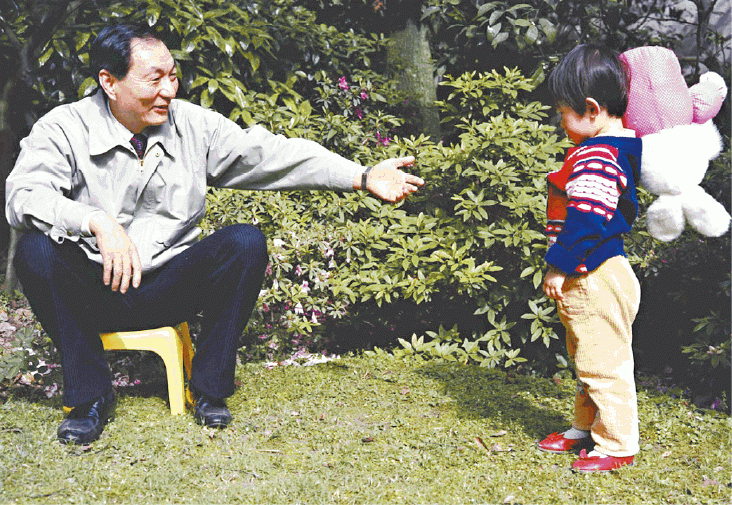
緊守周恩來教訓 不複製新聞
楊紹明憶述,當年周恩來在廣州會見外國元首,雙方友好握手。過後,新華社記者要求二人再握一次手作發新聞稿用,但周恩來語氣強硬的說:新聞是不能複製的,拒絕了請求。他牢記自己是新聞記者,肩負記錄歷史的責任。
「你要保持被拍對象的原樣,就不要驚動他。」
要躲起來嗎?我說笑。
楊紹明正色道:「不是躲起來,是等待、觀察、選擇、決定、抓住。」17歲他就洞悉這抓拍秘技,拍下13位領導人各有神態的《領袖們》。1963年,北戴河大雨過後,天邊出現一道長長的彩虹。楊紹明見毛主席正在沙灘上休息,他等待、觀察,見毛主席不苟言笑就靈機一動說:「毛伯伯,請你輕鬆一點。」毛主席說:「我很輕鬆啊!」此時,他按下快門,將毛主席與彩虹、大海一併定格。
提起毛澤東,就觸動楊紹明勾起文革的回憶,讓他沉浸在如潮的思緒中。「我在文革以前替毛主席拍了許多照片,文革時一抄家全沒有了。造反派無孔不入 ,他們是搶的,好照片都給拿走了,然後抓幾張說:『你拍亂七八糟的東西!』其實我沒有拍甚麼不好的東西。」當年,他除了部份收藏的郵票有藏起來,其他都被抄走了。
在文革的動亂歲月裏,楊家是首當其衝的批鬥對象。楊尚昆監禁達12年之久,後被平反,楊尚昆六妹楊尚朋被迫害致死。楊紹明記得,13年後家族團圓那天,他替父母在竹林拍了張合照,他永遠記得快門清脆的聲音。
開心與痛苦的記憶,都會鑲在照片裏,緊扣記憶。楊紹明家中放了一幀照片,從來沒有換過,就如牆釘子牢牢與家同在,那是由他操刀,拍父母親的一張合照。「我拍文革時他們如何受難,最苦的時候,我爸爸坐此,我媽媽坐在此,後面掛了一張魯迅的照片。都說魯迅的骨頭是最硬的,他沒有絲毫的奴顏和媚骨,這照片留到現在,我覺得最有意義。」楊紹明回北京後,就傳給我這張重要的照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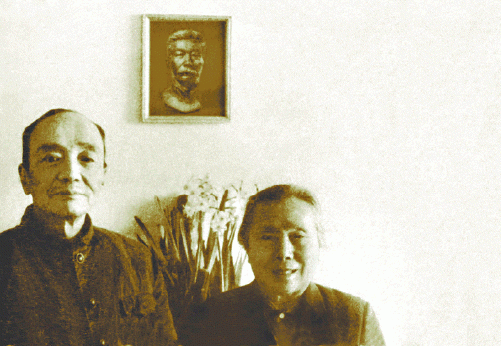
當年,有傳楊紹明因為受父親去世打擊而要進出精神病院,當下他再次澄清。「亂講!說我發瘋?不是這樣。我父親去世以後我是非常悲痛,因為我媽媽也受了許多冤屈,她走了後有父親還好,日子很充實,但是我父親一走,我們便感到雙親故去,世態炎涼,那時候情緒比較低落。」
鏡頭裏的父親,很多都是楊紹明突擊抓拍的,「因為我靠近他,無論在何種狀態下,我都可以抓得住他內心反映在臉龐上的個性瞬間。」
天安門記憶 不日開封
「在你心目中,楊尚昆是怎樣的一位父親?」
「他是一個好父親,培養我成為一個理想主義者,從小就要有理想。」
楊紹明抓抓動L頭說,年紀大了,他更喜歡拍老北京的街道,也喜歡拍傳統的生活方式,也拍過香港的七一遊行。「農民工我拍,清潔工人也拍,也拍當代的生活,地鐵的人。」
「拍到我不能拍,甚至我的生命已經停止以前,我都要拍。」縱然已進入半退休狀態,但楊紹明強調不會放下相機。
據說1989年六四期間,楊紹明在前線拍到無數血淋淋的天安門照片,對此他並不否認。「作為新華社攝影記者,這是很合情理的事,後來這些相片都給領導招供了,不由我保留。」
「一張不留?」
「一張不留。」
「那對於這段歷史你有甚麼想說?」我單刀直入。
「我想,現在還不是時候。」自稱「六四」見證人的楊紹明語帶感慨地說。
有一天,記憶總會開封。
記者:鄭天儀
攝影:梁志永、鄧鴻欣

香港國際攝影節「千戶」展覽
日期:即日至9月4日
時間:10:00am-8:00pm
地點:鰂魚涌太古坊康和大廈一樓ArtisTree
生日密碼
楊尚昆與楊紹明父子是同月同日生?這個流傳良久的說法,終於得到楊紹明親身解碼。
「當時鬧革命父親到外國留學去,人家問他出生日期他一時忘記了,脫口說出5月25日,那是我的出生日期,反映革命戰爭年代大家有多緊張。自此,他真的忘了自己的生日,很長時間我們父子索性同一日慶生。」楊紹明笑着解釋。
直到這位新中國第四任國家主席退下來,楊尚昆1995年開始撰寫回憶錄,找來歷史專家考證,終於確認他生於1907年8月3日, 農曆六月二十五日 ,估計因相差一個數字,故當年他錯把次子生日當成是自己生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