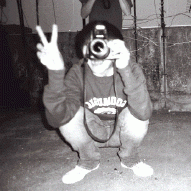「十八種香港」首站伊館已完結一個禮拜,事後陸續飛來各界觀後感與文章,「受寵若驚」四字已不足以形容我的受寵若驚。本菇從來並非容易飄飄然的人,越被稱讚越會對自己嚴格謹慎。這次得猛人如李怡叔、蔣芸姐、黎則奮、鄧小宇特地寫下評論,正好警惕自己更加把勁,別辜負各位厚愛。
回顧這次籌備直到禮成,就如畢明所說,是真正的粒粒皆辛苦。單是找場地已煩惱了好幾個月,想要的不批能訂的又不適合,怎料突然天降一個伊館八天檔期。因是政府場地,申請時心裏先打定輸數,竟又神奇通過了,哈。
然後是組成幕後團隊。因各種財政的不明朗,只能硬着頭皮逐一拜託好友幫忙;財務主管、美術總監、創作總監、舞台、燈光、音響、樂隊以致後台場務,無一不是親自致電,友情卡一一碌爆。事後有朋友驚嘆我們的齊心一致,這個當然。願意加入的每一位,都不只是單單做一個job,成為一分子首要條件是有共同理念,又不會斤斤計較的義氣仔女。
第一次開會,在座的都清楚意識到何韻詩在歌手身份上的角色轉換,這次似乎已不能只是歌舞昇平。但到底如何能於一直都是以「娛樂」為主線的香港演唱會模式中,把這個新身份和製作扣上?不想說教,不想煽情,又要不落俗套,但仍需從歌單和畫面上明確表達到種種訊息,這是我們面對的最大難題。
歌手身份角色轉換
我說,我想從「生於亂世 有種責任」這句話開始。既然要回歸「歌手」這個從此不一樣的身份,不如就從歌手的責任說起。如何能讓觀眾覺得自己不只是來觀看演唱會,而是當中的一分子?如何打破台上台下之間那面牆?華樂士提議,不如在觀眾進場前,你就坐在台下,大家一進場,就看到你在等着了,就是一種「我和你們在一起」。聽完這個黐線的提議,我完全沒猶豫:「好!」開場方式,就這麼敲定。
原本只是輕鬆啟動的一個演唱會,不知怎地雪球又越滾越大。我是有這種病徵,明明一開始只是想隨便做做,到最後總是會過份認真起來,而且更神奇是,總有一群人不小心跟我一起認真起來。麥婉欣的中途拔刀加入,那簡直就是梁好裘與蓮子蓉的兩不分離,元神統統歸位。
太多想說的,試圖單以音樂、聲音和影像道出,從「有一種聚散」,到「幾多種香港」、「有一種裂痕」、「有一種斷連」、「有一種我們」,甚至「有一種花生」(毛記部份),密密麻麻的訴說着香港人如今的各種無解。我們社會的病態、我們面對的無助,如滯留太空般的孤獨,我們的還在摸索中的身份認同。直到最後,我們發現,答案會不會就在社區裏,就在人與人之間那斷掉的聯繫?從我個人的故事說起,又何嘗不是眾多別人正在經歷着的疑惑?殖民地的我們、移民再回流的我們、回歸後的我們、首次要定義「甚麼是香港人?」的我們。

睜開眼睛做對的事
翻看我的筆記本,不知道甚麼時候寫下一句:「完成一個人無法做到的事」。我想,這次演唱會的威力,正是在於,這不是單靠我個人能做到的事,也不是為我一個人而做的事。
當中除了擁有團隊的強大創意和信念,更重要的是,帶有觀眾對這個地方的濃烈情感。我們把舞台讓出來,把演唱會從來強調的「歌星」變成「歌者」,歌曲已不是唯一主角,還有背後各藝術家展現的多角度香港景觀,以及團隊五十幾人的熱血,一起把我們這個家捧在手心裏,讓它變成這次的真正主角。
演唱會尾聲,沐浴中的獅子山上,出現了一句結語,「對得起自己和時代」。那是畢總為演出提供的結案陳詞。其實前面本來還有一句,「繼續推進,否則停止追夢」。也許有人會認為,在這個時代,堅持是一種病態,選擇追尋「善」與「美」也是一種不切實際,但直到你咬緊牙關,用自己的方法堅持到一個地步,讓別人也因你的不認輸而鼓舞起來,這一切便漸漸顯露出強頑推進的真正價值。
「在他的眼前,寬廣的大地展示了民生的內容……你也看見了我的兄弟了嗎?他們都是樸實、勞苦的一群,以前我只是聽見傳說,如今我親自看見。」──西西,《像我這樣的一個女子》就如侯導寄予的四字真言,「做對的事」。睜開眼睛,撫着良心,做對的事,準不會錯。生命影響生命,無論前路多模糊,我還會選擇繼續推進。Would you?

詩與胡說
撰文:何韻詩
野生菇一粒,活在娛樂圈邊境的自由人。
從音樂起步,卻意外地透過創作與生活,看到生命的可能性。
「希望」與「公義」就是自己的信仰。
fb連接 http://www.facebook.com/hocchocc
本欄逢周二刊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