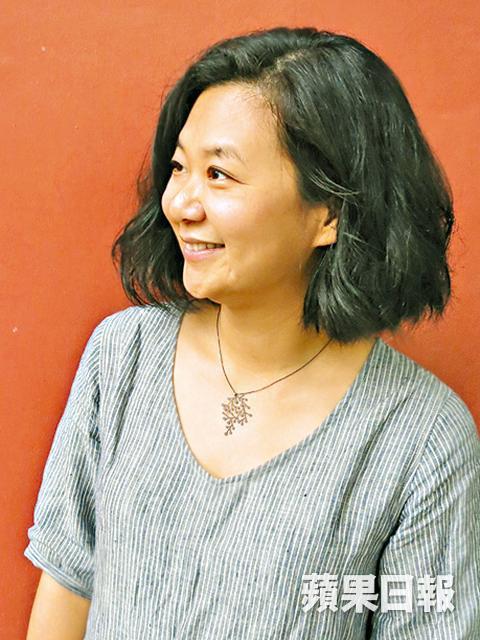
癌症甚麼時候變成一場戰爭?
美國總統尼克遜在一九七一年宣稱要向癌症開戰“War on Cancer”,傳媒以及各種公眾教育開始廣泛以「戰爭」比喻治病過程,癌症病人往往被形容為「勇士」。在香港,同樣可以發現這種「戰意」:醫院管理局出版的《認識常見的癌症病癥》小冊子,封面便印着:「癌病不等於絕症,及早治療可戰勝」;傳媒亦不斷在報道中使用「抗癌勇士」的稱號。
康復的病人是「勇士」,可是要戰鬥,就會「陣亡」──這種失敗的成見,實在沉重而不合理。Leo.M. Ellis醫生今年二月在網上醫學期刊jamaoncology.com發表文章《Losing “Losing the Battle With Cancer”》指出這有損病人尊嚴:「用戰爭作比喻,意味如果病人夠勇敢、夠聰明,就可以打勝仗。但無論多努力,有些癌症是沒法治好的。沒有任何病人應該被視為失敗者。」
因為這比喻,一些病人知道患癌後,堅決全力以付,拒絕任何退路──Leo.M. Ellis醫生卻坦言,戰爭和癌症並不存在同等的控制權,病人每天都得勇敢地面對生活的困難,不能以結局論輸贏。
珍惜最後的時刻
這種比喻背後也許是希望鼓勵病人,不要太早放棄,然而付出的代價,是漸漸不再懂得放手。有研究指出一些腫瘤科醫生為符合作戰的期望,傾向更長時間使用激進的治療方案,病人因而少了機會實現自己的真正醫療意願。
曾經訪問明愛醫院行政總監謝文華醫生,這位香港紓緩治療醫學權威,說了一個親身經歷:朋友的爸爸癌症末期,醫生說繼續打化療,她聽了各樣檢驗數字,直言:「可能最多只有一個星期。」那朋友非常愕然。
謝文華建議朋友的爸爸進醫院,可以更好地控制病情;而朋友就集合家人和親友去病房見爸爸,還在醫院一些特備用途室一起聚餐。大家都知道時間無多,所有身後事都交代了,結果就真的在七日後離世。「如果我不提他,可能那七日打化療,不知不覺就過去了,沒為意這就是最後的時間。」她說。
香港醫生普遍未能坦白談生死,當癌症擴散,不能化療,又沒法電療,連標靶藥亦無效,卻會告訴病人:「不如我幫你約個時間掃描,看到時情況如何?」那一約,往往是六個月後。
「其實三個月、六個月後,血液報告真的會好一點?這樣不是反而令病人更困擾?也浪費了病人最後的生命旅程,來不及做準備。」謝文華醫生舉例有一位八十歲的婆婆被轉介來紓緩治療科,這專科專責治療照護晚期病人。婆婆說腫瘤科的醫生也提到她有小腸氣,排期請外科醫生做手術,但要排到兩年後,婆婆直接問謝文華:「這是甚麼意思?」
謝文華醫生說婆婆也心知時日無多,奇怪醫生這樣安排,而這也影響醫院:「你轉介去外科,難道要外科醫生開聲:『婆婆,不是吧!你時間無多,還想做這個手術嗎?』為甚麼明知道這手術都不重要,還是轉介?總要做點東西才安樂嗎?」
也許,生命比疾病更需要勇氣面對。想和家人在一起,還是把時間耗在醫院等候室,寧願把錢留給家人,還是買藥打到最後一刻,這些都不是醫療範疇的決定,根本沒有輸與贏。
陳曉蕾
資深記者,著作包括《剩食》、《有米》、《死在香港》等,相信垃圾都是放錯位置的資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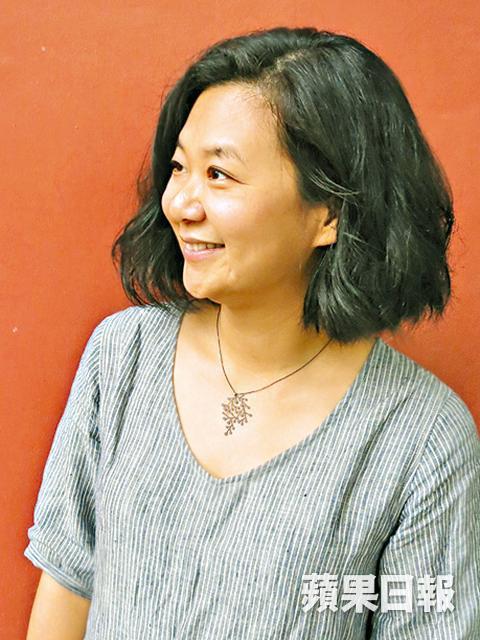
編輯:黃仲兒
美術:吳子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