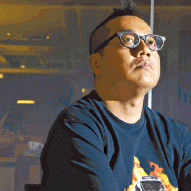今年年初的一個早上,我到紐約參觀一家電影院,在影院經理介紹着設施時,我隨口問他能否進放映廳參觀一下,因為聽說他們的椅子坐下去的感覺很不錯。那時候剛巧十一點多,早場正要開始,於是我就跟其他觀眾一起入場。場內大概只有二、三十人。我對該場放的是甚麼電影一點概念也沒有,加上後面也有行程,因此我預計只坐十分鐘左右便離開。可是十分鐘過後,我發現放的電影實在太有趣,最後我竟坐上一個半小時,把整個電影看完。
殭屍承諾不作攻擊
這部由新西蘭導演泰格韋替替(Taika Waititi)及祖曼卡文(Jemaine Clement)的仿紀錄片《低俗殭屍玩出征》(What We Do in the Shadows),在影片開始時,便煞有介事地出字幕,說明攝製隊得到殭屍承諾,在整個拍攝過程中,不會對任何劇組人員作出攻擊。看到這裏,我馬上忍不了大笑起來。
現在不少電影都喜歡一開場就出字幕,但其目的很可能只因為在初剪時,發現故事根本說不通,因此得有一些字幕去說明。可是一版又一版的文字資訊,會讓人在還沒有看到影像前,就先煩惱起來。你得明白,觀眾進入電影院,並不是為了看文字,因為要是這麼喜歡看文字,倒不如直接去看個小說。所以作為創作人,我一直都很抗拒,在開場時呈現大量文字資訊,去讓觀眾先了解,最好能以簡短的三言兩語說完。當然,《低俗殭屍玩出征》這種幽默形式的開場,就絕對可以接受。
電影是以仿紀錄片形式,去講述幾個活了數百年的殭屍之生活煩惱。其實吸血殭屍的電影已經看過不少,本以為不能再玩出甚麼花樣來,所以實在不得不佩服導演,自編自導自演和幾個朋友玩出了新意來。也許有朋友還沒進場看,所以就不方便說太多,但創作人在許多大家都熟悉的細節上,還是扭盡六壬,變出各種笑點,當中殭屍和人狼之間的幾場衝突,就讓我狂笑不了。


冒險配三級粗口版
散場後,我不理時差,就急不及待在微信上,把影片推薦給香港的朋友。後來聽到今年電影節會把影片選為節目當中,於是我又在網上推薦給其他人。電影節知道後,還留了一些門票給我送朋友,結果我推薦給不少創作人去看。那時候電影節把其中文名字繙譯為《直擊殭屍屋》(我認為有點過份平實),門票也很快售罄,後來電影節還加了場。
其後慶幸發行公司巴福斯把它買了下來,提出要在香港上映,並決定以英語原音版及三級粵語粗口配音版一同上映,而中文名字也改成《低俗殭屍玩出征》。可是在改了名字後,卻引來不少譴責,說為甚麼只因為找來鄭中基和杜汶澤配音,就硬要改上一個這樣抽水的名字?
其實我認同發行公司的看法,因為要是只純粹上映英語版,根本連買下來做生意的機會也沒有,原因是這種小眾瘋狂喜劇,是很難得到院線垂青,所以為了把它帶給更廣大的觀眾,就必須本土化,而粗口配音是個很大膽的決定。當然,希望看原音的人,絕對可以選擇原音英語版,但這個本土化的粵語版,能讓市場看到一線生機。因此我不介意他們拿了《低俗喜劇》和《飛虎出征》來幫忙宣傳,好電影本來就應該推廣給更多人看,改上一個甚麼中文譯名,也影響不了它好看的本質。
另闢蹊徑拍出好片
我是做創作的,也拍過不少喜劇,所以我很了解,能引人發笑其實是件極不容易的事。本來我對創作喜劇就特別有壓力,因為感覺甚麼都很難讓自己發笑,可是在初次看《低俗殭屍玩出征》時,即使沒有中文字幕,還是讓我在紐約過了一個愉快的早上,也是近年來,我看過最讓人心情愉快的喜劇。
當然,《低俗殭屍玩出征》不是《復仇者聯盟》(Marvel's The Avengers)那種荷李活大片,它成本不高,演員我們也不認識,但就是因為資源上的限制,反而讓他們另闢蹊徑,找到了一個有趣的演繹模式。所以每個埋怨得不到資源拍攝好電影的電影人,不妨去看一下《低俗殭屍玩出征》,也許會得到不一樣的啟示。
【我來了,是要叫人得過癮】
撰文:彭浩翔
祖籍番禺,生於觀塘。集作家、編劇、導演、製片人、演員及藝術家於一身之處女座。尚且幹活,只為供養其網購血拼及極限運動。
本欄逢周六刊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