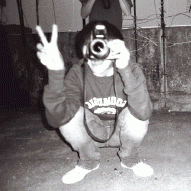我極不能悶。
年少時,隱約感覺到自己無法做單一的工作,每天重複一樣的事宜,腦筋不流動,只會令人慢慢枯萎,故此早就立志從事創作行業。若是沒有那贏了新秀的意外,應該就進了廣告行業。
後來當了歌手,進了這個看似滿是創意的環境,還是發現,喂呀,會悶的。那個悶,來自這裏的太多規限,大公司有大公司的限制,媒體有媒體的慣例,所謂的創意工業往往只剩下工業,沒了創意。空氣不流通,就連帶裏面的人們,開始時候的滿腔熱忱,經過這圈子長久的洗磨,血液亦漸漸凝固,齊齊患上各種痛症。
歌曲堅持真人彈奏
最近回歸音樂人,又多了一個投資者的身份,兩者加在一起,創意vs計數,有點矛盾,要顧及和學習的事情不是一般的多。從前不需理會的各種行政步驟,現在統統要靠自己去處理,單是做一首歌,甚麼作曲作詞版權費平台抽成支出費用,燈油火蠟一籮籮,要在這個唱片已經不再盛行的時代思考如何回本,基本上是mission impossible。
打個岔講個題外話,之前看見有人質疑做一首歌為何要那麼貴,火都嚟。告訴你,一首歌一張唱片背後要養一村音樂人,除非甚麼都只是在家中DIY,若要有品質的音樂,就要有相對的人才和器材,這些器材不會從天上掉下來,要用錢買,人才也是。有對音樂的熱情就不用交租吃飯嗎?當然現在甚麼聲音都可sampling,但對音樂有要求的人,還是希望歌曲中的樂器是有靈魂的。本菇專輯從來都堅持真人彈奏,可惜大家聽到歌曲時,都會自動省略這些背後的人力物力,看不到歌曲的真正價值,這算是我們教育的失敗。

有沒有辦法不一樣?
回正題。上回講到,我是黐線的。所以impossible歸impossible,還是任性地試試看。最近除了製作新歌,也在努力籌備「十八種香港」八月伊館,首站啟動演唱會。
第一次自己主辦大型演唱會,又是經歷了多重轉變後的第一次,當然有很多想嘗試的。香港演唱會文化從八十年代開始,到了今天,除了科技有所進化外,整個格式也幾乎從未改變過。那種你進場當觀眾,我穿珠片飛天遁地地唱歌跳舞的娛樂大家模式,運行了三十幾年還是一成不變。大佬,你不悶,觀眾也都看膩了。
然後我會想,到底有沒有辦法不一樣?不只是說加入更多爆破更多高科技配件的變化,而是說,那套表達方式,有沒有辦法不一樣?真的需要三小時換八套衣服嗎?不露肉可以嗎?更有內容可以嗎?製作模式有沒有可能不一樣?有沒有可能不只是一班工作人員襯托一個歌手,而是從台上到幕後,歌手樂手燈光舞台設計以至影像設計都是一個團隊,一起說出共同想法?有沒有可能連帶觀眾也能包含在這個團隊當中,台上台下一起說出我們對這個地方的期望?

義氣仔女為我接力
港式娛樂就是愛低估觀眾的消化能力,常常會把事情都描繪到一清二楚,結果消除掉一切想像空間。人的腦袋是有潛能被激發的─你把一切填到滿,讓他們從A看到Z,然後畫上句號另加一條腸,他們就永遠只會待在這套模式裏面;但若能留點白,停在一個冒號上,who knows?也許久而久之他們還能創造出屬於自己的另一套語言出來。
現在的我們,不只樂壇悶,娛樂圈悶,就連整座城市也很悶。你不覺得嗎?腦筋和血液都好像停止轉動了,整個環境快患上關節炎,動彈不得。但,有危便有機,甚麼都說不可以的時候,其實就是甚麼都有可能的時候。
訪問時我說:「現在我的可能性,就是我連走到深水埗打個筋斗也可以。說不定還會有一群人跟着我一起打。」原諒我的自信,但我是真心相信跟我一樣瘋狂而且願意一起試試看的人,多的是。而且我一貫的利誘方式,是自己先跳下水,濕晒身一股勁的游啊游,游到接近抽筋遇溺之時,就會有看不過眼的義氣仔女張開雙臂跳下水來為我接力,然後一起癲狂衝浪。
還有儍勁的人們,來來來,一起跳下來跟我在水中翻滾韻律泳吧!
P.S.自資四場伊館,今天城市售票網開售,請多多支持!

詩與胡說
撰文:何韻詩
野生菇一粒,活在娛樂圈邊境的自由人。
從音樂起步,卻意外地透過創作與生活,看到生命的可能性。
「希望」與「公義」就是自己的信仰。
fb連接 http://www.facebook.com/hocchocc
本欄逢周二刊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