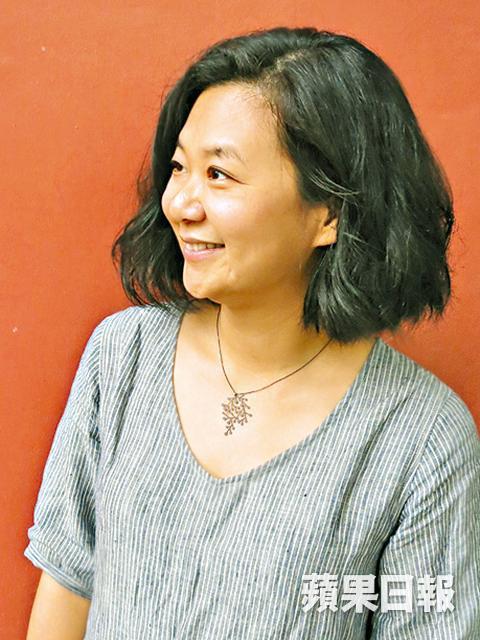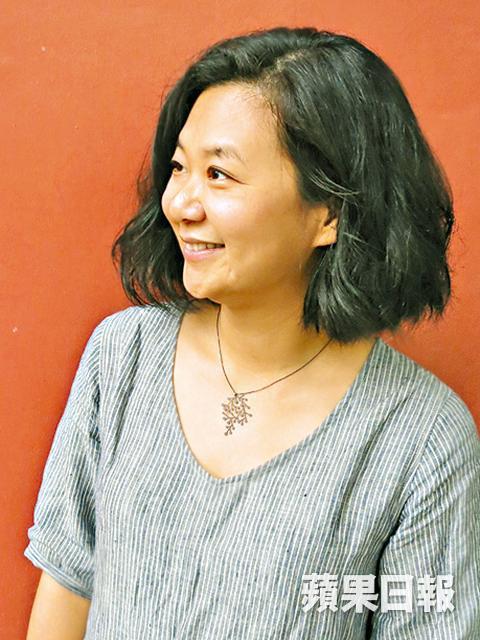
上周寫了日本醫生朝日俊彥視癌症是「幸運」,輕鬆地走完人生最後一程。可是,不是所有人都能夠這樣看得開,陷於情緒低谷時,誰能扶一把?
A有乳癌,最初心情樂觀,做完手術,第三次化療後開始沒法睡覺。醫生開了安眠藥,但說:「不要吃那麼多,個個都會失眠,慢慢就會好。」她不敢吃,結果一整個月都沒法睡,親戚都勸:「誰誰誰不也是乳癌?現在咪幾好?你別想太多!」丈夫支持她去看精神科醫生,可是藥物和安眠藥混在一堆,愈吃愈沒精神。
她割脈,一次用剪刀、一次用小刀,都失敗,丈夫嚇得全天候看著她。一天早上,她藉口想吃粥,叫丈夫上街買,又想自殺。「割脈失敗,我就想焗死自己。」揭開床板,躺不進去,於是躲進衣櫃,用衣服、膠袋重重蓋住。丈夫回來不見她,發散所有親戚去找,她待在衣櫃裡兩個小時,聽到所有電話對話,心裡只想:為何仍然可以呼吸
丈夫打電話找到一個朋友,其家人有抑鬱症,說不可能走得遠,先找家裡。丈夫這才打開衣櫃,見到她,嚇到彈開!親戚都來了,沒人敢走近,一個多小時後妹夫把她拉出來。
丈夫迫她去私家醫院的精神科,終於開始好轉。A乳癌康復,八年後再患上腸癌,發現時已擴散到肝臟。這次她去屯門醫院腫瘤科,一開始已經有心理學家跟進,心情好,反而能面對。「個人的精神可以比癌症更大影響,一定要能夠睡得著。」她在病人小組裡分享。
這小組的主持,不是社工,而是高級臨床心理學家何鳳珠博士。何博士坦言很多病人都忽略了心理需要,「我有癌症,不是黐線,為什麼要見心理學家?」可是病人情緒直接影響病情,睡不著、沒胃口、緊張、恐懼……全部都會影響治療成效。「長期睡不著會令人抑鬱,恐懼也會令人無法吸呼,病人自覺快要窒息,只懂得去急症室,但這更多是心理原因。」何博士尤其關注癌症病人的痛症,「有些病人真的『痛到想死』,但如果不痛,卻未必想死。」
她團隊裡八位心理學家,全部都受過專業的催眠訓練,可以利用催眠替病人止痛。曾經有位病人腸癌的位置近肛門,電療後傷口潰爛,痛得不能坐,不能開步走。「我替這病人催眠,離開時,病人心情輕鬆,居然可以站直走路,同事都很愕然。其實這不神奇,痛是非常主觀的,而大腦是可以操縱。」她強調心理學家經過嚴謹訓練才做催眠,心理治療也是治療的一部份,「我們不只是和病人談天開解,這是psych medical,心理學家和醫生都是一個團隊。」在屯門醫院,腫瘤科病人一開始便有機會按需要接受不同的心理治療活動。
對於醫療治療效果不大的晚期癌症,心理治療就更重要。何博士引述一份美國研究指出:最長命的癌末病人,是相對能夠入睡的一群。她有一位女病人垂頭喪氣,天天在家哭,家人都很難過,女兒於是勉強帶來參加病人小組。媽媽聽到其他病人分享,心情好一點,再加上一些冥想練習,開始能吃能睡,情緒穩定,精神好了。「雖然始終都會走,但她最後的日子生活質素好一點,也讓家人安心一點。」何博士說。
Profile:陳曉蕾
資深記者,著作包括《剩食》、《有米》、《死在香港》等,相信垃圾都是放錯位置的資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