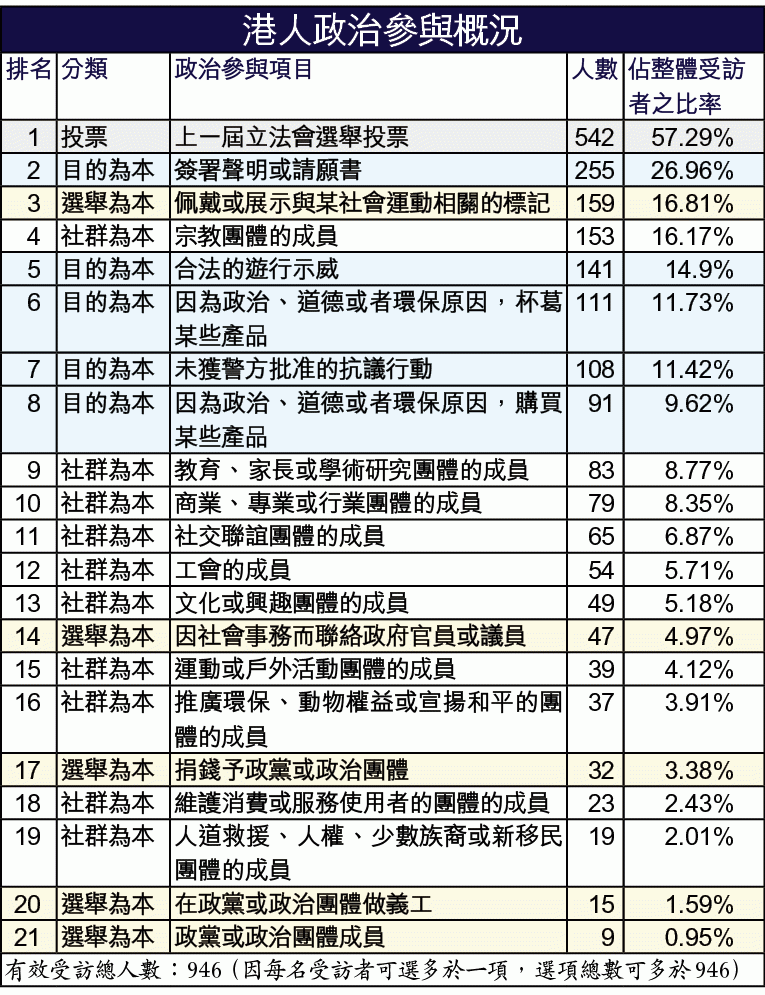
經歷了雨傘運動洗禮後的香港,所面對的困局不再是缺乏政治醒覺和參與,而是由運動所釋放出來的政治能量,往往是採取一個重個人,而抗拒領袖和組織,甚至互不信任和互相攻擊的形態來顯現。這逐漸地形成一個具有「香港特色」的政治參與模式,一個有參與者但沒有組織的情況,眾多參與者可以共處於同一個集體運動中,但又互相保持距離,互不代表對方的「離群共處」怪現象。這個現象在筆者的全港性調查中也得到了印證(註一),為香港民主運動的前路添加了隱憂。
在雨傘運動下,我們看到了香港人聲勢浩大,其實暗藏危機,就是過於着重個人而缺乏緊密組織協調和強化的政治參與,削弱了運動的最終影響力。
為了證實這個說法,及更全面了解香港人政治參與的整體情況,筆者的調查參考了哈佛大學政治學者Pippa Norris的研究(註二),使用了「政治活躍指數」(Political Activism Index,簡稱PAI)作為量度政治參與的指標。PAI分為四個面向:投票(Voting)、選舉為本(Campaign-oriented)、目的為本(Cause-oriented)及社群為本(Civic-oriented)。
除了投票外,每個面向下再分為不同選項。選舉為本的面向主要是量度和政黨及政治組織相關的參與;目的為本面向下的參與,傾向以較個人化和建制外的手段如聯署和遊行等,達到個別運動的目的;社群為本則詢問受訪者是否某些組織,例如工會、教會、專業團體和環保組織的成員,透過其組織網絡來量度參與程度。
研究的假設,即香港人的政治參與模式往往不喜歡透過或依賴組織,而傾向以個人身份參與,得到了支持和證實。附表詳細列出組成這個PAI的21項參與,並按每項之人數多寡排序。排名第一的是投票,顯示香港人的高度公民意識。可是,排名前列的絕大部份項目均是傾向個人化的目的為本項目,重視組織的選舉為本及社群為本的大部份項目的排名及參與率均偏低。
排名第2、5、6、7、8的參與項目,例如簽聲明、遊行抗議和杯葛或購買某產品,都屬於目的為本。這類參與模式,對主辦組織的依賴和認同相對較低,參與者往往以個人身份參加,只需認同行動而毋須加入任何組織,更可隨時選擇脫離行動以劃清界線。例如,即使共同參加遊行或某聲明,個別參與者也未必認同組織者。近期最明顯的例子是佔領期間,雖然運動本身支持者眾,但個別參與者或群體,對雙學、佔中三子,乃至「大台」甚為不滿,其後各院校更衍生退聯的行動。
選舉為本的項目,即與較為嚴緊的組織(例如政黨)有關的參與行為,在香港並非主流,排名為3、14、17、20、21。當中之所以相當多人曾展示標記(排名第3),相信大部份是和雨傘運動的特殊情況有關,未必與任何組織有太大相連。同樣地,除了宗教組織外,社群為本的項目的排名及參與率均十分低,顯示了香港人對組織化參與的抗拒或不信任。
這種因對「大台」不信任、對領袖心存芥蒂,而定意不靠攏任何組織,只信任自己個人力量的「離群共處」參與模式,長遠下去有機會進一步撕裂公民社會,大大降低帶來轉變的可能。回歸政治現實,組織對團結運動中的群眾力量的作用仍不可忽視。
在這個反思前路的後雨傘時代,對很多看過電影《馬丁路德金:夢想之路》(Selma)的朋友來說,感受最深刻的是領袖、團結和策略對在抗爭中爭取最後勝利的重要。一如電影的主題曲《榮譽》(Glory)的歌詞所說:沒有人能在戰爭中單獨取勝(no one can win the war individually)。只有排除分歧,有效地整合個人力量,才是通往勝利榮譽的夢想之路!
註一: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委託中大傳播與民意調查中心,於2014年11月12-14及17-20日進行「媒體和公共事務」意見調查。
註二:Norris, Pippa.(2005)"The Impact of the Internet on Political Activism:Evidence from Europ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lectronic Government Vol.1 (1):20-3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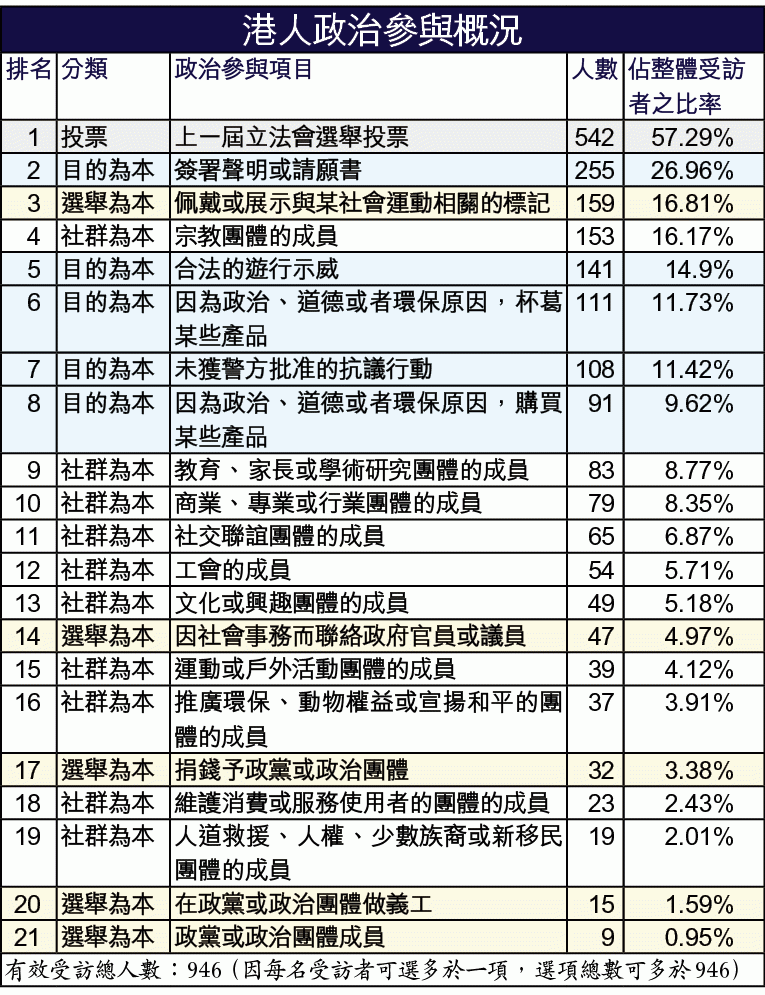
黃偉豪、陳思恒
中大政治與行政學系副教授、研究助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