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羅便臣道私人屋苑裏的猶太人社區,裏面有一所用彩色玻璃點綴的教堂,教堂前是微黃麻石廣場。像從歷史走出來的美國老兵Rick Carrier,坐在教堂門外石壆接受訪問。身後一盞孤燈,伴他訴說七十年前人類最不人道的戰爭苦痛景象。
第二次世界大戰終結七十周年,Rick因為曾參與一九四四年登陸諾曼第戰役,以及於一九四五年發現圖林根(Buchenwald)集中營,他上周末應香港猶太大屠殺及寬容中心來港,到不同學校巡迴演說,見證戰爭真相,讓學生親身接觸老兵,上歷史一課。
「你想知道甚麼?我告訴你」。無風無月的香港冬天,空蕩的廣場,像騰出一次歷史相遇的機會,讓老兵在他喜歡的天氣裏,講一次七十年前見過的事情。
「我想知道你剛發現集中營時候,在裏面看見甚麼?」記者問。老兵對鏡頭非常敏感,很留意攝影機運作情況。說話時傾向主導內容,且敍述能力極強。
「啊,我沒有進去。我當時很害怕,要記得,我那時還是年輕人,這事剛好發生在我二十歲的那天」。近六呎高的老兵,不拿枴杖,喜歡跟年輕人說話。
「我那天起床,還在想,很美滿的一天,我踏入二十歲了,不再是少年。誰知,那天找到的是Buchenwald。在我一生之中,從無這樣的經歷,那是不能相信的經歷」。人以為生活美好得只有再美好之時,在另一片碧藍天空下,有戰火,有殺戮,有比不幸更不幸的,歷史與現實,從來沒有改變過。
Rick Carrier於一九四五年四月十日,成為第一個發現Buchenwald集中營的美國士兵。集中營位於德國北部山坡,在他口裏,集中營如在電影鏡頭中從遠到近展現。

嗅到比看到的惡心
「若跟在死亡集中營所嗅到的味道相比,任何地方的氣味,都如香水」。眼睛很近,思想很遠,這是他發現集中營後的第一個感覺。當嗅到的比看到的還惡心,恐怖的事情一定存在已久。集中營單是味道,已經令人如陷死亡之谷。按West Press出版的《The Buchenwald Report》紀錄,那裏曾關押約二十三萬多人,最少五萬多人死去。戰後於巴黎習畫的Rick,曾遇見畢加索,受大師指點鼓勵過。擅於視覺影像描述的老兵,這一次以口述方式,再次繪畫那個令人震驚的歷史畫面。
「只剩皮包骨的活人,他們不會說話,因為他們根本不能說話」。Rick模仿骷髏人發出深沉的聲音,彷彿絕望的靈魂又再於面前走動。「在他們身邊走過,迎着面對面的臉孔,都是瘦得只剩一對大眼睛,眼睛外面圍着黑色眼圈,若果他們張開嘴巴,看到裏面的牙齒,全都腐爛。他們滿手長了不知甚麼東西,所有頭髮都掉光。全身只剩骨頭,完全沒有一處有脂肪」。他一邊說,一邊比劃着,這個人間地獄裏的人,就是跟生活在貧民窟的窮人比,絕對相差一萬八千里。
「裏面的人如走動骷髏?」記者問。
「是,走動的骷髏。但難以想像,他們走動時並沒有顫危危。其實,他們每天碗口裏的食物,可能只有一點點油,加一片紅蘿蔔,一片蔬菜,再加一小片麵包,這就是他們所能吃到。若果被發現偷多一點點食物,就會被拉出來毒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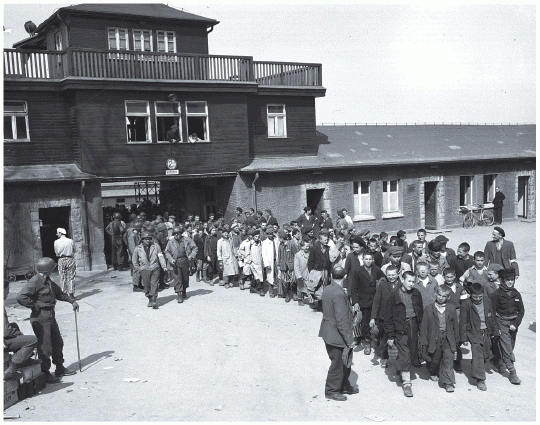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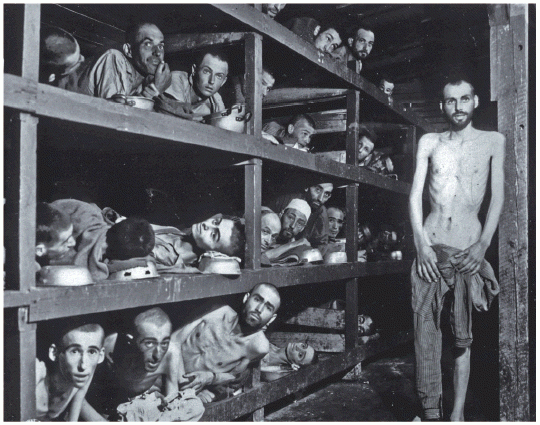
交談也會被吊死
進入營裏以後,Rick沒有可能跟任何人對話,「營裏的人,四處站立着,根本不能說話。即如在眼前這個廣場,有人走出來,目光空洞,向你發出不明的聲音」。空洞的活着,絕望都在雙眼裏。「但他們不笑,我看不見一張笑臉,在裏面,根本不知道甚麼是歡笑」。可是,被囚的人當刻意識他們已被救,護士及相關人員立刻照顧他們,並安排他們離開。
經長時間調查撰寫的《The Buchenwald Report》裏,有一張被囚在Buchenwald的政要名人名單,裏面包括意大利國王的女兒、法國的總理夫婦、巿長、工業家、作家及世界游泳選手等。主要來自歐洲各國包括前蘇聯、前南斯拉夫、猶太人、波蘭人,甚至中國人。在黑暗勢力到來之時,不分貴賤,都成了極權裏的囚徒。
「我進入Buchenwald第一件聽聞的事情,是囚犯進入裏面以後,被分配二百人囚在一個倉裏。每一個營倉由一個囚犯當指揮控制,每個SS(納粹德軍親衞隊)指揮管理六個營,每一營房的指揮決定誰可以外出,或是做任何事情。另一個人負責紀律,他的工作是把搞事的人處決,然後丟棄到營外。」
納粹德國在集中營裏,施行各種不人道刑罰,包括用活生生的囚犯做醫學實驗,又用絞刑,把囚犯折磨至死。Rick聽到一種刑法,「他們用繩把人的手綁到後面,然後從後把他們吊起。全身的重量都會墜到肩膀上,這樣被吊起,大約要兩天時間才會斷氣。其間受害者恐懼地尖叫着,直至死去。所以,進入營後,沒有人會交談,不准交談。若被發現交談,就會這樣的被吊死」。
第一天解放集中營,所有管營的人都被捉拿。一九四五年納粹德國已經開始把集中營納粹德軍負責監控及治安的親衞隊撤退,按Rick所知,美軍進營時,仍留着八十個親衞隊成員。因果循環,有人把德國管事者逮着,然後,用以眼還眼的方法,把他們處死。「他們不肯立刻殺掉那些人,要施刑者像以往無辜集中營囚犯同一方式死去」。施刑者雙手被綁到後面,吊起掛在樹上。他們稱呼這些樹做「歌唱樹」(Singing Trees)。
「雖然我沒有看見,但我聽得見,長長的慘叫着,像狗嗚咽着:『嗚……嗚嗚……』他們不能說話。直至他們死亡,有時只需幾小時」。有一種味道,有一種聲音,留在他心裏已久。


引美軍解放營地
命運注定,他有一個歷史任務。「我不知Buchenwald在哪裏,我就是要找出它的位置」。當時美軍根本沒有任何相關情報,他隸屬的部隊負責工程,專門搜尋德國人的工具及物資,用來建屋築路,以及設立電話通訊等。
Rick的上司當時正在追捕納粹德軍,後來有人通報附近有一個很大的集中營,授命Rick訪尋。Rick指示工程部開貨車去接應,運送接收物資。途中經過一個剛被兩枚炸彈轟炸的德國小鎮,認識一位在教堂前擺放桌子、專門慰問鎮裏人的神父,因為,爆炸過後,所有人都惶恐不知所措。Rick問起神父集中營的事,神父對他說:「我知道在哪裏。」當時,憎恨納粹的德國地下革命組織,已開始反抗納粹德軍的行動。神父找來兩名知情的俄國人及德國女孩,一起協助Rick。
最終,神父、俄國人和德國女孩,三人坐Rick的吉普車到山坡尋找集中營。因為有中間人牽引,所有人安全到達,沒有受狙擊。「集中營的人協助我跟鐵網裏的人說話,告訴他們我是誰」。當時,他還見到有一個營裏被囚的人,冒險在鐵網下,扒挖着泥土,在他面前匍匐着逃出來,對身體的傷害,好像一點也不感覺痛苦。當Rick把鐵網剪開,也有四個人,毫無畏懼地走了出來。
Rick審視現場情況及位置以後,立刻發放無線電傳訊回去軍部,然後指引美軍部隊到場。翌日,Buchenwald被全面解放。Rick說,美軍當時沒殺任何一個人,「美國人只把生人帶出來。還有不同的機構工作,把倖存者帶走」。他估計,解放Buchenwald之時,可能有四千人進入集中營裏面,包括醫生及護士。
Rick說,當時不可給瘦弱的倖存者任何食物,包括朱古力,「當他們吃下朱古力,不夠五分鐘就會倒下死亡,一下子被殺,因為,胃不能適應新食物,會吐血,所以,不能給他們任何食物,一切要由醫生處方,護士執行,大多只能吃液體」。而按《The Buchenwald Report》紀錄,發現集中營時有約二萬一千名被囚倖存者,至正式點算紀錄時,倖存者只剩二萬人,有一千人捱不住死去了。Rick留在Buchenwald足足三星期,負責把營裏倖存者包括小孩叫出來,安撫集結。他獲頒的一個重要勳章,就是紀念他救出被囚少年Irving Roth時候的感人場面。「三十年前,我看到一本法國雜誌關於大屠殺的報道,赫然在照片中看見自己,我是第一個星期天其中一個從教堂走出來的人」。
解放集中營的歷史見證者,一生都埋藏真實的殘酷畫面。活了這麼多年,生活是如此充實,作為一位作家,一位導演,老練的歷史傳遞者,很明白外面人想知道的。但集中營看到的景象,對外來者終究是個創傷。
「這經歷對你有何影響?」記者問。
「我仍然感覺痛苦,當我講述經歷,就有悚懼的感覺,我不喜歡做這件事情,這是一些我不想再說的話,但因為你想知道這些資料,我盡力給予,但這不是好的感覺。」兵哥性格,坦率直接。
「還會有毛骨悚然的感覺?」
「這是內在情緒感受,若果我在咪高峯前再說,好多時很容易落淚。我告訴你看見的情景,把見過的人再描述一次,猶如回到那個過去,其實我心裏並不安寧。」


太陽穴留下疤痕
從解放集中營開始就難以阻止復仇,人的殘忍行徑,由一個權力,轉移到另一權力。「當我們離開,俄國人接管,又把它變成另一個集中營,地獄一樣,他們殺害更多人」。這就是歷史小兵看到的真相。
慘烈的戰爭、見證不人道對付人類的恐怖經歷,沒有令他悲觀。只是,人沒有好好學習,他憤恨極端組織伊斯蘭國把人質斬首,認為完全是邪惡的。談到現今世界秩序,老兵完全感到失望,「我以為已經走出戰爭殘殺陰霾了,誰知現在更差,恐怖的事情又回來了」。
征戰幾人回?右邊太陽穴仍留着淺淺一道小傷痕,那是D day登陸諾曼第一役造成的。因為爆炸碎片擦過額邊,留下疤痕。「祖母常提醒我,要靈巧像蛇,所以,我經常都伏在地上,不想被擊中」。偌大的艦艇在海上開火,天上的空軍放下如雨的炸彈,一切都在分秒間摧毀,士兵被攔腰削開兩截。Rick Carrier知道,戰爭的殘酷,跟電影情節一點不能相比。「電影裏頭看到的,沒有一點像真實」。
Rick小時候活在貧困大蕭條時代,在故鄉賓夕法尼亞州捉野兔,打黑熊,把毛皮曬乾留下,把肉送到豬肉檔處理。如他所說,或許戰爭改變他最大的,是熱愛生命。他媽媽懂得做衣服,姊姊曾是紐約著名模特兒。今天的老兵,仍然充滿活力,現居紐約曼哈頓,他六十年代自編自導兼拍攝第一部獨立電影《Strangers in the City》,講述異鄉夫婦在紐約的生活挫折。現在Rick正為電影拍續集,還在寫大屠殺的書。
「電影中兩個男女主角現在怎樣?」記者問。
「哈,我才不會告訴你」。老導演把已經六十多歲的男女主角找回來,用電影語續說他們已經變成怎樣的人。訪問完結,記者從石壆把老兵扶起,一時間,他顫抖抖,雙腳乏力。征戰沙場,見證苦難,當一切已成過去,他還是相信:活着真好。
記者:冼麗婷 攝影:謝榮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