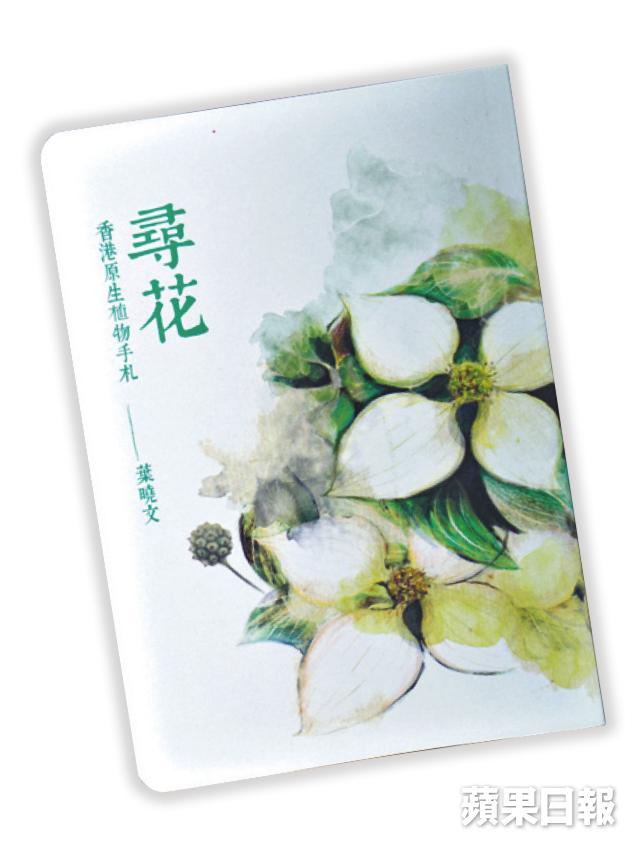如果不是李嘉誠一句佔中對他的生意影響好少,我幾乎忘了科大經濟系教授雷鼎鳴的巴閉預言,甚麼佔中每天損失十六億元,長遠損失一萬一千億元,雷氏計數機果真如雷貫耳,貫在它的失靈。
這次燈神再次登場,這回計出減少郊野公園面積,換來一年二百八十八億元的居住成本,雷氏粉絲(如有)會貫徹不要問只要信的作風,反正億億聲也夠嚇唬人的,那麼我等愛書之人只好從書中領略香港郊野公園的可貴。
撰文:呂珠玲
台灣角度看四分三香港
香港行山友應該感激台灣作家兼自然學家劉克襄的,他的書提醒我們香港的郊野公園是怎麼精采絕倫。他會由衷告訴你,儘管台灣也有連綿山頭,卻不像香港的郊野般山水一色;他說台灣人只能飛往澎湖群島才見玄武岩,但香港人坐程的士即見萬宜水庫的奇稜巨岩。劉克襄約十年前任浸會大學的駐校作家,他爬獅子山的次數比很多香港人多,後來他甚至由台灣專程飛來香港行山。他在書中寫的二十六條行山路線,由最熱門的獅子山到最冷門的屯門徑,他都以秀麗的文字描繪出如畫的風光,還有他親手繪畫很有繪本特色的行山地圖。
在雷鼎鳴眼中,郊野公園只是一堆死物,但在劉克襄眼中,香港的古道是本土歷史的見證、山村是尋常農家的安樂窩、還有風水林是嶺南文化的精髓。佔香港四分之三土地的郊野公園,是香港人的重要資產,我們必須好好珍惜。

追溯八十年行山潮流
撐起郊野絕非為了趕潮流,資深行山友郭志標證明早在香港開埠初期,已有人繪製新界郊遊行山指南,連外國的動植物學專家也愛到香港的山頭研究本地品種。到二十世紀中期,本地行山組織更是遍地開花,包括一九三二年由老報人創立的庸社,每周舉辦一次行山團。
這本書詳述香港人的行山歷史,當年人們去大埔行山,得大清早到尖沙嘴鐘樓旁的火車站坐車;要是往大嶼山行山,還得趕上黃昏前的尾班船回來。書內憶述當年不同行山組織的創辦人,又收集這些組織的刊物、隊徽、襟章和旗幟,還有當年自家製的行山地圖。
這本書以八十年的香港歷史呈現本土旅行的發展過程,以麥理浩港督年代通過的《郊野公園條例》為里程碑,到沙士襲港時行山遠足活動復興,行山友的每一個腳印,其實都在撐起郊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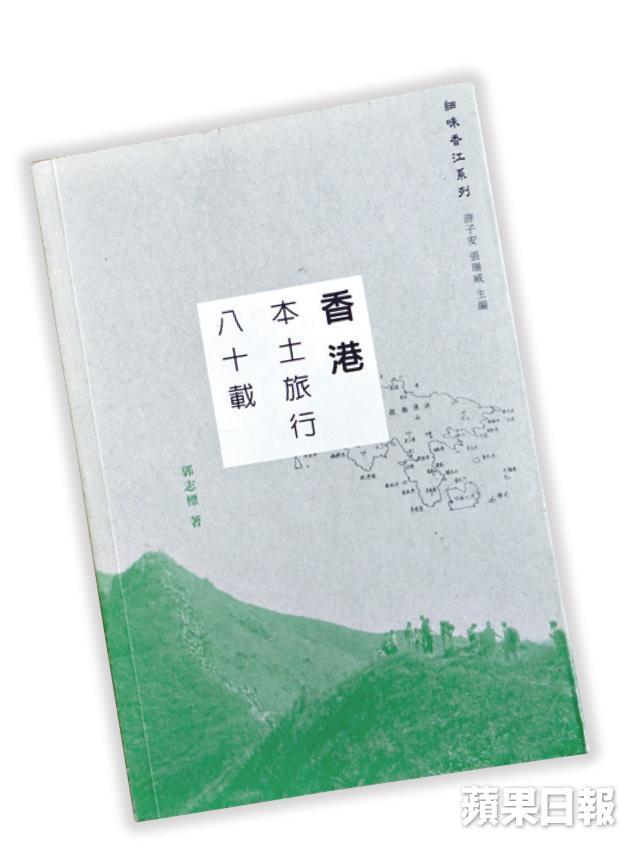
叫人感動的花卉紀錄
十九世紀末法國神父發現了洋紫荊,二十世紀中土生葡人白理桃女士蒐集一百二十多個本地蘭花品種,多年來外國植物學家對香港的花草樹木情迷不已,不過香港人也不讓外國學者專美,包括年輕作家兼畫師葉曉文。她花了一年時間跑上山頭尋花,紀錄了五十種香港原生植物。
二百多頁的精美小書,依夏、秋、冬、春四季紀錄,蘆葦、金線蘭、紅花荷、羊角拗等等,葉曉文都一朵一朵繪畫, 並寫下牠們的學名、種類、花期果期、出現地點,以及列入《香港稀有及珍貴植物》的哪一個瀕危級別,背後所花的精神時間,叫人肅然起敬。葉曉文畢業於嶺大文學系,贏過青年文學獎小說組冠軍,每一張漂亮的圖畫後頁,都是她約五百字的散文,以一手秀麗的文字寫下一個關於這朵花的故事,也許是她某天的行山經歷,也許是這朵花來自詩經或楚辭的某段典故,認真得叫人感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