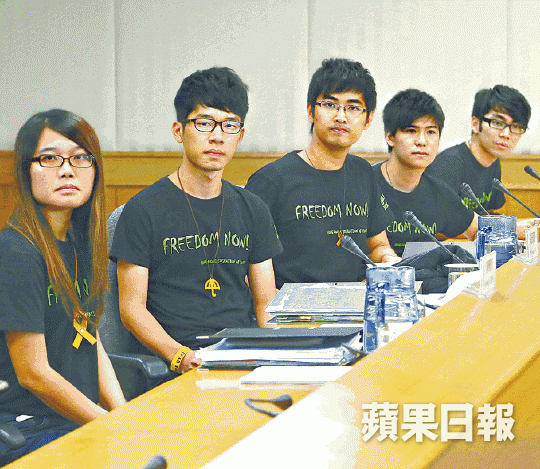大約是上周日,陳健民在親友陪同下,第一次從雨傘廣場回家。喝了一碗好湯,躺在床上,一睡11小時。
床上是久違了的柔軟感覺,但身體太累,心太清醒。半暗半明,半睡半醒,還是記掛手機會不會突然傳來廣場的訊息,怕別人有事找不着他。未來日子,除了為香港中文大學課堂備課會回家兩天,其餘時間仍然會留守廣場。前天他在電話跟記者訴說複雜心情,「回家了,但沒有回家的感覺」。
陳健民作為和平佔中發起人之一,初衷是公民抗命爭取2017年真普選。現在佔中變成雨傘運動,預計數天的公民抗命演進為看不到盡頭的抗爭。他上周二回校,佔領後首度復教,那一課,是講社會運動的價值傳遞與創造團結。課室裏的學生,見他進來,先是呆一呆,然後就如眼下香港人一樣,經過複雜的亢奮、過度的情緒燃燒,開始進入平靜的期待裏。

終有一天自首上庭抗辯
2003年西班牙右翼保守執政黨在大選前夕,把火車站恐怖爆炸襲擊推在巴斯克分離分子身上,實情是,西班牙政府與美國聯盟反恐攻打伊拉克,引至阿爾蓋達報復襲擊火車站。一個少年聽小眾電台分析,找到蛛絲馬迹後,發了10個短訊號召朋友到執政黨總部默站,誰知短訊十傳百、百傳千,結果數千人到場要求真相,一發不可收拾,最終引致執政黨選舉失敗下台。這是陳健民以往在課堂上講授的蝴蝶效應例子,現在恍然自己也在佔領運動裏經歷了這個序幕。
他說,9月26日黃之鋒等學生衝入政府總部公民廣場,如蝴蝶拍翼,噠噠噠,其他學生和應,然後佔中三子與巿民陸續捲入一場香港史無前例、你中有我的社會政治運動,「那是活生生的Butterfly Effect(蝴蝶效應)引發的一場現代社會運動」。
從蛹變蟲,蝴蝶拍翼高飛一刻美麗,但生命是有軌迹的,香港爭取民主30年,走到今天,看着蝴蝶撲不過天涯,我們有權不理解嗎?
「有隻蚊!」2014年香港10月圍城,近龍和道立法會外示威區帳篷盡處草坪,陳健民早前接受訪問,講到運動形勢尖銳之時,突然釘着一方癢處發出警告,記者閃快用右手打了自己的左手臂一掌,在看得見以前,蚊子已經飛得無影無蹤。世間上,很多事情本來就是徒勞無功的,那管是打死一隻蚊子。
陳健民自小迫自己理性思考,運動之中,他與戴耀廷既不以領袖自居,又不能隨心而退,如履薄冰,六四烙印的一代人,不為物喜,不為物悲,時刻以學生安危為重。在中大修讀社會學之時,他也修藝術課,懂得畫畫寫書法。一本書、一杯茶、好音樂,就可以安然度日,所以他說根本不恐懼周融要就佔領告他至破產。為公民抗命向警察自首、上法庭抗辯,這筆賬,他有天一定了結。
學生時代的陳健民,有強烈宗教信仰,八十年代社運之子,半生追逐,一半理性埋葬一半感性,投身佔中運動後,一半支持還要面對一半反對,「現在乘坐港鐵,有一半人跟我握手,但還是有一半人想打我吧」。
這一次,沒有多少香港人能置身事外,有人滿身拳印,更多人滿心傷痕。有媽媽憤怒地嘲笑着:「那個戴耀廷,學生都不看他的了。」她何曾忘記兒子在成長期又有幾回看她的?現在「沒有英雄的年代」都嫌老套了,網絡時代但求去中心化。惘然疑惑的日子,大家充滿不信任。陳健民老朋友港大教授陳祖為認為學生應「進退有時」的心底話,被人誤會是佔中三子為安排退場鋪路;陳健民回家備課,連自己都會心生恐懼,怕別人以為他全退。
香港人可能忘記了香港人如何成長。陳健民那一代,還不是我們熟悉的香港兒女?
八十年代初赤泥坪村瓦片屋頂下,一室書香,不少香港中文大學學生在那裏租屋共住。有些是學生會的人,有些是國是學會,有些是青年文學獎搞手。有時討論國家大事,有時唱李建復《歸去來兮》,熱情有理想,對來訪中學生友善。他們給後輩留下無限想像,這些人,將來到底會變成怎樣?
「當時讀社會學是很有理想的人,我不是那些鴛鴦蝴蝶派」。
「讀社會學也要結婚的,拍拖沒有大不了。」記者說。立法會外訪問,陳健民誠懇又半拘謹。再在電話傾談,記者詢問赤泥坪生活,他驚訝又驚喜,「那是很重要的一段生活,我們經常日以繼夜的討論人生、宗教、哲學,無所不談」。他與陳祖為及鄧偉棕等同學一起租住村屋,有時會請來老師開壇討論香港前途。大學四年班,風花亂墜的日子,男生們過着共產主義公社式生活,所有人的獎助學金,不論多少,都會上繳作買餸之用,間或有人要買一束花追女仔,可以事先申請撥款。
「這豈不要公諸於世?」記者問。
「我們根本就一起獻計,有時我負責畫一張卡,心聲字句,他自己寫」。
從樸實年華走到佔中的日子,當了律師的鄧偉棕是陳健民身邊死士;從來不沾社會運動的陳祖為,是一早就認定要當學者的英國牛津政治博士,寫了文章,論述普選有國際標準,普選有分真假,也寫過有關公民抗命真義。學聯五子為跟林鄭月娥等官員對話作準備時,這位港大政治與公共行政學系系主任負上重要的一分力,背後友情,與他辦公室內陳健民的那幀書法一樣無價。
曾與王維基瞓車底堵路
本來想好好享受讀書,追回在協同中學錯失的學習時光。從中大第二年加入學生會開始,陳健民總是身不由己。「領袖不是你想像般傑出,很多時候只是因為缺人、因為你比別人有承擔、因為你願意放下身邊事情」。他是80至81年的學生會外務秘書,王維基及何安達亦有參與。
甚麼人做甚麼事情,早有玄機。中大那些年,他眼中很聰明的王維基,看準群眾心理,把徐克新浪潮電影帶進學生會,代替疏離的愛國電影及社會批判電影,希望學生會與學生群眾拉近距離,當年證實是成功的學生會巿場學。「關鍵時刻,他會出現,跟着我們一起瞓在校長車底」。那一年,中大討論四改三,時任校長馬臨在行政樓開會後,被學生圍堵,王維基一眾瞓在校長車下堵路,陳健民在烽火台上主持,校長被擠退到台上,「他只講了一句話:我好肚餓,我要食飯。多高傲,學生都呆了」。
結果,陳健民那晚串連了幾百個宿生包括吳志森及黃洪包圍校長府,一時間府第狗吠聲起,哥兒們遞來一支紅色原子筆給陳健民,他憤筆直書一封給校長的信,遺憾中大四改三,捍衞中大博雅教育精神。之後,校長召見學生,但不是對話,而是當面逐一訓斥學生。「陳健民你有沒有話說?」馬臨問。「我無話說。」他回應。
「你入得他門口一定想對話,難道送上門讓人訓斥?」記者好奇社運先鋒為何不回敬大家長幾句。
「我不喜歡跟人糾纏,你有誠意就對話,我不喜歡跟人對罵」。校長不談判不和解,他就繼續在外面搞運動。83年畢業後,他與朱耀明參與推進發展東區醫院工作,扶助弱勢社群,協助精神病患者,後來考取獎學金,遠赴美國耶魯大學,先後修畢碩士與博士學位,主要研究公民社會與民主政治發展關係。
「重看以前中大學生會時候,你這一代與跟周永康這一代有何不同?」記者問。
「他比我們這代優秀,老實說,要我們去這樣辯論對話,我好懷疑自己當時有沒有這種能力」。
「為何他們可以這樣優秀?」
「旁邊很多人幫他們,教授及律師願意這樣投入一個運動裏面,當年我們學生運動哪有這麼多社會人士加入,社會根本好少大學生,沒有其他人,還沒有政黨,壓力團體剛起步,我們大學生是先鋒。今時今日學生走出來就看到光環,其實,背後很多人在側邊支持,(記者:他們是知道的。)希望啦。時代不同,社會各個界別參與形成一個運動,雖然是他們成就了這個運動,但他是踩着好多人肩膀的,我都希望他們明白」。
「你們那一代的決心與這一代的決心是不是有分別的?」記者問。
「可以這樣說,我堅定相信自己當時爭取是對的,一點不懷疑」。
「是,我們都相信,但我們一定會回家啊」。他笑了,回頭看,為甚麼我們要主動回家?陳祖為認為兩代人的土壤不同,難作比較,但現在的年輕人,經過97以後十多年,只看到一個沒有希望的dead end。
「那時是想着會回家回大學,但現在學生想不想回家呢?學生亦未必不想回家,但總是覺得,群眾不想回家,他們也不可隨便回家,但他們也不是不知道現實,你怎樣在短期內拿到公民提名呢?所以當日提出希望政府有時間表,但群眾可能不是這樣想的,我一定要拿到真普選才離開,那種決心與我們幾十年前真是有差別,這班年輕人經過好多刺激,有好多資訊,好determined,我們那時最多只覺得自己是個啟蒙人,我做不到,希望師弟做到。」陳健民說。
「你那時已經想着留給後面的人做?」
「你爭取不到有何法子呢?因為力量不大,社會上沒其他人和應」。
「那時候社會怎樣看你們的?」
「根本沒有理會你,寫一下文章了事,都在校園裏面,學生要走出社會搞運動並不多,差不多到86年,我們參與爭取88直選,學生所佔比例仍然很少」。李柱銘以大律師身份爭民主,盧龍光及朱耀明牧師結合公義與信仰的行為,都給他一個正面形象。當年馮檢基參選巿政局,助選經理是楊森,陳健民是義工,因有書法底子,不時負責寫橫額、掛橫額,「有一天見楊森在大坑東公共屋邨瞓在地上,好大震撼,當時認為大學講師好尊貴,好少人會瞓地。席地而睡,我們現在睡了28日(10月24日當天)了」。
戴耀廷夢裏 佔中沒人來
陳祖為認為佔中根本沒有發生過,但陳健民卻認為佔中已經融化在雨傘運動裏。戴耀廷曾經說過,他發了一個夢,夢裏佔中開始,卻一個人都沒有來。現實版是,很多人來了,但這裏是金鐘,而且,宣佈佔中以後,幾乎有三分二學生要離開,時間地點人物好像全部錯了。
「那感受是怎樣的?」
「當然好差、好沮喪。你們叫我們進來,一上台,群眾走,立即又叫我們下台」。
「你讀歷史都知道群眾是這樣的,如何親身面對?」他承認為當時不掌握群眾是一些甚麼人,匆忙的來,一上台,已經有學生圍着很不滿地說:「為何要讓佔中入來,你們有沒有問過我們?」
一場覺醒運動,原希望讓人明白非暴力公民抗命爭取真普選,但年輕小子早就明白了。「我們當然有要求,但是不是今次就能推翻人大常委決定?我們沒有想過有這麼大力量可以改變,我們只是累積累積,去到某一點可能有突破」。
「這樣又要累積30年?」
「我不知要累積多少時候」。南韓光州學生墓海令張文光寫了感人的文章,南非曼德拉等待20多年才等到一個願意與黑人和解的總統。陳健民已經辭退中大中國研究中心主任之職,再辭公民社會研究中心主任一職他看是早晚的事情。過去20年,他一直研究公民社會與民主發展關係,大陸裏面的民間組織,包括愛滋病、扶貧、人權都是研究對象,在96、97年是最早把公民社會概念帶入中國的組織,也成功跟中國著名大型慈善基金會建立關係,「我自己在裏面出版雜誌也被禁了,當然好多波折,中國是起起跌跌的,怎會沒有困難呢?」
中大中國研究中心的規模可與哈佛相關中心齊名,建立公民社會是發展民主基礎,正如陳祖為說,陳健民那種知不可為而為之不是虛浮冒進的,而是一步一步有計劃的。為了佔中理念,他放棄與犧牲的東西都是如此實在。
他與戴耀廷一直願意在運動裏擔當輔助角色,學生有時主動跟他們一起吃東西,轉頭見他們進入開會的地方又好像不太歡迎,早上說好了的,晚上又改變,近日關係進一步疏離。現在,他們也只能像新世代父母一樣,在孩子願意聽的時候才會進言。
尊重學生選擇,不想拖後腿,但不代表沒有計劃,陳健民說,「這一分鐘我都認為,你未去到被捕、上法庭,人們仍然不會理解公民抗命的理念,好多人還是覺得你在破壞法治。年輕人沒想過承受刑責,或者,只如革命,打war game,部份人還是認為他們做的是抵抗運動,不是公民抗命。公民抗命是你要做了一個平台又不摧毀法治,需要在法庭上承受刑責,所以在我們來說,整件事情還沒有完整。公義與法制,必須有一個平衡,若果破壞太大,就不是公民抗命了,長時間破壞,與革命有何分別呢?」,現在中央態度強硬,保一個梁振英,炒一個田大少,生殺之權明甚。陳健民坦承一直勸學生撤退,但在未商討出決定前,三子不會單獨行事。他分析運動最終結尾有四種可能。最美麗是民主化提委會,以新九組模式讓每一個員工在每一個界別投票,符合《基本法》。最不想見到是暴力收場,「放完催淚彈,向天開槍,呯呯呯,甚至射人,大家都不想見到,這樣雙輸得厲害,北京都輸了,不只是特區政府與香港巿民,六四整個運動的挫折,年輕人不再參與政治,只做生意,這是大家都想避免的」。另一種可能性就是在無法取得協議時,學生如太陽花一樣,不停留於佔領區域,而是把運動從廣場移到社區遍地開花。最後是和平被捕,「如果有3,000、5,000人,由他們抬我們兩天、三天,慢慢抬,你就產生道德力量」。
記者在馬鐵見過一個爸爸級中年男子,看到電視新聞播出學聯希望與中國總理李克強對話的要求,衝口而出:「黐線!」旁邊冰冷的鋼鐵座位,完全沒有回應,社會的情緒已經漲滿得令人無法不自言自語。
本來,看書寫字畫畫才是原始的陳健民,但要回歸平淡已經很難,看着不斷潰蝕的社會,他不能若無其事,也知道自己不會放下承擔。「多謝體諒支持,每一個人都想過安穩溫馨生活,但看刻下管治制度,必須有短暫的震盪,才有長遠的安穩。造成你們的不安,我也很不安」。這是他對家人、香港人的心底話。
一對夫妻,從佔領運動開始,一直為陳健民茹素,佑他平安。馬丁李柱銘不時來找三子,跪在地上與他們一起祈禱。在亂局裏,人的智慧很低,陳健民願意仰望上天,那管他早已無法馴服於固有基督教信仰範圍之內。人生,未到結局,還是那種走在路上的尋覓感覺。
記者:冼麗婷 攝影:謝榮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