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方敏生曾經是海邊長大的陽光女孩。父親方心讓早年用50萬元買下赤柱海灘道16號三層高別墅,裏面有15米長泳池,但六個兒女總是喜歡到海灘堆沙建城堡。誰人心情不好,誰人要生氣,父親一定可以在沙灘找到他們。
本來可以像一隻海龜,把頭、手與腳都縮在大殼裏,但方敏生偏偏要尋找屬於自己的天空與海洋。家族蔭庇,也是一生的背負。年少反叛努力避開父親建立的復康工作,人到中年,卻又回歸父親的影子裏。
在港大社會科學學院新辦公室訪問方敏生,她笑起來,嘴角綻放,毫不掩飾。「你笑得像四萬一些,還是Anson(堂姐陳方安生)笑得像四萬一些?」記者問。「當然是Anson。」又是咧嘴大笑。56歲依然眉目清秀,她當年是陳方安生的花女。
退下社會服務聯會總監一年了,方敏生現在仍然為香港紅十字會擔任國際服務委員會主席,也在法律改革委員會關注訂定最高工時的勞工法例,還協助復康會、社區組織協會和在港大兼任教席。

勇悍反叛 舍監中止宿位
港大簡約的辦公室裏,有一張古典味濃厚的英式綠色皮椅,特別搶眼。那是復康之父方心讓當年在聖保祿醫院當院長的椅子,另一張相同的,由姐姐擁有。她支持環保,一室綠色氣派。從呂大樂那邊拿來的一幅畫,綠色主調,是個飽滿的女人。一直纖纖瘦瘦的她,當年被同屆修讀社會學、後來研究香港文化的呂大樂起了一個低俗又親切的花名,「你知他叫我甚麼?他叫我肥婆生啊!」
港大肥婆生勇悍,在殖民學府裏反宿舍加租、反高桌晚宴(High Table Dinner)禮儀,最終被舍監中止宿位,與同學在西環租住板間房。她的一年級同學林鄭月娥,修讀社會工作課程一年後已轉讀經濟。
祖母高玉昆,因為丈夫抗日將軍方振武國內失蹤的陰影,希望兒孫盡量讀醫,不要揀法律,最好遠離政治。小孫女方敏生在英皇書院預科畢業之時,獲英美著名學府收錄,但她決意留港認識社會。醫生父親方心讓替當時正在外遊的她填報香港大學入學申請表,父女商議,選了比較新的社會科學系。
至1980年父親獲頒CBE勳爵時,港大畢業的小社工搬離赤柱大屋,住在九龍書院道堂哥方慶生家裏,每天乘小巴到白田邨徙置區當社區社會工作者。專攻房屋政策的她,曾經聯合全港居民組織反對加租,示威瞓街,當年算是激進鬥士。英國國會議員訪港,她找杜葉錫恩帶洋議員出巡貧窮的殖民房屋,爭取了改善安置區公廁及治安。
背後裏,前線社工跟行政、立法兩局非官守議員方心讓爸爸吃早餐,毋須預約。父女各司其職,一個從上影響權力核心,一個由下為基層充權,「若果他要到立法局開會,我不去門外示威啦」。富貴北斗星,在家族與社會都充滿個性,有人說她是小資產階級人道主義者。現在香港政治與民心再難有上下之分,只有橫向合作,她退休回歸大學,無非想借助學術研究數據分析,再發一力,希望在香港面對人口老化之時,聯合醫療與社工界推動政府實施極具人道文明概念的臨終政策。
「爸爸第二次中風後六年,開氣喉,吊着奶,沒有清醒過。因為卧床肺積水,每年來回瑪麗醫院幾次,過了幾年,家族裏醫生多,大家開始討論往後要不要搶救。爸爸每次重新插喉泵氣,可以自行呼吸,每次肺炎需用氧氣機,但每次身體都會變得更弱,每次家人都要經歷那個痛苦的決定。爸爸看似沒事,其實很辛苦,而辛苦的也不止他,每次在療養院叫救護車,一定去瑪麗,那裏人手不夠,媽媽要做抹身各樣事情。她今年92歲,五年前80多歲,(記者:她一定是捨不得的?)是。因為我爸爸是突然再中風,他沒準備,家人沒準備……」2003年方心讓第二度中風後昏迷六年辭世,女兒方敏生首次分享漫長而痛苦的六年。
「爸爸沒說過一句話……從去世五年到現在,說時間會淡忘,其實,是不會的」。方心讓離世,方家全族一時失去頭領,現在族中長老,除了方心讓太太葉孔瑳,還包括陳方安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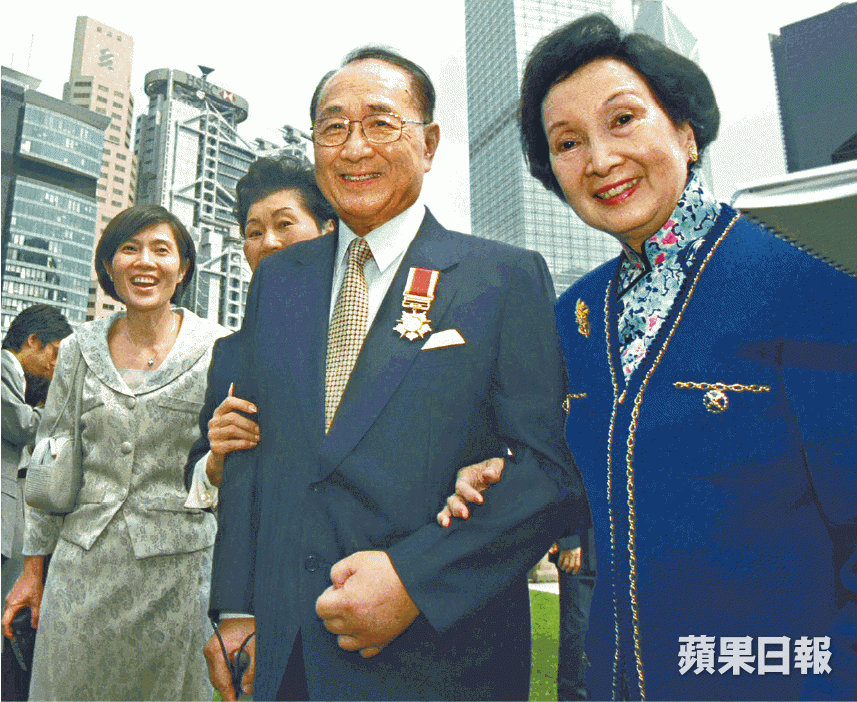
「搶救是不是真的最好?」
「我們兄弟姐妹親人眾多,搶不搶救當然由媽媽決定,經歷這麼多年,她都辛苦。這個決定也令全家焦慮,於是,也會想:我死時,要不要子女經歷這種事?我是不想的。很多後生一輩因為內疚沒有陪老人家多一點,出事後一定要搶救,但這是不是真的最好?」來自社福工作,她知道住老人院的好怕去醫院,「要重新驗血插喉,不能上廁所就插喉,有些少老人癡呆想落地的就要被綁着,每次入院的老人家回老人院又要重新學行」。
「難道就此決定死去?」記者說。
「不是。是要減低入醫院需要,強化入院照顧,尤其應讓老人選擇可以在其他地方過身」。臨終政策包括病者預設醫療指示,以及善終身心靈輔導。可是,春風秋雨,人會離開,人會傷心,人人經歷,為何要政府推行喪親服務?
「你問了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因為你珍惜生命,所以你要有尊嚴地度過人生最後階段。用錢衡量可能無價值,對政府來說,不在醫院離世,開支是少一些。但對人道主義的人來說,喪親後的創傷,是一世都不會撫平的」。
為社會做事,思想要比人先行。七十年代,方心讓建議讓傷殘人士可以使用地下鐵路,當時的財政司否決說:「讓傷殘人士使用集體運輸交通工具,倒不如用勞斯萊斯接載他們更化算。」今天,方敏生推動臨終政策亦不會容易,但英國與澳洲已先後於2008年及2012年推行,她說30年後每三人中有一個老人,港大社科院調查巿民對死亡及何謂好死的看法,大多數人都希望不要負累家人、要有尊嚴、不想痛苦,人想不想決定怎樣為自己畫上句號?
方心讓喜歡工作,息勞以後的光景,他沒時間想,還是不喜歡想?他自傳裏的日記引美國詩人Robert Frost所寫"I have promises to keep, and miles to go before I sleep."(我安睡以前,還有承諾要履行,還有一段路要走。)身處精采又重要的時刻,他自信已把上天賜予的潛能好好利用,懂得天份不難,願意勤懇利用天份不容易,全書最後一段也是關於工作。
"We are none of us the same people we were even a few years ago. We have come through some rough times, and we face some tough challenges ahead. We can only do what each of us can do, to the limit of our abilities, to try to leave the world just a little bit better than we found it. That is enough of a job for me. Time to get back to work."(時間過去,沒有人不會改變。我們經歷艱難時刻,還有挑戰在前頭。每一個人都應盡最大努力做自己能力所及的,好使世界變得更好一點。我一生使命夠了,而這一刻,又是埋首工作的時候。)
方心讓沒表達臨終意願,但他的心思,都寫在書裏,那一種工作態度,啟發強於吩咐。結果,方敏生繼續與老父生死呼應,五年裏,替他興建一度中斷的鹽田港老人院,下一步是喪親服務。
父母花一生去愛子女,或許,子女也要花父母一生的時間,才能聽明白他們,看明白他們,閱讀明白他們。1958年方敏生出生那天,過了午夜,媽媽羊膜穿了,爸爸親自駕車,八分鐘就把妻子送到瑪麗醫院。剛到產房,三女方敏生急不及待出世。方心讓形容,她是個滿身長毛的美麗寶寶。小天使脾氣不好,哭叫幾小時卻不流一滴眼淚。方爸爸被吵得失去耐性,警告要打屁股。小寶寶的眼睛告訴他:我不明白,也不相信,然後,又再哭叫。最終,父親使用了唯一一次體罰,雖然後悔,但小靈精真的沒有再哭。
六十年代,方家養六個兒女,用一輛九座位平治房車,方心讓每天袋着妻子給他準備好的50元零用錢,浩浩蕩蕩送孩子上學。孩子之中,方敏生是嚴謹的人,最恨遲到,偏偏每天早上出發時間,太多兄弟姐妹,太多懶洋洋的心,方敏生經常被氣得沮喪哭了。她眼淚流得多,大家的動作也被催快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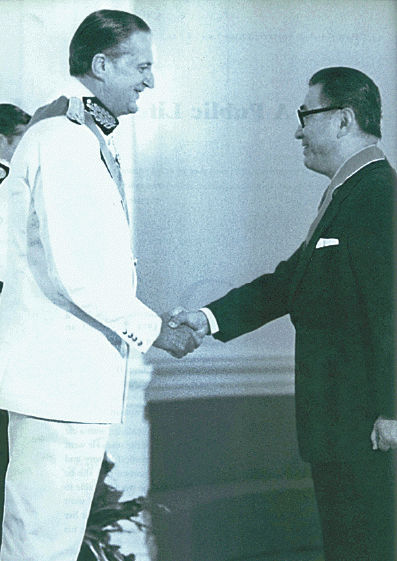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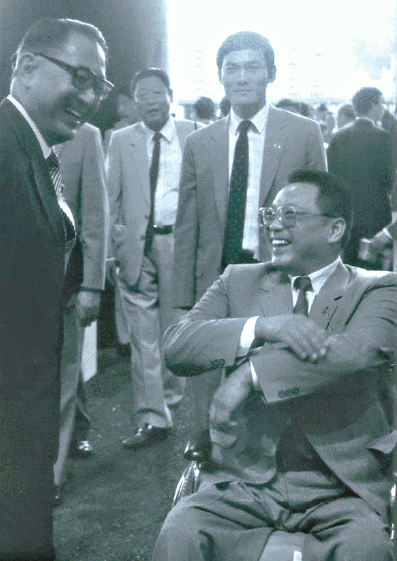
名醫面前 人人無分階級
赤柱大屋一住25年,注滿兒女溫馨歡笑,至羽翼豐滿一一飛走,空巢感覺,名醫心裏落寞,約1988年把別墅改建成大廈,方家每一戶只要付100萬港元建築費,就可以分一個單位。後來他也用香港資本在北京興建港澳中心,當年是得體酒店,是香港記者採訪回歸新聞必住必守之地。
頭腦靈活的名醫,女兒當進步小社工,他暗地欣賞,從不反枱。他用高層游說方式推動復康工作,知道打入馬會權力核心的重要,教陸軍會員用250元投注最終贏20多萬不過是小事,把協助殘疾人的復康約章從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帶到教宗約望保祿二世甚至中國領導人趙紫陽,這是一種眼界與魄力。
當年麥理浩懷孕五個月的女兒在英國撞車癱瘓,他諮詢方心讓意見,香港名醫面前,港督體會傷殘家屬的創痛。權操香港命運的鄧小平,兒子鄧樸方在文革洪流裏從北京大學三樓墮下癱瘓,八十年代鄧樸方主動求教方心讓推動全國殘疾復康服務,最終走上國際,互相帶動,兩人交情非淺。97回歸問題讓香港人忐忑不安之時,魯平跟方心讓見面,安排當時的布政司陳方安生秘密訪京,最終公務員順利過渡,中英回歸典禮上,方心讓感動盈淚。
香港半世紀都在政治裏翻騰,一個人,一個家族,跟一個國家的關係是很渺小的,重要的是時勢不是人。方心讓在英國曼徹斯特為麥理浩完成手術後開口,最終促成政府撥地興建麥理浩復康院,這一種時代過去了。回歸幾年,京官意氣,陳方安生離開公務員隊伍。現在政府推動政策要去拜票,社工爭取公義,寧願用手上一票選代表。以往,方敏生為免衝突,與在政府裏的陳方安生絕少接觸,但幾年前她出選社福界功能組,陳太為堂妹拉票,雖然最終落敗,但方敏生仍有跨界別包括利子厚及陳智思等商界協助推動社福。政治裏,人會跟着時代轉變,此時此刻,香港已經蛻變為大多數人希望直接參與管治的公民社會。
「你好似很強。」記者對方敏生說。
「當然不是。」她很大反應。
「但你也好似很弱。」她亦想反對。容易笑的,其實也都容易哭。心裏感應太多,在乎的也太多。在香港這片風雲地,政治經濟先行,搞社會工作,誰在乎?
自覺simple and naive
「讓我再選擇,我仍然會走這條路,社會工作讓我看到生命中甚麼才是重要。當人面對困難,甚麼令他回轉過來?甚麼令他熬過去?其實好簡單,就是人關心人的親情。我在貝魯特、薩拉熱窩、盧旺達跟當地人談,他們每天上街也不知道自己有沒有命回家。任何宗教、政治理想,都不是藉口去殘殺生命,為何到今天我仍為紅十字會服務,就是simple and naive呀,就是相信生命,生命的盡頭要有尊嚴。為何我現在要做臨終服務,因為生命帶給人好多生活意義與價值。社會工作讓我面對很多不開心的人和事,但在這裏面,你看到有些東西是larger than life」。
她緊接說起當年實習社工時的第一宗個案。一個吸毒少女,出賣身體換取金錢,「後生女,沒錢吸毒,你叫她做工廠?她說:我做一晚已經賺回來了。我問她為何戒毒,大可繼續打針、繼續做……她說:因為阿婆」。不知父母是誰,自小由外婆養大,最後心裏沉吟徘徊不去的,仍是年老的外婆。
「是她,不想她失望!」記者沉默着,讓方敏生一口氣把社工獨白說完,讓她好好重新進入30多年前的社會新形象-北斗星,一代少年人的理想。回到當下,這個時代這一刻,人間無數,方家三小姐,仍然浸在初心裏,一雙倔強眼睛泛着微微光影。「每個人的足迹不同,我們幫助他們哪裏跌倒,哪裏站起來。有些人沒有幸運如我,我們不可以選擇在哪裏起步,可是,在哪裏結尾可以選擇,所以,我就做臨終服務囉」。她又咧嘴泛起堂家姐Anson四萬式笑容。
最弱勢的呼喚,是最強大的力量,方家父女,一生都在強弱之間周旋。
今天,方敏生已搬回老爸赤柱舊地方居住,姑姐復康之母方心淑的女兒住同一大廈。當年賣汽水的沙灘叔叔已經不在了,浪花淘盡,問題不一定可以解決,但道理一定要想通。一天一天,一代一代,她還是喜歡浪花洗濯的感覺。
記者:冼麗婷 攝影:何柏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