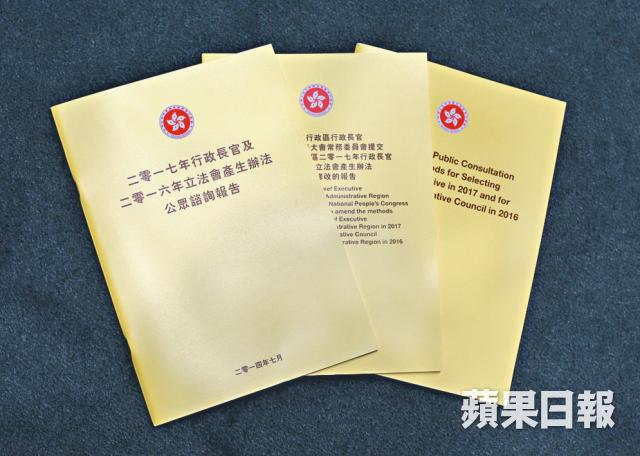
政改諮詢報告出爐,北大人愛聽的成了「主流意見」,數十萬港人投票力撐的公民提名卻被貶為「一些意見」,溫和方案無影無蹤。有份倡議以公民推薦代替公民提名的18學者之一方志恆,憂慮香港兩極化的政局更趨嚴重,溫和方案上場無從。惟盼各方,尤其當權者認知到,政改一旦拉倒,民主回歸論述即告崩潰,分離主義、甚至獨立意識勢必更強,管治香港只會越來越難。政改三人組月底與三子會面。退讓也退讓過,行前也行前了,是撕裂還是有商有量,還看政府如何回應主流民意。
記者:朱雋穎 雷子樂
方:方志恆,18學者方案倡議人之一、教育學院亞洲及政策研究學系助理教授
陳:陳健民,和平佔中發起人、中文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
記:《蘋果》記者
記:
其實我們最終有甚麼能「落到袋」?
方:
以學術研究角度看,這份報告的嚴謹程度令人質疑。很多時政府只是提出一個觀點,未有充份論據支持,成個報告予人感覺是有預設立場,再堆砌出來。唯一正面的是現階段未有肯定或否定任何方案,包括公民提名,仲可以有商討空間。
陳:
報告讓人感到政府與市民好大距離,好似自說自話,像尊子有幅漫畫,香港的「主流意見」原來跟中央意見這樣脗合,大概在大陸也不能做到如此脗合吧。唯一正面的是,若非70多萬人投票、51萬人上街,可能報告會變「主流同意支持篩選」。但現報告作為總結,不過是總結北京的意見。
方:
令人擔心的地方是,如果北京最終不接受公民提名,它又能給港人怎樣的替代方案呢?若北京願回應港人要有符合國際標準方案的訴求,就應該引導大家想,雖然沒有公民提名,但符合國際標準方案。但諮詢報告對中間方案的着墨,卻非常少。
我個人對政改達成共識感困難,尤其這次處理最核心的特首產生方法,一直北京給人的訊息是放出的空間很細,北京對回歸後香港,一直是要特首成為一個忠誠的代理人去管治香港。如劉兆佳言,北京視今次討論特首選舉,是政權的保衞戰。
我掙扎很久,要不要提出一個溫和方案,就是因為有感難以滿足北京要求的安全系數,同時回應到香港市民要有真正選擇的訴求。最終我們一班學者聚在一起提出方案,就是想就算機會少於百分之一,也盡知識分子的責任,去突破困局發出聲音,但由始至終我都是比較悲觀的。
陳:
整個問題是心魔未解決。中央根本未能接受,香港可以有個有真正競爭的普選。但就算由黨員去當特首,也不能確保是完全忠誠的執行者,薄熙來也是黨員,最後不也被打成反中央?中央其實心知肚明,沒有所謂百分百的安全系數,香港也不可能變成大陸,你要面對時代的挑戰去管理一個現代的社會。
社會好感受到兩極對抗、撕裂,這時候更是溫和方案出場的時候,社會中經過一段兩邊對壘的時間,很多人想找解決問題的方法。這才是溫和方案出場之時,而不是之前,若溫和方案是三個候選方案之一,相信也不能跑出的。若經全民投票輸了,反而沒了空間,但現在有了想像空間,應再多爭取。
方:
18學者方案的提出,在我心中從來是備用的方案,即只能在大家都願意讓步時,才可能發揮作用。北京就算不要公民提名,也讓一步接受香港人要有符合國際標準普選的訴求;民主派朋友也要考慮雖然沒有公民提名,但也無篩選的方案。只有雙方肯讓步,中間方案才可發揮作用。但現實環境卻不存在這樣的空間,只有對決,無人勸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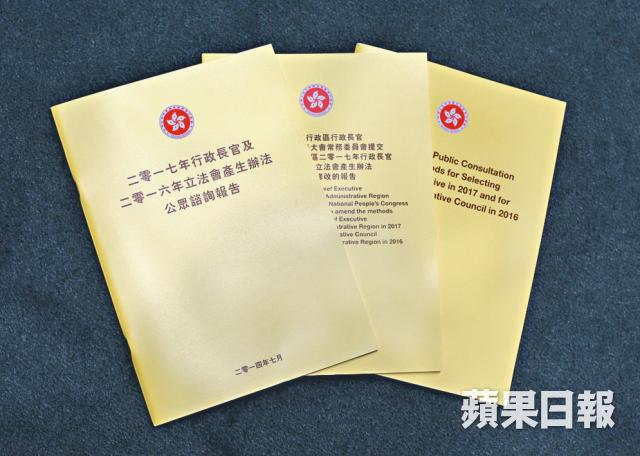
記:
一直以來,中央有讓步過嗎,我們見到的只有步步進逼,溫和方案有真有希望?
方:
我也感受不到,由我們4月發表方案到現在,都看不到中央和特區政府,願意考慮中間方案,或嘗試推動社會考慮中間方案。無論是政改諮詢期間及報告出爐,其實對中間方案的着墨都非常少。掌握權力的始終是中央政府及特區政府,他們有責任拉近各方距離達成共識,但連他們也不願做,社會上的中間力量又能發揮甚麼作用?作為知識分子,可做也做了的,是提出備用方案,現實的政治力量可以成為逃生門,但如果各方都不準備讓步,只想要決戰,也無人有力勸交呀。
陳:
民主派一直讓了很多步,泛民提出的政改方案是各式各樣都有,由最初不理會《基本法》,甚至提出全民制憲,至到接受提委會,再落去有公民推薦,甚至只是改革提委會,全都是泛民提出的,我見到泛民一直退後,給予選擇的空間,對面卻是要全票制、50%通過、四大界別,由中央到香港建制派,一直都無講得寬鬆點。
方:
我認為大家要評估政改拉倒的後果,惟有各方都考慮到一旦拉倒要付出的成本,才會去想出路。我的想像是,一旦2015年真普選無望,首先出現的是所有溫和民主派消失,2016年立會選舉會由進步民主派如社民連、人力等,取代民主黨、公民黨等溫和民主派,成為主流民主派。
更長遠而言,香港會出現分離主義的思潮。其實現時已看到,年輕人間的本土意識越趨增強,那其實是對一國兩制的不信任。80年代到現時,主流民主派的論述都是民主回歸,一國兩制下最終是能做到民主治港。正因如此,民主派才那麼守規矩,如不去挑戰《基本法》的權威,社會上反建制的行為也相當少。
一旦2015年政改拉倒,最大的問題就是整個民主回歸論述破產,當市民根本不相信、或北京講明一國兩制下,不會有真普選,年輕人會怎想?舊有民主派的政治論述基礎徹底破產後,一定出現分離主義思潮。年輕人未必是強烈地想要獨立,只是對北京與一國兩制不存好感。政改拉倒如駝背上最後一根稻草,把僅有的對一國兩制的希望都壓碎了。
我們要充份評估,政改拉倒會出現如此狀況,尤其北京。如果北京堅持零風險的篩選方案,就當準備面對以上問題吧。但若同意風險與代價太大,就要冷靜想一想,是否還有彎轉,是否可以中間方案作為出路。
記:
現時中央擺的姿態,似是想推到某個位,全面接管香港。承受後果的是港人,中央有甚麼後果要承受?
方:
有種講法「大亂後有大治」,政改拉倒、香港動盪、中央全面接管,但它到時又真的「管得掂」?香港不同內地,如果社會上,已有兩、三成市民堅定爭取民主香港,不可能全都拘捕、鎮壓,如果發展成獨立的思潮,當然中共維持政權穩定下,香港不可能獨立,但無疑雙方會形成一種強烈的拉扯狀態,你消滅不了我,我也消滅不了你,北京對此又有充份準備嗎?我很懷疑。
陳:
我相信會變的,民主黨有兩條路線的鬥爭:議會路線與街頭路線,以往不贊成議會路線的,就會離開議會走上街頭。政府的做法卻很儍,以為大家不講議會改革,可以乘虛而入,維持功能團體,卻不知大家是盡地一博2017年的特首選舉。大家深知2017年沒有,2020年也不會有。整個議會生態都會改變,再談進入議會去推動改革,只會淪為笑柄,無人可以接受一直去投票但一直輸。
記:
建制派一旦主導議會,就可以改議事規則,新界東北就是一例,再粗暴都敢。
陳:
所以就「掟嘢」囉,再不依任何議事規則,只有掟嘢與拉布是有意義。對,他們可以改很多規則,但另一邊也就完全不依,議會只是街頭的延伸,議會路線再無意義,主流泛民爭論多年的路線,一下子就大崩潰。政府以為可以偷偷笑不處理2016年立法會選舉,其實不知那是大崩潰的前夕。
記:
2005年25萬人上街,政改方案被否決,但07、08年政府又果真甚麼都不做,原地踏步,不會管治不了,也不會有暴動。
陳:
那是一個潰爛的過程,我們有良好的體制,不會一下子就collapse,但會decay。政府的政策不一定是壞的,但如果政府左手在扶貧,右手卻拿走我們的自由,那為何要配合你?我寧可甚麼也卡住,全面抵抗。這次佔中就是如此,就算爭取不到真普選,也會轉化成為一種長遠抵抗的力量。
再來會出現的是中產的cynicism(犬儒主義),覺得無可為,這心態一旦出現,一定有移民潮,只會顧自己與子女,對社會的參與度也大減。中產大概不會去搞分離主義,但會想定與家人過幾年就走囉。
而主管地方的官員,一旦有動亂也無好處。新疆有炸彈,主理地方的官員就大鑊,既壓不住也疏導不了,就是失職,對部門、仕途利益也有害。那就是習近平四、五年前要面對的,當時他還主理香港事務,香港一亂對他無好處。官員為了自己的部門利益,也必須為香港找出路。
方:
我覺得現時與05年的政治環境很不同,當時曾蔭權代董建華上台,仍有相當高的民望,市民對曾算是疑中留情,就算做不了政改,仍有期望。且爭拗點也全然不同,但今次北京卻要揭底牌,即其實是否真有民主治港?如果沒有,那種反彈跟以往的所有政改都不同,一定遠超以往的拉倒。
陳:
當然有人會問,大反彈哪又如何,都影響不到北京,的確是可能成了悲劇的結局。所以希望還是在港人身上,我們要盡力去做,做不到也形成抵抗的力量,去保住我們的核心價值。我們只能寄望在港人身上,不會犬儒到一個地步,全都潰爛。

後記:
訪問中,方志恆常把「悲觀」掛在口邊,對政府冷處理溫和方案,有掩不住的無力感。陳健民講得更多的是,若真想溫和方案被正視,就要多走一步,甚至幾步。他說起元旦躺在中環馬路上看着天空,覺得自己過去20年,過得實在太安逸,「躲在書房就能爭取民主?是全世界都沒有的事!」
多走一步,不只是聯署、寫文、提方案,「如果只係寫方案,我一日就可以寫10個出來」。爭取認受性才是重點,盡力在市民、港府與北京間,創造對話空間,「就算有方案,它也希望你有政治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