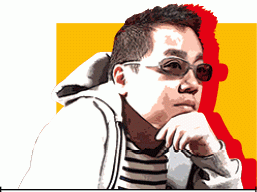每次出埠旅行超過一星期的話,我和太太坐在往目的地的飛機上,都會不約而同地提出類似的話題。
「我想,這次每天可以早點起來,抓個時間去跑一下步。」
「所有活動都能約在午飯後嗎?好不容易才能靜下來,我想在早上處理一下工作。」
其實連我自己都搞不懂,為甚麼每次明明說好是出埠休息,卻總要把工作帶到旅途上。回想起來,只要是不出埠的所謂正常工作日子裏,都總會被各項會議和雜事打亂了我的正常流程,例如早上醒來運動,然後處理一下雜務等事,就像在卡拉OK裏,不停有人進來插播一樣,結果一開始點下來的那堆歌,到埋單結賬時,還沒有唱到。

相反,一旦脫離日常的時空,少了會議和朋友的應酬,反而能把平日犧牲掉的項目,重新堅持下來,所以每次在去旅行的行李箱內,我都會帶上跑步鞋、運動衫褲,或泳褲泳鏡等運動裝備。當然也少不了大堆看了一半沒看完的書,和一些應該在數月前看完的劇本和文件。
或許有些人不贊成把工作帶到旅途上,認為這樣不是真正的放鬆。當然,有些人會選擇在一年裏不停工作,然後放上一個徹底的長假期。但我和太太都是那種天生驛馬星動的人,亦愛好不停往外跑,因此我們往外走的假期,基本上每一、兩個月就會有一次。由於父母沒發奮,我沒有成為富二代,雖然我不怪責他們,但在這樣頻密的假期中,經濟上還是會有點壓力。

完成了許多假期
於是我和太太想出了「半工假」,不完全停止辦公,但只拿一半時間來執行工作,例如平日是工作八小時,在假期裏就只抽三、四小時來處理工作,其餘時間便專心玩樂和休息。我們用這種形式完成了許多假期,不管是北海道滑雪,還是泰國潛水,甚至是跑往非洲。有了網絡和微訊等科技,工作自然順暢多了。當然,還要有工作上的可靠團隊,在我出外玩樂時,他們還是會守住公司的最前線。
我去年生日給自己許下了幾個願望,其中之一就是即使再忙,今年都要撥時間到紐約小住一下(當然還有別的幾項活動正努力計劃中,希望能在今年生日前達成)。本來是計劃住上一個月的,卻因為有幾個一早答應了的工作和講座,結果只得把此次美國之旅切開,先待十天紐約,然後飛回香港工作幾天,之後再飛回美國。
幸好坐長途機我沒有失眠的問題,因此沒太大困擾,加上有許多電影因為一直忙着沒時間進場觀看(當然有些是覺得不值得入戲院觀看啦),於是長途機成了惡補近期電影的一個場所。尤其我太太可以一連看上三、四部電影,所以每次當我從睡夢中醒來去洗手間的時候,其實她已在看另一部電影了。結果後來買回家的DVD,大部份她已看過,弄得每次把DVD放進影碟機前,都要思考良久,才能找到一部彼此都沒看過的電影。

像跟老朋友碰面
與東京的六本木森美術館一樣,紐約的MoMA是我每次到紐約的必要朝聖之地。每次我都不會仔細研究MoMA有甚麼新展覽,因為即使沒甚麼有趣的東西,或可能有一半作品我已看過,也無妨,隨便進去閒逛一下,就像跟老朋友碰面,看看他最近可好一樣。
MoMA給我印象最深的,還是莫奈(Claude Monet)的睡蓮,它總會把你的思緒拉進去,是張值得盯着很久的作品。雖是看着畫,卻是在重新檢視自己,這是個需要寧靜的時刻。可諷刺的,在莫奈的畫作前,都總是充滿着各式各樣的人潮,喧鬧得像個市集。
有時候我和朋友說,莫奈是需要靜下來觀看的,大家都會笑我瘋癲,說在MoMA博物館中,怎可能找到一個能夠靜下來的時間。其實只要有恒心,在那沙發上坐下來,向着莫奈,加上一點運氣,偶爾還是會出現一個莫名其妙的時刻。所有遊客突然瞬間像潮退一般,離開展館,就像海嘯即將到來之前,岸邊的海水突然被抽回大海去,那是種很奇怪的感覺,只要夠幸運,那一刻坐在沙發上,就能享受到整個房子中的寧靜,你會發現睡蓮好像只在跟你溝通一樣。當然,這個時刻,你要在此,才會有機會碰到,就像你每年五月到美國中部,也不一定能見到龍捲風,但只要去得夠多,或多或少也有機會碰上。
就正如海嘯的先兆一樣,人潮突然退去,也意味着有另一個更洶湧的人潮即將到來。在享受過這一分半刻之後,下次人潮來到之前,就默默起身,繼續去找尋別的老朋友。
聽到在紐約的朋友說,布魯克林大橋(Brooklyn Bridge)對面有個過百年的造糖廠結業,有藝術家在那裏用糖做了個巨型雕塑,最近剛開始展覽,每星期只展示數天,因為糖會溶掉,一旦溶掉後展覽就會結束。有幸碰上,這幾天得找機會去逛一下。
紐約就有這樣的好處,隨便亂逛,都會碰到許多驚喜。

【我來了,是要叫人得過癮】
撰文:彭浩翔
祖籍番禺,生於觀塘。集作家、編劇、導演、製片人、演員及藝術家於一身之處女座。尚且幹活,只為供養其網購血拼及極限運動。
本欄逢周六刊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