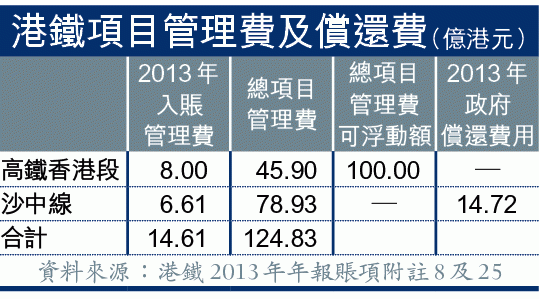
上周講到港鐵成立前,分別是九鐵及地鐵兩個作為業主的「獨立王國」。兩鐵合併後,政府並未專業地監管項目的進展及成本的控制,導致超時超支。今次續分析項目超時超支的結構性問題。
港鐵成立前軌道項目由地鐵及九鐵兩家政府擁有的全資附屬公司去負責,政府是最終業主,但兩鐵作為全資附屬公司既是業主、亦是管理人,因此他們在董事會下需保護其機構內的資產、資本、控制成本、完工時間表及質量,並向政府及立法會問責。
港鐵是單一壟斷者
港鐵於地鐵及九鐵合併後成為軌道項目的單一壟斷者,接納新項目時不再有競爭對手,加上港鐵已是一家上市公司,其對項目的取捨及談判條件的能力大增,而政府的直接項目監管能力低(因為項目一向依賴兩鐵去做),項目的實行最終演變成:
(1)政府代替港鐵作為業主,主要出資者及超時超支等風險的直接承擔者。
(2)港鐵透過多個與政府簽署的 「委託協議」下擔任管理人,不再做業主,不需出資,但收取巨額管理及償還費用(見表)及項目完工後有經營權。
以上新安排令港鐵在無資金壓力、無風險及業主沒有足夠資源及專業知識去監督的情況下賺取費用。最致命的風險因素是項目施工前應做的設計及勘察工作不足,對施工難度不了解,以致難以估算成本上限,最終把整個項目送上超時超支的路。內行人知道這種邊做邊設計 (design and build) 的方法帶來的不確定性是最大的,而這種新安排下要承擔風險的是業主。
另一角度看,這種邊做邊設計安排對非業主的經理人,顧問及承建商往往是夢寐以求的生財之道,因為設計的問題在施工後可不停地發生或被產生而創造額外開單的情況而構成超支,而埋單的則是政府及納稅人。
超時超支控制與業主及經理人的辦事能力、監察能力及着緊性有直接關係。從「驚訝」及「意外」的回應角度看,我們的業主並沒有適時地知情,亦即是政府的知情制度佈局欠奉。從港鐵高層向傳媒的報道來說亦不見得到有高度適時性及專業性的解釋。細閱2013年港鐵年報的企業管治報告內的風險篇時,亦看不到港鐵就其擔任經理人的高鐵及沙中線項目的有關風險有任何披露,同時亦沒有就其賺取管理費應提供有關服務如未達標或有疏忽時或會產生的風險及或有的法律責任作披露。亦極有可能在港鐵及政府兩方簽署的委託協議中所有項目產生的風險都歸政府承擔或埋單,這點因為沒有委託協議的細節而未能確定。這些都是疑問!
另一角度看,亦因主要問責官員:運房局局長、財庫局局長及運輸署署長及港鐵主席及行政總裁等高管都坐在同一個港鐵董事會,便產生了另一個大問號:港鐵的企業管治、風險管理及內部監控系統的設計有沒有滿足向業主、管理層及整個董事會的知情權而影響其監控行動及問責性。再往前看如果這個「撻Q」的情況不改善的話,往後的項目工程進展可能繼續「撻Q」及超時超支。為甚麼?因為眼前見到流露出來的問題只涉及土建工程,往後待建的還有供電、訊號系統及車種等機電科的問題。我們亦知道軌道系統常發生的問題不是土建,而是源自供電纜、訊號及機器等問題。以上種種其他項目未發生的問題可能更考功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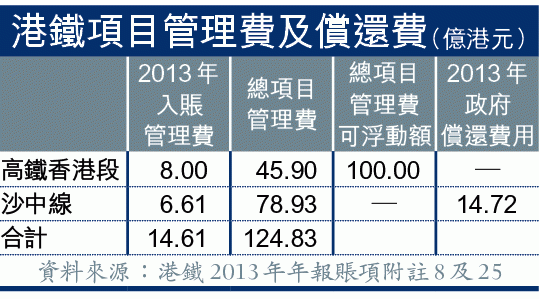
要有果斷止血行動
因此,我建議行政長官應考慮行使賦予他的權力去:(1)專項命令審計署去做一個跨境高鐵及沙中線項目的衡工量值審計;(2)專項命令申訴專員署去就跨境高鐵及沙中線項目去做一個就項目的問責及是否有行政失當的調查,對象應包括但不限於運房局、運輸署、路政署及港鐵公司。律政處亦應看看一眾委託協議有沒有違約的情況;(3)就上述(1)及(2)的結論組織一個專門處理大型基建項目的局(大基局)來監察及控制項目成本,完工時間表及項目經理人的工作表現。我會建議這個(大基局)的工作範圍應包括港珠澳大橋及第三條跑道與原計劃的超時超支分析及監控。
我亦認為上述問題不應透過一個立法會特權專責委員會去調查,因為姑勿論調查的結果是怎樣,補救工作仍需政府去負責實行,所以倒不如一步到位,讓行政長官去行使他的特權去直接解決問題。
問題的聚焦點是業主及管理者的身份由同一機構一拆為二。本來用政府撥的老本去發展新項目的兩鐵會把資本及固定資產投資看管好,問題出在港鐵今天只是無風險地去賺取管理費及使他人的錢的經理人。
2015、2016及2017都是選舉年,政治噪音將增加及陸續有來。因此,調查提供補救辦法及推行補救行動時間不多,希望我們的問責官員敢擔當及果斷地去處理已醞釀多年及已在腐爛的生果樹!
我亦想說的是與其港鐵公司在各項委託協議下的收費會達200億元的話,政府可考慮把港鐵公司私有化,去解決「使他人錢」的企業及公眾管治的典型 Agency問題,省卻一筆管理費。以上的數據並未包括港鐵在上述項目可賺取的土地上蓋發展利潤。
周光暉
mailto:[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