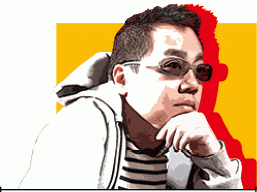這幾天在內地忙着我的新片《香港仔》之訪問,剛巧碰上香港電影金像獎選舉,因此不少傳媒來到時,都會第一時間追問我,如何看《一代宗師》在14項提名下拿了12項獎項這事情。
說來奇怪,大家都提出了一個莫名其妙的方向,就是《一代宗師》拿下了12項獎項,一些傳媒和網上影評人都以此大做文章,指這是香港電影衰落之現象。但我認為這論調有個邏輯上的問題,為甚麼《一代宗師》拿下12項獎項,就是代表了港產片衰落呢?
首先,不論《一代宗師》有多少個團隊,它仍是一部港產片,因為香港電影金像獎已經為港產片設下了一個定義。根據香港電影金像獎的評選規則,只要滿足了以下三項之其中二項,就是港產片。
1.導演(最少一位)是持有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證的香港居民;
2.出品公司(最少一間)是香港合法註冊公司;
3.最少有六個工作項目的工作人員為持有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證的香港居民,每個工作項目只計算一位,依據15個獎項計算,包括:監製、編劇、男主角、女主角、男配角、女配角、攝影、動作設計、美術指導、服裝造型、剪接、原創電影音樂、原創電影歌曲、音響效果及視覺效果。(若「原創電影歌曲」的作曲、填詞及主唱多於一位香港工作人員,亦只會計算其中一位。)
因此,毫無疑問,《一代宗師》就是港產片。
高水平華語電影
此外,又有一些莫名其妙的網絡評論人,說《一代宗師》有許多內地人參與了製作,所以它不是一部純港片,因此這電影的成功,不代表純港片的成功。這個更讓我有點不知所措,一個地域的電影,從來都不代表只有這個地域的人參與,王家衛在拍《一代宗師》前,他的電影都已經有了國際化的團隊,就像《春光乍洩》到阿根廷取景,也用上了不少當地的工作人員,但它仍然是香港電影,那為甚麼只要加進了內地團隊,就突然一口咬定,這個電影已經不算是香港電影?
又有部份觀點指出,這是合拍片的勝利,純港片的沒落。但這個觀點也有問題,因為在競選名單中,除了《狂舞派》是純港片外,其他的電影統統都是合拍片,那港片的沒落這個論點,是立足於哪裏呢?
也有人說因為沒有幾個電影,選無可選。但我個人認為,以《一代宗師》之整體質素,不論是拍攝還是其他技術部份,其實不只是港產片,甚至是整個華語電影裏,都是相當高水平的。我是香港電影工業之一分子,我也有代表我的屬會,包括導演會、編劇會去投票,我是毫無疑問地投給了《一代宗師》,因為它確實精采。也有人質疑這種業界投票,會出現人情票的現象,無可否認,每種選舉都有機會出現這種情況,奧斯卡也是走業界屬會投票制的。當然,像康城影展和台灣金馬獎那樣走專業評審路線的,有些時候可能會選出一些不太貼近大眾、但藝術成就高的電影,但也不代表內裏就沒有人情的因素在內。
克服自行配票
許多時候,投票人都難以避免在投票的時候,會出現內心配票的現象,好像要是在其中一欄填了某電影,到填下一欄時,他就會想︰呀!這個已經給了它,是不是要把另外的機會留給別人呢?不能全都選一部電影啊!然後他就會自行配票。
《一代宗師》能讓每位投票人克服到這種內心現象,而成功得到大家的支持,一定程度上,就是因為它每個部門都能達致一個非常傑出的水平。當然,這得用龐大的資源和多年時間去換回來的,也不是每個投資方或導演都能得到的優勢,這是王家衛導演個人的能力和幸運。但坦白說,在投票時,我們都應該獨立去考慮每個獎項去作為標準,而不是以甚麼生態平衡或分豬肉的概念,所以我認為《一代宗師》拿下12項獎項,真的一點問題也沒有。
當然,這種討論到最後,都會得到一個結論,就是往地域方向走,說甚麼純港片,目前只剩下粗口、裸露和情色,說得香港人好像特別低俗一樣。每次聽到這種論調,我都不知道從何說起,因為不是生氣,而是覺得幼稚,為甚麼大家都是成年人,還要去討論這種無聊見解?
首先,我不認為髒話和裸露色情,有低俗到甚麼地步,這是生活的一部份,該出現的時候就會出現,也是全球都會出現的狀態,正如馬田史高西斯(Martin Scorsese)的《無間道風雲》(The Departed)一樣,再大的明星也不會迴避粗口,因為這只是反映着波士頓低下層生活的情況,而審查當局也不會跳出來,說甚麼會傷害了波士頓人民的感情之弱智論調。
保着說故事的權利
關於情色和裸露的影評,大家都說得好像只有香港人會這樣,其實我也不打算要為港產片辯護甚麼,因為這種討論實在已經去到很小學雞和無聊的地步。我認為喜歡情色,不是華人的特色,而是地球的共通性,每個地方也有這樣的事情,只是許多西方國家,都已有完整的規範,例如電影分級制,甚麼事情可以做,甚麼事情不可以做,都規管得清清楚楚。可是目前我國電影沒有分級制度,於是所有成年觀眾,就只好被迫去看小孩都能看的電影。那內地人特別不喜歡情色電影嗎?不見得,《3D肉蒲團》和沒刪剪版的《色,戒》,不是讓大堆內地自由行旅客爭相湧到香港,走入戲院觀看嗎?這沒有高級低級之分,只是食色性也,人類的共通性而已。
由於內地制度的不完善,讓髒話、裸露和情色都不能呈現到大銀幕,於是內地網絡上也出現了大堆鹽花的微電影(好吧,我是有搜尋了一些,但主要是為了這篇文章的資料搜集)。可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這幾年我一面拍着合拍片,偶爾想到一些奇怪瘋癲的點子,因為知道無法通過審查,所以就直接拍成純港片,於是有些立心不良的傳媒,就把我定性為在合拍片制度中的投機分子。可是我不明白,為甚麼那些影評人或傳媒會有一種扭曲的概念,認為一個在香港出生長大的人,有天離開香港跑到別的地方拍戲,就成了一個投機。但不見得所有在廈門長大的電影人,都只會一直留在廈門拍戲,而不能到別的地方去拍攝。這樣把每個人釘死在某個地域上,到底是多扭曲的一種思想呢?但反過來說,我也從沒堅持像《低俗喜劇》一樣的電影,只是拍給香港人看,或只會在香港拍攝和放映,要是你問我,我更希望電影能放到世界各個不同的角落播映(實際上它在歐洲、澳紐、美加都有公映,只是沒有通過審查而無法在中國內地上映而已)。
我們都希望每部電影能接觸到最多的觀眾,在最多的電影院裏播放,這個當然是大前提,但同時間,創作人也希望自由自在地說他那一刻想說的故事,這兩點是可以平衡的,只要你明白你的市場,不是每一部電影都要賣上數億(可能有些老闆不同意),而是要如何在每個製作中不虧本的情況下,盡可能去說出你內心想說的故事,這才是我們作為創作人的最大要點。想着不虧本,不是因為銅臭,而是為了走更遠的路,能夠保障到投資回收,就意味着你有下一個說故事的權利和能力,只要保住這個能力,其他所有的詆毀或讚譽都不再重要,因為站在台上說故事的,是你,不是他們。

【我來了,是要叫人得過癮】
撰文:彭浩翔
祖籍番禺,生於觀塘。集作家、編劇、導演、製片人、演員及藝術家於一身之處女座。尚且幹活,只為供養其網購血拼及極限運動。
本欄逢周六刊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