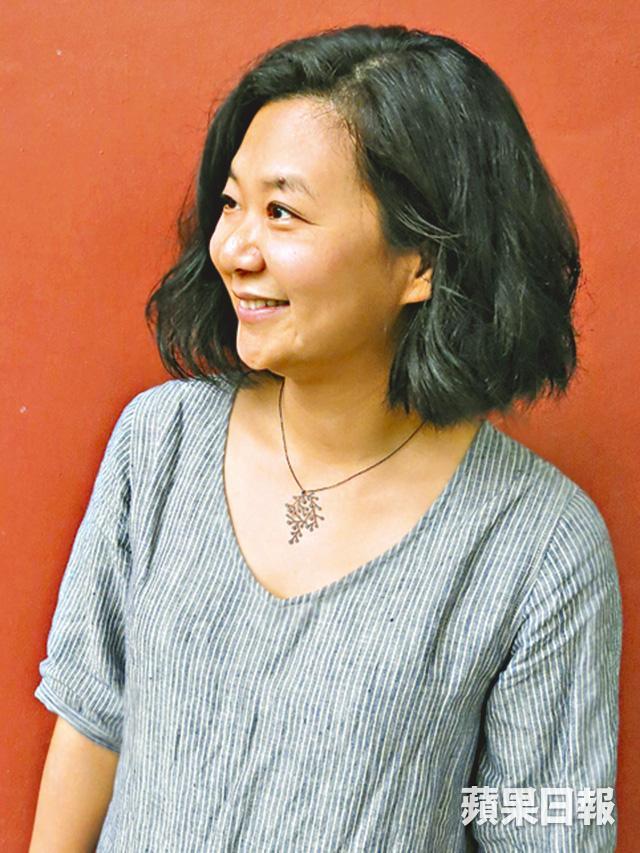第一次讀到江瓊珠,是九十年代尾。初進雜誌社,上司放下一叠泛黃的報紙,大半都是江瓊珠在80年代撰寫的人物故事:「去查一下,這些人現在怎樣了?」一看就着迷,大人物最難也許是約訪問,無論寫甚麼讀者都追看,小人物要寫得更好,而且一失分寸便淪為濫情煽情。江瓊珠筆下的人們,縱使微卑,生命的厚度卻令人入心入肺,難怪讀者(包括上司)會念念不忘。
「我初做記者,做不到大嘢,一去到現場就不知道被人逼咗去邊,好早就被點做花邊新聞,寫那些街邊阿嬸阿伯。執垃圾的阿婆,我好早就寫。」江瓊珠直言。十年在主流傳媒打游擊,寫得幾多得幾多,香港回歸,她毅然開出版社「進一步」:「出版社和社會的關係,面向大一點。」《從米蘭到鑽石山:甘仔故事》、《我看不見,但……》,追看江瓊珠一本本人物傳記,未幾,遊記多過訪問,《咖啡、茶或一本遊記》和《路上見》,通透的眼睛,依舊從一粒砂看到世界。再接着,是紀錄片,就像下周一在中大首映的《我們總是讀西西》。

由西西童年說起
西西低調不接受訪問,江瓊珠選了西西的文字,再找來詩人、電影導演、酒吧老闆……把西西由童年一直念到葉子落下。又請藝術家用不同手法,呈現文字的意境。「西西看到一定好開心!」她半呃半哄,兩年才等到各人交來作品,可幸每一段影像,都那樣用心,真誠而恭敬。「我十年前第一次拍紀錄片《姊姊妹妹和紫藤》,居然拍到,嘩,咁可以拍西西!」她理直氣壯:「無得傾,西西輩份咁高,當然要拍!」誰不讀西西?姐妹們把《哀悼乳房》收入書櫃,社運分子抱着《我城》去靜坐,而江瓊珠最驚艷的,是《縫熊志》。「那些熊仔好勁!西西右手不靈光,還能縫出這樣多的生命和喜悅,角色好難設計,水滸傳九紋龍熊喎!悲壯如荊軻熊,但一件白袍就表達出來。西西學問很深,書寫空間極多層次。」
片中被訪者,各自說出與西西的交往,文思慧教授和西西走過同一條樓梯,去上牟宗三先生的哲學課;鄧小樺在西西住過的土瓜灣長大,廖偉棠收到西西送給他女兒的布偶……好學的西西、幽默的西西、溫情的西西……在紀錄片的格子裏跳飛機。看畢,心暖暖的,大家的掌聲不會太遲,真好。
可是,若由江瓊珠去寫西西,意境相信更高。為甚麼不寫呢?「我有寫!」她睜眼。原來這些年江瓊珠受聘為許多志願機構,寫了大量人物訪問:老人、病人、農夫……只是這些書,不是印數很少,就是根本不賣。「從來都不期望更多人看到我的書,要看到就看到,看不到的就看不到。」她說,我的表情越錯愕,她越是不在乎,想了一會,才答允借我她的著作《斜路上,瑪利灣:一間女童院舍的四十年》。由女童到修女,跌跌撞撞的女子們,交織出香港的動盪和折騰,簡直不捨得讀完。
不是為了紀錄片首播,江瓊珠不會接受訪問吧。看她的紀錄片是要記下日期的,之前的作品《她的反世貿》、《Why 馬國明?Why Benjamin?》、《菜園花花之愈抗爭愈美麗》、《張先生搞出版,持續靠左》等,只有放映會,沒出DVD,要看到,就要去看。
Profile
資深記者,著作包括《剩食》、《有米》、《死在香港》等,相信垃圾都是放錯位置的資源。(mailto:[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