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媽,我真的能碰碰這些雪嗎?」一位居住在福島縣的小女孩問道,母親點頭微笑。一群小朋友一大清早隨義工團體從福島到低輻射區的雪地。
雪地白茫茫一片,小朋友手裏拿麵包糠在跑,一群灰鴨蹣跚地趕上,重重包圍了孩子們呱呱叫。另外有些孩子戰戰兢兢地拿着滑雪板跑到高處滑下來。一瞬間,緊繃的臉孔放鬆了,久違了的笑臉被攝入照相機。
災難已過了三年,然而有賴一批國內國外的義工團體,帶領這群可愛無辜的小孩到本土低輻射區,甚至到國外旅遊,讓他們依然能體驗那些在福島裏「能看不能碰」的花草海洋,他們正在努力過活。有志願者說:「我們最害怕的不是輻射,而是被遺忘。我們需要幫助和支持。」

這批小孩,一大清早隨「移動育兒計劃」來到沼尻低輻射區的雪地,父母們一致地在旁觀看,生怕錯過每一張笑臉。「有一位母親在3.11地震後得了抑鬱症,那天她看到孩子盡情玩樂,三年來她第一次開懷大笑。」移動育兒計劃創辦人上國料龍太憶述。他於2011年7月成立移動育兒計劃,「從郡山市向西出發,只要30分鐘的路程,就能到達低輻射區,如田舍町和湖南町,每年輻射含量不超過一毫希,遠低於國家標準。可讓小朋友在那裏接觸大自然。」身為人父的上國料龍太回想三年前地震那刻他身處東京,當時六神無主,只想着同在東京的兒子,後來得知妻兒平安才釋懷。
「移動育兒計劃」中文網站: http://idouhoiku.com/cn/

短住三個月 天天大海暢泳
「媽媽,那我身在千葉的朋友每天吸入輻射,會很危險嗎?」小小年紀的Anna在母親Yumi懷裏哭訴。日本發生大地震後,Yumi為免小孩暴露在輻射中,數月後舉家移民夏威夷。

回想起三年前要離開日本,Anna萬般不願。「她擔心身在日本的朋友,我告訴她,這就是我成立Fukushima Kids Hawaii的原因。」Yumi說。他們每年會舉辦各類型的活動,讓小朋友、青年和家長接觸海洋、舉行戶外音樂會等活動,甚至提供住宿讓災區父母在夏威夷短暫生活。Yumi說:「當我牽着3歲Rio的小手跳進海裏,她說在福島時天天看海,但卻不能游泳,現在終於能在海裏玩水,她都不知道自己為何會流淚。」
籌款日漸困難
在facebook尋找服務福島災區的志願團體,有不少經已「荒廢」。遠在夏威夷籌措經費難上加難。「在國外,大家誤以為日本災難經已完結,只以為我們貪得無厭。」因為他們的努力,美國人親身接觸福島小朋友,外界漸漸明白災區的人依然活在水深火熱中,他們在美國的合作夥伴Hawaii Montessori Schools還願意全費資助福島學生的學費。然而把福島孩子們帶過去也要面對一項挑戰,「福島有些人會妒忌他們能去美國,所以他們都很低調,我們的推廣工作就更難了。」
去年冬夏兩季該機構各帶了10個孩子到夏威夷度假三個月。機構會資助一萬美元的生活費給每一個孩子,由於資源有限,Yumi丈夫雖是全職員工,但不受薪。他們每個周末都舉行派對、音樂會和義賣募捐。「最難過就是孩子們離開的時候。我問他們的夢想是甚麼?他們異口同聲地回答:『我想再游泳。』」大地震發生前,我們都不知道游泳原來可以是一個難以實現的夢想。「因此,我們的目標是,把福島30萬個小朋友通通帶到夏威夷。」
Fukushima kids Hawaii網頁: http://fukushimakidshp.blogspot.hk/?m=1

訪復興城市 拋開長袖衫褲
在剛過去的12月,本是台灣黑熊保育研究者的羅美音、師妹陳蕙萍、日籍台灣人小宮有紀子,以及前僑務委員會委員長張富美博士,用她們的積蓄及六個機構的贊助,邀請16位未曾出過國的日本小六學生,到屏東與高雄參加「台灣關懷福島兒童計劃──冬之太陽旅行」。

2009年,台灣屏東縣發生八八水災,今日重建,還發展太陽能及養水種電計劃等,開發可再生能源。張富美博士:「希望日本的小朋友們,知道林邊也經歷過災害,希望他們能勇敢站起來,不要被打倒。」
12月的福島正下雪,氣溫零下5度。剛抵埗的孩子們很害羞,來到高雄廿多度的炎熱天氣,終於可以穿短袖衫,在陽光下盡情地跑!有一個愛踢球的小朋友大虎,災難後就很少踢球了,見到草地特別開心。孩子們放心地在這裏深呼吸,一時要踩單車,一時要去海邊撲浪。他們第一次摸蜆仔、在石灘釣螃蟹;還到2009年重建的原住民小學學習射箭,最開心竟可以夜宿屏東海生館,睡在大水缸的旁邊,興奮死了。台灣寄住家庭很熱情,帶他們逛夜市,打長途電話給日本的父母報平安。電話那頭的張富美一口氣地說得比孩子們還開心:「每朝早餐都未吃,孩子們已在屋外四處跑。我只能看,都追不上了。哈哈哈!」
張富美:「福島上能搬的人都搬走了。其中一所小學甚至只剩下一名學生。留下的,都是沒錢、沒能力離開的。」福島的孩子今日都帶隨身帶着輻射偵測器,大熱天時都要穿長袖衣服遮蓋皮膚,在戶外逗留不能超過一小時,操場上的泥土仍有核反應,政府說「沒問題」,也沒地方可移走。
2012年,香港「反核之眾」也辦過一個讓福島孩子來港的旅行團。在《不要再有下一個福島》電影放映會上,大家問:「我們可以做甚麼?」現場一片寂靜,張富美的答案卻一樣無奈:「我們沒甚麼可為他們做了。目前我們的生活,都是向未來世代預借的。大家保持對福島,以及核災的關注,避免災難再發生,已是最大的幫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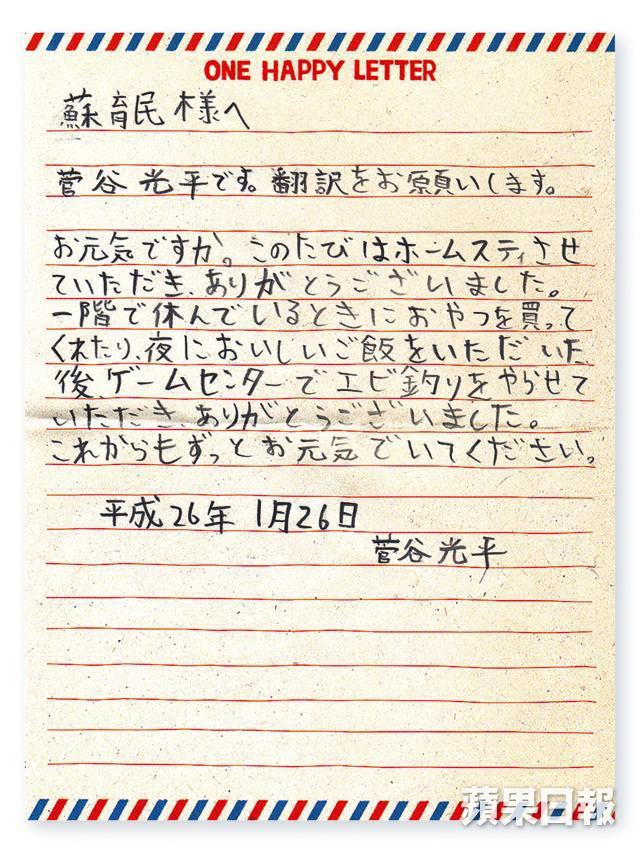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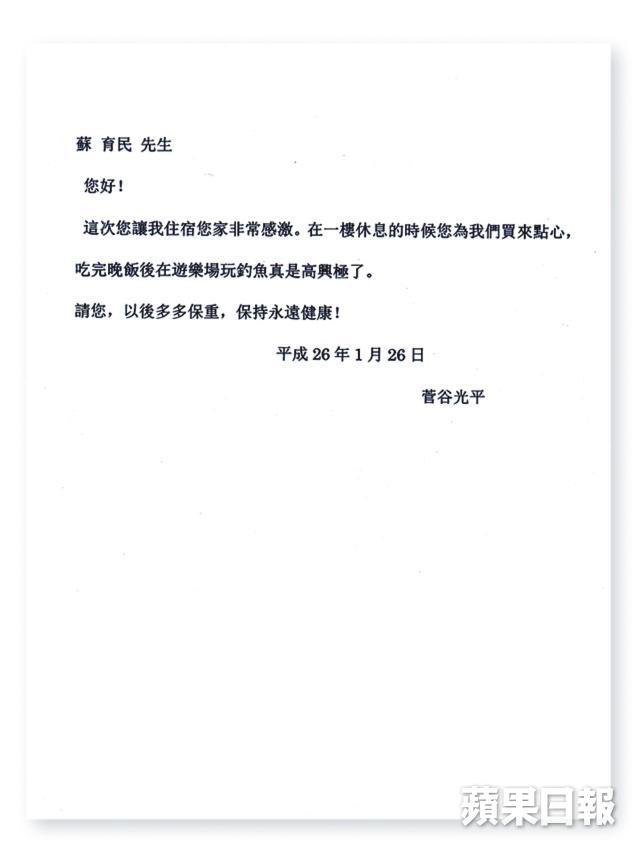
名建築師打造暫借窩
災難後,最逼切的是災民的住屋問題。世界著名日本建築師坂茂,設計過2000年德國漢諾威萬國博覽會日本館、紐約游牧博物館及法國龐畢度中心新館等。他組織了一個災害支援企劃部,利用紙建材輕巧、能迅速組裝的特質,設計了許多漂亮、結實又防水的紙建築,還有莊嚴神聖的紙教堂及臨時學校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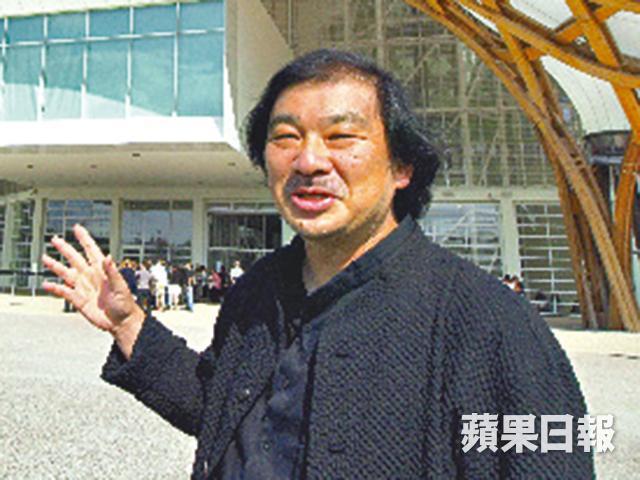
除坂茂外,建築大師伊東豊雄與妹島和世、隈研吾、內藤廣等組成「歸心之會」,重新思考日本建築。2011年,伊東在仙台設計了30人即可建成的臨時屋。2012年他以"Home-for-All"為主題,拿下第13屆威尼斯建築雙年展金獅獎。而去年妹島和世更與年輕建築師趙揚合作,在宮城縣氣沼市設計了一座可遮風擋雨的活動屋,成為當地漁民回家的燈塔。

災後通訊衍生LINE
除WhatsApp之外,不少人也有用Line,原來那些兔兔、饅頭人,也始於3.11。地震後,不少通訊網絡中斷,要在通訊微弱,不知餘震何時再臨的時間裏,迅速以精簡訊息聯絡家人、好友變得更重要。當時南韓第一大搜尋器公司NHN位於日本的子公司,以個半月時間趕製出Line,提供免費通話及短訊服務。簡單的介面,能快速輸入,在兵荒馬亂的年代很有效地進行聯繫任務,有些人成功送出自身位置後獲救。近年新增的大量貼圖,也是求快求便利。「我們要讓貼圖變成身體語言來協助溝通,一幅圖勝過千言萬語。」日本Line公關部的山田葉月接受訪問時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