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4年,被稱為「愛你一世」之年。現今世代,「一世」二字很虛無縹緲,當年輕人視轉工跳槽如換女朋友般,找到新目標,不理是否合適,匆匆換了再算,結果如何?不得而知。愛情沒有一世,連工亦沒有一世。回想數十年前,在那個找一份工比找女朋友更難的世代,孔鴻剛有幸入行學做嫁女餅,包伙食包住宿,還有人工,生活得以安穩。可遇不可求,當下立心要做好這份工。今年已屆68歲之齡,還繼續做着這份工,暫不言休!從他口中,也說出了唐式嫁女餅的前世今生。
記者:區佩嫦
攝影:陳永威
福哥那些年……



時光回到1962年。當時颱風溫黛襲港,人心惶惶,加上大陸難民不斷湧到香港,要找一份工作往往需要舖保人保。為求每個月賺取十元八塊,買得五毫子一斤的白米果腹,已經大費周章。當時,一位名叫孔鴻剛的小伙子,只有16歲,有幸跟隨父親入行,學做糕餅,因樣子儍更更、性格憨直,被師傅喚作「阿福」;今天的阿福已是奇華餅家的唐餅部主管,員工尊稱他為福哥。當年的奇華只是一間售賣糕餅、糖果等的雜貨店而已,糕餅是自家製作,福哥一入行便學做麵包、西餅和唐餅;學餅以外,最重要的工作便是「拉柴」。「當時還是燒柴年代,學徒要將一綑綑的柴枝從天井搬至柴爐旁,方便師傅烘焗糕餅,因為柴身太重,搬起是不可能的,只可拉動;我們便叫『拉柴』。直到1971年引進電爐後,『拉柴』時代正式結束。」福哥回憶道。
嫁女餅的榮華富貴
做糕餅學徒並非福哥的本意,只因孔爸爸怕他學壞,堅決要他跟隨左右學做餅。「當時找工作很難,有工返已不理喜不喜歡、有沒有興趣,而且公司還包住宿、包午晚兩餐,可以留下工錢報讀夜校。」初入行,月薪七十元,那年頭一個白領的薪水才不過百多元呢!可是上班數月,受政府《僱傭條例》所限,18歲以下青少年不能留在工場內工作,福哥遂改於油麻地上海街的店子做售貨員。該舖鄰近避風塘,顧客以水上人為主,他們特別重視禮節,多會選購店舖的招牌貨──嫁女餅。嫁女餅,行內人又叫五色餅,分別有紅綾、黃綾、白綾、合桃酥及雞蛋糕。「綾,即綾羅綢緞中的綾,是最名貴的衣料。禮餅就以綾酥為首選,寓意榮華。」而不同顏色的綾酥各有寓意,黃綾以豆茸做餡,寓意貴氣;白綾則是五仁餡,代表女方貞潔;紅綾餡料為蓮蓉,寓意喜慶。看着福哥將粉紅色麵糰包着蓮蓉、鹹蛋黃,手法乾淨利落,不出一分鐘,脹卜卜的紅綾蓮蓉酥立現眼前,蓋上紅色印章,齊齊整整地放在餅盤內。在示範過程中,傳來此起彼落的聲音:「福哥,影相呀!」、「好靚仔呀!」、「笑得開心點!」這時,我感受到室內的牛油酥香,還夾雜着一份幸福和親切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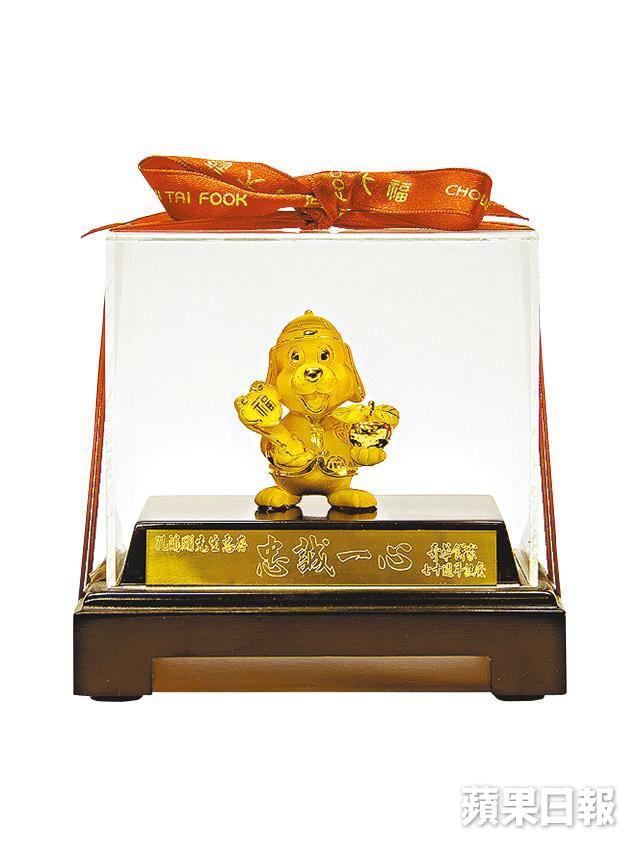
唐餅始終是唐餅
今天,福哥仍然穩守在工場繼續做餅,全因自己夠主動。「20歲時,北河街工場開始運作,我要求回餅房學唐餅,搓麵粉、炒蓮蓉、混餡統統要學,近二千呎的工場放着三張長枱,一張枱站滿廿多人;你搓粉,我分餡,他包餡,一人一樣,分工合作,而一起工作的爸爸每次見到我稍有差錯,即用水勺敲我後腦,卻不會告訴我哪裏出錯,我惟有扮勤力,樣樣學、樣樣問,加上我較性急,最能將唐餅做好。」原來唐餅講求韌性,麵糰搓好後必須於五、六個小時內入爐,否則餅皮便會失去韌性,餅身亦不會脹身。原來,性急也有好處。
只是性急的壞處,在炒蓮蓉時盡現。「每次也要炒百多斤蓮蓉,所用的大鑊和鑊鏟像小艇與船槳,每次要不停划不停划,划足個多小時至蓮蓉帶黏性才行,心急很容易炒不好;若是那天少吃碗飯也不行。到80年代,炒蓮蓉、搓麵粉等工序才開始由機器取代。幸好公司規模開始擴大,才不致淘汰人手。其實有些步驟仍然要依賴人手,好似去蓮子芯、包餡等,始終機器是無法完全取代人手的。」的確,自80年代開始,人手開始被機械取代,唐餅亦開始被西餅取代,不少唐餅專門店悄悄結業,要繼續站穩住腳,惟有改革應戰。老餅改革,將之年輕化,找明星代言、大賣廣告,「唐餅始終是唐餅,不像西餅般可以轉口味、轉外表;我們為了迎合健康的潮流,棄用了豬油,黃蓮蓉改為白蓮蓉,甚至做出低糖口味。」
人情味今不如昔
在奇華工作了半個世紀,難道沒被重金挖角?福哥笑笑口說:「沒有!」怕在公關面前說實話被責訓嗎?「不是,我對公司很有歸屬感。記得六、七十年代時,老闆黃業榮對員工很好,除食宿外,隔年還安排我們到東南亞旅行,東南亞國家已經全部走勻了!」只是,昔日的公司旅行褔利,今天已不復再,不過,去年還是到了海洋公園。那在這五十年間,可有在公司找到另一半呢?「哈哈,以前學做唐餅的,全部都是麻甩佬,那像現在有女性入行!倒發生過難忘事,三十多歲時,晚上兼職做司機,被一塊從五樓跌下的玻璃砸到手指,手指筋斷了,休息了兩個多月亦發覺手指不太靈活,惟有逼自己苦練,當時真的很心急,很想完全康復!」由最初被逼學做餅,到受傷後發覺已經愛上唐餅;就是這份愛,讓福哥安於奇華中工作,還不言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