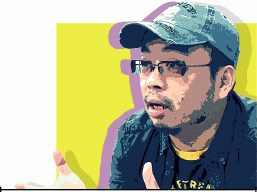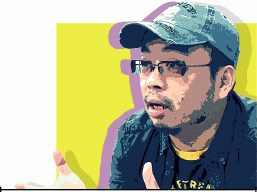
據所謂banality of evil,我完全明白為何有土生或土長的港人會懼怕學民思潮及其所能鼓動社會的那份力量。
又或如老本行中為求生動創作電視劇的反派角色,落筆間為他或她多添一份檢視自身善惡的迷思,至為實惠。撇除內地總局對奸角的落伍面譜準則要求,「立體反派」的戲劇化處理仍是今日潮流,pure evil固然出彩,同樣真實,但畢竟只是少數,毒販黑幫漢奸魔教教主苦海一眾若在每天殺人放火的辦公時間外仍得秒秒自覺行惡,多累?倒不如也來點父慈子孝偶然買買旗種種花扶阿婆過馬路,角色頓變得「鮮活」,觀眾受落也非單單此技巧得法,就因現實人辦你我皆見(包括照鏡,這是事實)。今天建制議員689鄉事派雜交俱樂部諸君固然擁抱這種情懷,你又以為泛民陣營中乏人?放眼盡是例子,就算行為再出爾反爾也要戀棧自我期許的那片道德高地,生前死後,若沒有一句為執善而行惡的理由來開脫,鏡中自己能站得住腳步嗎?所以學民每次上陣交鋒,建制打手們醜態畢露是常識,泛民中人現狼狽相也越見平常,而戲碼重複亦無非「立體反派」這種角色心態實在太普遍(連眾多以狙擊泛民者也難免落入同一套路),陳套的角色行為才會演個不停。
成長必招折損
至於為何厚此薄彼不將同學們的激銳坦率同樣形容作衝動幼稚的一番藉口,原因就只在那份成年人人心中早褪色的「純粹」。古往今來,當權者怕學生,其實任何成年人,包括為父母者也怕,當中,並非文革恐懼症(我絕不會拿紅小兵來如此矮化眾生,請放心),實只是嫉妒而已。成長必招折損,當中那張失物清單上盡是人性真善美的形容詞,有時我禁不住會偏執到每遇上一個無知、淺見、自以為是、小學雞的年輕人,也認為是因他們長大得太早太急,非他們年歲本質上的錯。
記得去年與戴教授淺談過後,我在還未能弄清楚行動最終將會以何種肢體語言被迫在中環展現,就答句記者譚蕙芸會支持佔中,除了因為這是受制於非常局勢下為追求正常事而行的非常手段,我也真好奇香港人是否也難免例外於「平庸的邪惡」,屆時我城的大多數究竟選擇為存活而拒承擔時代身份,抑或叛逆其求生本能,為族群往後能跨開闊步作出冒險,甚至犧牲?就只可惜,一年間變化,一年前的好奇,我今越不樂觀。
或許,所有自恃有民意授權的代議士、甚麼教主及甚麼甚麼精神領袖們,是時候放棄追逐人世間的主角領銜,作個supporting role好好支持、承擔歷史責任,才是本份。我們年華已去,我們包袱已厚,我們腦筋已俗,我們言辭已窮,我們稜角已鈍,我們火花已滅……謂政治就是妥協的藝術,在多數時候,到底也就只是一句鏡前的自說自話,成年人的所為早令成年人也失望,我們還能厚顏要求年輕人馴服座前?
【周一鳴】
撰文:周旭明
金牌編劇,細膩筆觸刻劃出人生百態。
本欄逢周一刊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