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概因為父親年輕時曾習油畫的關係,在我念小學時,父母就送我和我哥到油麻地的香港美術專科學校學習素描。記得那時候每逢周末,我和我哥都是自行去坐地鐵,從觀塘到油麻地上課。父母比較放心,可能因為是那時候的地鐵都很簡單,九龍線的總站就是觀塘和油麻地,所以我們其實只是由一個總站乘到另一個總站而已。
有些時候偶爾早到,我們就會到附近的中華書局看一陣子書,然後才去上素描課。小時候獨自上街的機會不多,所以那時候的每個周末,就是我兩兄弟最自由的時光,也可能是這個原因,從小便培養出我對美術的興趣。
初中的時候,我曾立志要成為畫家或廣告設計師,因為在我當時的模糊概念中,畫家和廣告設計師都類近,他們在電影或電視劇中,永遠不用穿西裝上班,工作時間也好像很自由和有彈性,喜歡睡到甚麼時候就甚麼時候,喜歡往哪裏跑就往哪裏跑,而更重要的是,這些角色大部份都深受女生歡迎。
電腦普及遇挫折
十一歲那年,我和我哥在土瓜灣一間書店內,首次看到日本畫家空山基(Hajime Sorayama)的噴畫作品,被他那恍如照片般真實的金屬女機械人所震懾,既性感又不怕被家長責怪(起碼當時我是這樣認為啦),也充滿未來感,那時候心想,噴畫必定是未來的一種嶄新繪畫模式,於是趕緊回家哀求母親讓我學噴畫。
結果,母親替我和我哥找來一位姓鍾的噴畫老師,也到旺角的廣益美術設計用品公司買下噴槍。鍾Sir除了教授噴畫外,還有教平面設計,那時候電腦仍未普及,平面設計都是用着一張張牛油紙,在上面用marker記下要落色網的顏色比例,一層一層的四色印網。記得鍾Sir還說,這都是成年人才會的技巧。那時候我在想,我和我哥在十一二歲的時候,就已經跟鍾Sir學着掌握這種技巧,我們這樣就比所有想做廣告的人跑得更前,有了這樣的技術,中學還未畢業,已可能被廣告公司招攬了。
但世事往往就是如此荒謬,你提早學會了技術,但沒想到,技術也在不停演化。當我們再大一點時,電腦開始普及,平面設計不再用一層層的牛油紙去指示印刷公司如何去做,所有事情都能在電腦內完成。在我發現這事情時,我已差不多中學畢業了,所以對我來說,實在是個無比的挫折。
結果這個挫折感,讓我開始害怕美術方面的工作,而與此同時,我也開始對寫作和電影產生了興趣,於是繪畫和美術的事情就擱了下來。中學時我經常翹課,只有美術課才例必出席,因此偶爾在舊生聚會時,都會有同學問我,是否還有畫畫。於是有時候我會想,這樣放下好像有點可惜。


關注瀕危大熊貓
由於近年工作開始比較能自行分配時間,所以我就想在不同媒體上做創作,偶爾拍拍寶麗來,弄一下絲網版畫。雖然一直也想做雕塑和裝置,可是一年到晚四處跑,總是無法靜下來待在一個地方,因此比較難找到機會。
幸好,去年獲策展單位AllRightsReserved之邀請,與岳敏君、山本耀司及NIGO等,一起參與了為四川都江堰成立的首個大熊貓疾控中心之籌款計劃「HE.ART for Panda」,每人製作一隻屬於自己的大熊貓裝置作品,希望藉此喚起大家對瀕危大熊貓保育的關注。大熊貓本身的造型,是以國際知名藝術家Lawrence Argent所創作的巨型大熊貓為藍本,再以此創作。
去年我忙着兩部電影的拍攝,在香港北京台灣三地跑來跑去,兩個劇組部份的拍攝期甚至是重叠的,但為了這個創作,我在路上仍一直惦記着,尤其要跟這麼多位大師同場,可不能隨便交出個行貨。
在跟AllRightsReserved溝通時,他們曾想跟我說一下別的藝術家會做甚麼,但我趕緊着他們別告訴我,因為這樣會對我構成壓力,雖然我也會忍不住去想像各大師的表現手法,但又怕影響自己的創作,所以還是先不要知道會比較好。這個大概跟和幾個導演一起拍那種短片合集電影有點近似。
我在想該如何喚醒大家對大熊貓的關注時,就認為應該用一些極端的方法去呈現大熊貓現在瀕危狀態的嚴重性。我特別喜歡看B級恐怖片,所以凡事都會往B級恐怖片的方向去思考,結果想出了要做一隻大熊貓木乃伊,因為木乃伊經常是B級恐怖片的源頭。
木乃伊片攞靈感
記得數年前在香港電影節看過一部低成本的美國獨立電影,名字好像繙譯為《骨扒好嗒》,是講述在一間老人院內,住了幾名老人,其中一人自稱是貓王,因厭倦浮華生活,所以和經常扮演貓王的人交換了身份,可是交換沒多久,對方就暴斃了,自己則因傷流落到老人院;另一人更離奇,自稱是甘迺迪,因被政敵暗算,把其膚色染黑,變成黑人,然後安排他遇刺假死,把他困在老人院裏。二人既好色又粗口爛舌,誰知有天碰上木乃伊襲擊老人院,兩個年邁的英雄決定重出江湖,大戰木乃伊(對,我已把所有劇情都說完了,最後的半小時,就是兩個老弱殘兵跟木乃伊,在老人院門口的草地上大戰)。
記得當時我都看得笑翻了,雖然太太完全不明白為甚麼要看一部這樣的電影。因為這部電影,我決定要創作《熊貓木乃伊之逆襲》(Here's Mummy Panda!)這個作品,來提醒大家要是繼續視若無睹、漠不關心,我們的下一代恐怕就只能等大熊貓木乃伊復活時,才有機會見到大熊貓了。
為了把木乃伊縮小比例,於是我在藥房買來各式紗布,然後切成幼條狀,染上各種顏色去測試,也參考了很多木乃伊的電影和真實木乃伊的圖片,盡可能去模仿其質地。這是個很有趣的過程(當然對切紗布的助理來說未必是),在替大熊貓包上紗布時,覺得效果不佳,便馬上拆掉,這樣來來回回弄了四五次,最後就成了現在這個模樣(其實我認為蠻像一個大熊貓木乃伊的,雖然太太第一眼看到時,說它有點像一隻生薑,應該用刀背拍扁它)。
這個裝置將於今年一月十四日至五月三十一日在四川成都國際金融中心(Chengdu IFS)公開展覽,並進行慈善拍賣,所籌得的善款,將全數撥捐該研究中心作大熊貓治療研究、安老和教育等範疇,用以提升國際對大熊貓的保護和科研上。
雖然一直要把這個大熊貓帶在路上,跑上幾個城市去創作是很累,但整個過程卻挺有滿足感,希望接下來能分配到更多的時間到這些不同媒體的創作上,帶給大家更多有趣的作品。畢竟,創作不一定是文字或電影,有些創意,還是可以有更多不一樣的模式去表達。希望這隻生薑,能幫到四川瀕危的大熊貓吧。

【我來了,是要叫人得過癮】
撰文:彭浩翔
祖籍番禺,生於觀塘。集作家、編劇、導演、製片人、演員及藝術家於一身之處女座。尚且幹活,只為供養其網購血拼及極限運動。
本欄逢周六刊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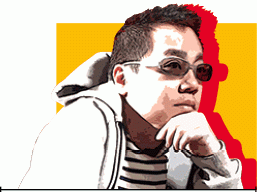
戲裡戲外,話題最強,立即收睇《動戲場》:
http://hk.movies.nextmedia.com/extra/li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