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多姿多采形容鍾普洋的人生,他的朋友一定異口同聲:你知道的,實在太少。我多麼希望認識30歲的鍾普洋,那時候他剛在香港創辦DHL國際,背景是殖民地香港,年輕人充滿自信,鍾普洋身兼DHL總裁、銷售員、速遞員等數職。我可以想像,鍾普洋那時候的笑聲比現在更響亮,因為在他面前,一切都有可能。能夠和30歲的鍾普洋一齊探索人生,我相信是賞心樂事。但我第一次接觸鍾普洋,是70歲的鍾普洋,我很難假裝不知道他的燦爛過去。這感覺很特別,我不認識鍾普洋,但又很熟識鍾普洋,這餐飯是在這前提開始。
訪問鍾普洋並不容易,他人緣一定是很好,相識滿天下,關於他的事迹,傳媒已有大量記載。不過,問十個認識他的朋友,怎介紹鍾普洋這個人,可能得出20個答案。讓我試數:創業者、企業家、國際名人、才子、作家、創意人、思想家、藝術家、收藏家、慈善家、教育家、知識人、方法學家、雜家、人生策劃家、生命經營者、退休家、文藝復興人。我跟他只食過一餐飯,我只數到這麼多。
以大衞與哥利亞論發牌風波
飯前,在電話中,鍾普洋已跟我說故事,這是電視發牌風波高𥧌期,他似乎是不吐不快,他想說大衞與哥利亞的故事。鍾普洋1972年創辦DHL國際,是香港第一間專營速遞服務的私營公司,對手是郵政局,即是政府。DHL由鍾普洋和秘書租兩張寫字枱開始,政府最初沒多留意。1973年,DHL開業約一年,警方控告DHL威脅郵政局專利,要求DHL停業,DHL決定反擊。
大衞挑戰哥利亞,在殖民地香港,應該是以卵擊石?結局是DHL勝出,過程中包括DHL和政府對簿公堂、政府試圖收緊郵政條例等。政府出奇地敗下陣來,但鍾普洋強調,重點是政府願打服輸,沒語言偽術,沒搬龍門,跟現屆特區政府管治手法,構成強烈對比。
40年前,DHL和政府這一仗,鍾普洋在他著作中寫過。大衞擊倒哥利亞,故事當然壯烈,但此時鍾普洋腦袋中不停在轉的意念,不是這麼簡單。他想到更深層次的東西,午飯前他送了一本書給我,Malcolm Gladwell的新作《大衞與哥利亞》。
《大衞與哥利亞》是一本破謬之作,普通人挑戰巨人,表面上無得鬥,普通人很多時能夠勝出,並非僥倖。3,000年前,大衞與哥利亞之戰,便是這本書第一個案例。哥利亞是昂藏七呎的巨人戰士,大衞是牧童,但Gladwell指出,哥利亞身穿逾100磅盔甲,動作緩慢,而且懷疑他長得這麼高,是由一種病引起,而這種病令他視力受損。
哥利亞以為依照戰士傳統,跟大衞近身以兵器搏擊,不過大衞沒打算跟哥利亞埋身肉搏,他選擇以對自己最有利的方式對抗哥利亞。原來大衞是久經訓練的投石者(slingers),古時投石是戰爭武器之一,專業投石者可在三幾百米距離,準確擊中細小目標。大衞知道埋身搏擊是死路一條,當哥利亞等待迎戰之際,他擲出一塊石,擊中哥利亞額頭,撞擊力大如被手槍射中,哥利亞當場死去。
DHL對抗政府 勝在計仔多
這本書的主旨是,哥利亞不是這麼強,大衞不是這麼弱。弱者沒背負着一定要勝出的包袱,可自由選擇其他人未想過的戰略,例如大衞沒打算按照戰士常規出戰。巨人的優點同是缺點,世人對巨人有期望,普通人被視為弱者,反而製造出奇制勝的機會。DHL對政府一戰,政府這個哥利亞其實有弱點,DHL這個大衞勝在計仔多。
「大衞不簡單,他是一個有勇有謀的年輕戰士。」鍾普洋指當時DHL在香港規模雖然不大,但在美國的姊妹公司已建立網絡,最初DHL在香港業務以美國為主。除非美國速遞公司走來香港,DHL是做獨市生意。DHL提供一項確實有用的服務,目標客戶一講即明。說服客戶,鍾普洋有一個只需一句話的撒手鐧:「我可以把你的文件一日內送到紐約。」當時經郵政局寄一封信去紐約,需時約八日,並且是不肯定的八日。DHL當時主要客戶對象是銀行、貿易公司、廠家等。
政府曾計劃修改郵政條例,鞏固其獨市地位。哥利亞不錯是權力大,但弱點是權力不是天賦的,有它的來源。表面上,殖民地政府不是民選產生,不需每事徵詢民意。大衞看穿政府的主要權力來源之一,是商界,而商界講現實和利益。鍾普洋游說商界,指出郵政條例修改後,跨國企業營運將受損,因此反對修改郵政條例,不是幫DHL,而是幫自己。商界群起反對修改郵政條例,政府敗下陣來,郵政條例至今沒變。DHL一仗後,郵政局基本上是接受速遞公司的存在。
「速遞不是很難做的生意,收件和送件,幾簡單。不簡單的地方,是這生意真真正正需要以人為本。」
「你想下,幫襯一間速遞公司,客戶唯一接觸到,是收件和送件的速遞員,中間過程客戶看不見,只能信任速遞公司能準時把文件送達目的地。這是一種憑感覺的信任,而這感覺很大程度建立於客戶與速遞員接觸的經驗。」速遞是永遠「作客」的生意,速遞的主場是別人的辦公地點。
成功靠信任 最緊要「執生」
DHL成為全球最大速遞公司之一,一切是從香港開始,總部由始至今設在香港,這是香港人的驕傲。我們不時批評香港富豪,指他們靠地產發達,怎富有也衝不出鯉魚門。鍾普洋是例外,這富豪從開始便是以全球為家,建立鯉魚門以外的業務網絡。DHL一開始便賺錢,但所謂賺是紙上賺,公司一直欠缺現金,原因是應付賬和應收賬之間出現缺口,生意做得越大,缺口越大。鍾普洋回憶,DHL創立初期,長期缺水。鍾普洋談DHL成功之處,重點是被環境逼出來的用人方法,背景是DHL沒資源發展完善管理系統,一切靠人,靠對人的信任。
信人,就是現代企管人大談的empowerment?鍾普洋糾正我:「不是empowerment,empowerment意思是上司本來擁有這權力,只是把權力下放予下屬。DHL一套是把權力向下推,從開始,上司便不擁有這權力,這份工作由始至終都是屬於下屬。」DHL發展主軸是人:信自己、信同事、信客戶。

「做服務業,最緊要懂得『執生』。」鍾普洋對「執生」有很深的研究。客戶提出特殊要求,速遞員須請示上司,他認為是失敗。速遞員視自己為決策者,給自己權力下決定,處理突發事情,在DHL文化,是基本功。我問鍾普洋,執生英文是甚麼?「最貼切可能是improvisation,長一點是dealing with an unpredictable outcome on the spot。以餐廳為例,我向侍應提出食物上要求,假如侍應須請示上司,便是不懂執生,侍應應可當場回應我,假如牽涉食物技術問題,頂多是請示廚師。」
DHL提供服務的地方,永遠是客戶的主場,久而久之,DHL變成客戶業務的重要部份。DHL身份由外人變成自己人,這客戶被鎖住了。鍾普洋提出服務者就是服務的概念(the server is the service),服務員的性格、知識、態度決定服務質素。一個懂得執生和不懂得執生的服務員提供的服務,可以是天淵之別。企業希望提升服務質素,應做的事是,提升服務員質素。

「以人為本」成為企管人的護身符,口中念念有詞,真正做得到,少之又少。實情是企管人都是權力狂,不願或不肯把權力分給別人。企管人對自己的肯定,源自擁有多少權力。放開,對企管人來說,輕則是不夠堅強的表現,重則是自信心出現裂痕。
放開,對鍾普洋來說,是理所當然。這或者是他的性格,他只是做自己喜歡做的事,或者是他看得通,放開是經過精心計算,最大可能是兩者皆存在,互相影響,難捨難離,最後內化為例行動作。鍾普洋認為服務業只能以人為最基本和寶貴的資產,怎樣了解人性,成為他一生追求的一套學問。
「從事服務業,影響我的處事思維,而我的做人原則,也影響我怎樣管理DHL。從開始,我便相信人的重要性,連empowerment也談不上,把權力向下推,我認為管理服務機構,只能用這一套。我對權力的信念,成為DHL的優勢。」
「我接到DHL這個波,是我的幸運,我接住這個波之後怎樣走,這不是幸運。」
企業文化可觸摸得到
這餐飯中,鍾普洋重複了幾次:企業文化是個人和家庭文化的延續。你怎麼樣,由你帶領的團隊,就是怎麼樣,扮不出來,逃不開。企業文化不是虛無,其實觸摸到,它就是關於人。
我在想,假如鍾普洋不是撞進服務業,而是進入以系統和制度為本的其他行業,例如製造業,以他的性格,捱得住嗎?「我應該會轉工。」鍾普洋報以雄亮笑聲。
我開始明白鍾普洋怎看待權力,深深影響着DHL的發展。懂得把權力向下推,「執生」變為核心質素,DHL服務水平與眾不同。客戶提出不同要求,DHL服務員具自信地處理要求,是創新的泉源。DHL創新不是在自己會議室想出來,而是由用家主導,再經過最接近現場的服務員考慮,這種創新肯定最貼近客戶需要。
DHL故事是關於三個外國人加上鍾普洋,而坐鎮在香港總部,一直主要是他。鍾普洋承認,塑造DHL企業文化,他出了很多力。DHL由早年一個「山頭式」管理的跨國聯盟,發展為一間有隊形、有重心、有方向的跨國集團,維繫着所有人的,是文化。鍾普洋放得開的性格,融入服務型思維,如魚得水,性格和思維相互影響,帶領DHL創造出一個不多見的走出鯉魚門故事。
從資料知道DHL其中一位股東十多年前突然去世,因為遺產問題,間接引發DHL股權出現糾紛。據我所知,幾位拍檔在世時,合作沒問題,沒出現爭產風波。鍾普洋苦笑:「做最多嘢嗰個唔出聲,梗係冇矛盾。」
會說故事更懂別人所想
飯前我看過鍾普洋部份著作,看到他敏銳的觀察力,以及樂於與人分享的胸襟。我多麼希望認識30歲的鍾普洋,那時候是他當打之年,我相信他容人胸襟應該沒變,聽一個在戰的戰士說故事,份外動聽。30歲的鍾普洋辛苦一日後,和我在大牌檔飲啤酒,聽他說今日發生過的精采事,多爽。懂得說故事,是一種重要的企管本領,我一直在學,學得不夠好,我覺得鍾普洋是箇中能手。
鍾普洋哈哈點頭大笑:「識講古仔嗰個贏。」講古仔是一種需磨練的技巧,我所謂的講古仔當然不是閒談吹水,重點是articulation。我選擇用英文解說,因為articulation中譯是表達,我認為表達不到articulation的意思。
講古仔講得好,需要清晰和力度;清晰容易理解,力度來自信念,較飄忽。說故事人相信故事,故事有力,即使說故事人在說一個虛構故事,能夠令自己相信故事,力度一樣可以很大。說故事的企管人懂得清晰和有力地表達自己所想,可體會同事和客戶的看法,鍾普洋所說,懂得說故事的人贏,不是說笑,這是一項實在的優勢。
一個這樣熱愛工作的人也有言倦的一日,鍾普洋離開DHL之前,心情是怎樣?「創業者跟專業管理人不同,公司和人都有生命周期,在不同周期,創業者須不停調整自己。我很早便去史丹福大學讀專業管理,理論我都認識,但骨子裏,我始終是創業者,一個服務型思維的創業者。」
「50歲去激勵20歲同事去創新,去做一些其他人未想過的事情,感覺很不同,難免有脫節感覺。到最後,可能我已經不願意再做。」
離開,容易嗎?「我可以,可能因為我周身癮。」

落力退休
鍾普洋52歲退休,以任何角度看,也算是早。以香港人平均年齡算,還有30年的路要走。換句話說,讀完書工作30年,退休生活也是30年,果真是分開人生上下半場。鍾普洋寫了《落力退休》這本書,教人退休。對,退休要學。
幾年前出版時,這本書的書名早吸引着我,「落力退休」是oxymoron,對大部份人,退休是放慢腳步,過休閒生活,何來落力?鍾普洋道出許多退休人士沒有正視的問題:退休漫長歲月,不規劃的話,退休生活隨時辛苦過工作。52歲這年齡跟我太接近,鍾普洋做到了,我可能也要開始細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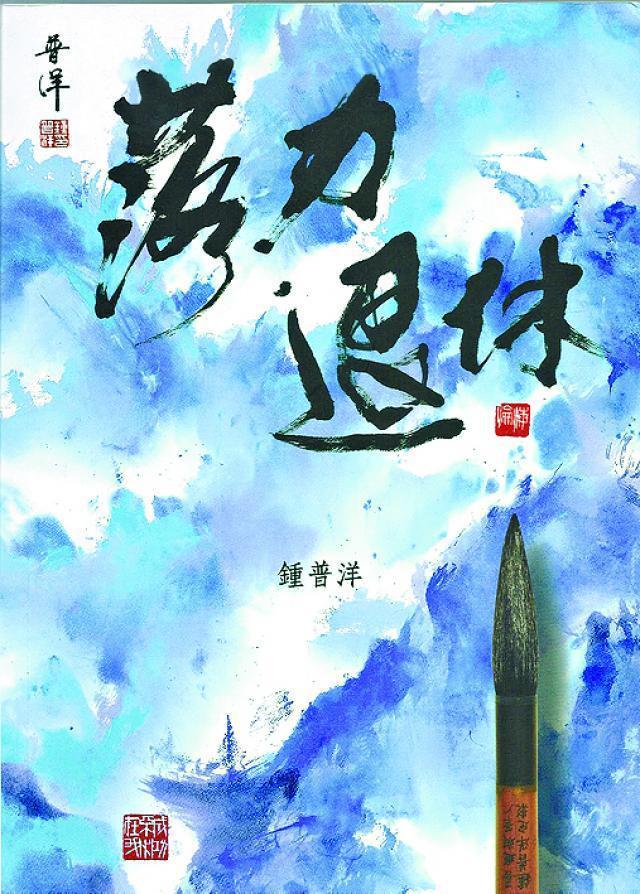
「獨孤求靜」探索新體驗
鍾普洋經驗中,有一件事我覺得很有意思,不少退休人士鬥心仍強,凡事想做得好,退休後脫離不到想贏的心魔。然而,退休後,資源和體能上,客觀環境不同,鬥心怎強也未必能達到想贏的標準,本應是着重放開的退休過程,可能產生種種失望。
鍾普洋坦言經歷過這種迷惘,後來發展出一招「獨孤求靜」方法,處理自己心情。獨處製造出靜,人靜可找到新體驗,越聽鍾普洋談退休,越覺得自己未準備好。
蔡東豪
足本收睇《亂噏24》x 楊千嬅;緊接落嚟 Miriam 繼續同你談談情, 吹吹水!
周一至周五《亂噏24》約定你: http://bit.ly/appletalk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