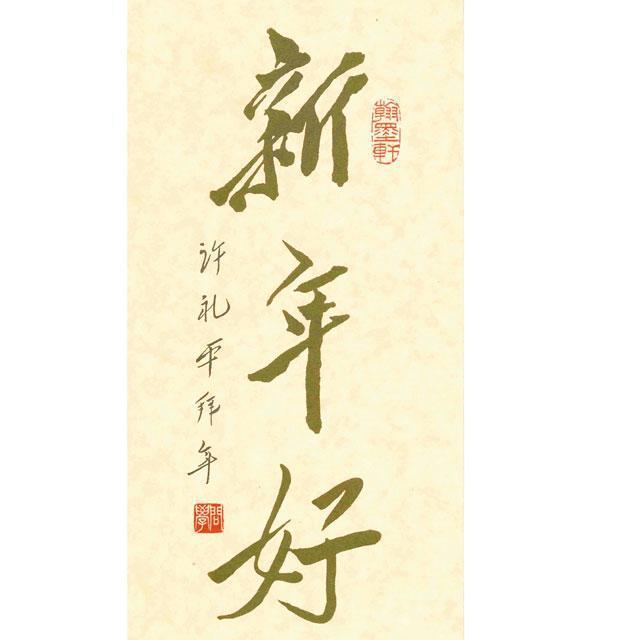
小思傳來賀歲美影,卡中紅白梅花交織,在白朦朦雪瓦齊檐之下,一度清幽古雅木門,上懸看似楠木綠字橫扁,彷彿退隱田園的名士齋門,門下「立春」二字,像宋人黃善夫刻本史記上的字體,醒目高雅,這讓我驚覺踏入癸巳新歲了。我隨即檢出舊日綴集「新年好」三字作回賀,也算為「禮尚往來」。我這三字不是集甲骨和金文,也不是集漢唐碑版,而是集「先帝」的手澤,筆者俗人,在「禮尚往來」之際,下點心思,也不免於趨時和媚俗的。
歐陽修有詩:「新年風色日漸好」(歐陽修《文忠集》卷五十三),簡而言之就是「新年好」三字。我原想以鄭孝胥「照海波光已釀春」(鄭孝胥《海藏樓詩》卷一)綴集這兩句詩為聯,這是頗切合香港新年的眼前景物的。但轉念鄭某是偽滿總理,他的詩題又為《日枝神社晚眺》,處此中日關係緊張之際,這是易招責備的,還是棄而不用,改集「先帝」手迹。這樣最為保險,是可免悠悠之口的。
七十年代以來,筆者每年都拼集不同名家如何紹基、吳昌碩、臺靜農、鄧爾雅的法書為吉語賀詞,製成長方形拜帖,以提昇底氣,以之郵遞諸友朋,一以賀年,一以表示小生尚在人間,幾十年都如是,積習難返。近幾年懶散,兼有電郵,遂免此習俗,不勞煩綠衣郎(郵差)了。
順便一說,劉九庵老先生曾賞面,自言每年收到筆者奉呈的賀年片壓在故宮博物院他老人家辦公枱玻璃面下。月前,蘋果樹下有文章提及,這箋箋之物居然也流入拍場,而正是那篇文章的作者買了,這位作者固然文獻為心,能采及葑菲,雖然我不知作者為誰,但令我感動的同時,也促令我緬懷劉老。蒹葭秋水,彼何人哉?不意此箋箋賀卡,敬意而外,卻能成了一點故實。
說罷賀卡,再說「新年好」,這三字妙在一個「好」字。毛公慣用「好」字,甚麼「好得很」啦,「革命委員會好」啦,「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啦,總之一個「好」字。甚至軍頭檢閱部隊,也高喊「同志們你們好!」三軍齊呼「首長好!」
另說,筆者寓所長年懸掛一個「好」字卻是賴老(少其)手澤,這個「好」字,灑金紅箋墨書,是賴老九十年代初來香港時所書,但沒有直接送給我,或許賴老覺得寫得不大滿意,就留在當時寓居麥當奴道友人鄭先生家中,本擬丟棄也。鄭君係筆者老友,古道熱腸,覺得此件其實還不錯,對筆者甚有意義,遂送來小軒,筆者叩謝不置。其實此件主要在佈局問題,動動腦筋,略加剪裁移位置成菱形,交老師傅麥泉公子裝裱,配以酸枝鑲影木方框,懸於壁間,觀感大佳,居然成一寶物。從此長年懸於寒齋,每天對着,就算有甚麼不好,也見到好,弄到好!開門見「好」,大吉大利。賴老所書「好」字右邊題有小字數行:「禮平大兄,已有一女,庚午之夏,又得一子,子女繞膝,欣慰可知,故書一好字以賀。」而署款「賴少其」壓在「女」字下。賴老夫人曾菲,梅縣客家人,紅軍女戰士,與先帝前妻賀子珍過從甚密,論黨齡則早於賴老。有老友笑賴老,一輩子都被夫人壓着。賴老十歲戴紅領巾參加兒童團,在廣州美術專科學校時是學生運動領袖,但到一九四○年才入共黨,共黨論資排輩,怪不得有一回賴老問女兒,是我說了算還是你媽說了算。曾菲比賴老聰明,政治上敏感度高。七十年代初賴老復出不久,上頭擬調賴老出任北京故宮博物院院長,曾菲堅拒。文人進京,難有好下場。當時賴老若乖乖聽令入宮,說不定就上了四人幫的賊船,一九七六年「花好葉茂」(華國鋒、葉劍英拍檔)之秋就不好受了。
賴老一世好命。一九一五年五月十六日生,筆者嘗笑他你是「五一六」(子虛烏有的反革命集團)。廣東普寧人,與筆者算是大同鄉。早歲搞木刻創作,十八九歲時已編著出版了中國第一本介紹版畫技法的書《創作版畫雕刻法》(一九三四),署名賴少麒。賴老說麒字筆劃多,木版上不好刻,就省為「其」了。文革時被批判,紅衞兵故意將他的「其」改為「奇」,以與劉少奇同名也。一九三六年畢業於廣州美術專科學校西洋畫系(與本港畫家林建同丈同學)。被魯迅譽為「最有戰鬥力的青年木刻家」。一九三九年十月投筆從戎,參加新四軍,一九四一年皖南事變中被捕,解上饒集中營,關站鐵籠,九死一生,嘗託人捎信與老友苗公(黃苗子,上海公安局掌璽大臣)求救,苗公去信託人相助,或起作用,賴老得脫後嘗去函答謝苗公。賴在部隊搞宣傳,相當於軍中文化部長。一九四九年隨部隊登船南征,忽接急電,馬上離船,奉命上京參加開國大典。不然或早已沉屍碧波綠水中,或血濺黃沙光榮犧牲了。
賴老人不錯,聽啟老多次讚揚他。解放後賴老出任南京軍管會文藝處長,中共南京巿委宣傳部長。對不少畫家多所幫忙。嘗到傅厚崗六號探訪傅抱石,時中央大學學生左傾,認為傅抱石係國民黨反動派走狗,蔣公總統的告全國同胞書就是傅公起草的,學生不上傅公的課,進行抵制,搞得傅很被動。賴老拔刀相助,以軍代表、黨代表身份,勸說學生,為傅公解圍。傅感甚,擬贈畫與賴公,拿出精品數十幅,讓賴老自己挑選。賴老向我透露,其實他看中《大滌草堂圖》,上有徐悲鴻題「真宰上訴」,但知傅甚重視此作,不好意思問津,只拿了件湘夫人中堂,嗣後又獲傅公賜一唐人詩意山水中堂,再就一件二湘圖成扇(今歸紐約鄧仕勳兄)。賴老當年也曾到杭州看望林風眠,見到這位藝專老校長家徒四壁,寒傖得很。後來安排林去上海。賴老對黃賓虹十分敬重,北京政務院總理周恩來贈齊白石「人民畫家」稱號,南方的賴老即封黃賓虹名譽稱號,並為黃舉辦一生人第一次正式展覽,出版畫集,賴老親自寫序,高度評價黃賓老。
一九五二年賴老調去上海,出任中共華東局文委委員,上海巿文聯副主席等職。因與賀子珍往來密切,又向上頭反映久住醫院的賀子珍要求出院回家,惹了上海巿委第一書記老左柯慶施不滿,打個報告,麻煩頓至。加上不久之後當今皇后娘娘先帝愛人江青同志收到匿名信,警告江青莫胡作非為,否則將其三十年代在上海不欲人知的歷史報告中央,信的下方有華東文委字樣,曾菲嫌疑最大,被鎖定審查,壓力極大,雖有貴人相助度此一厄,也弄到大病一場。上海成立中國畫院,賴老主其事,而院長一職,吳湖帆與賀天健都有可能,但互不相讓,矛盾頗深。賴公要調和矛盾,做了不少說服工作,擺和頭酒宴請吳、賀二位。次日上海新民晚報披露此一消息,而大字標題:賴少其與吳湖帆賀天健握手言歡。好了,又闖禍了。吳、賀二位係內定右派,作為中共華東局主管宣傳的地方大員,竟與右派分子握手言歡,這也被上頭老左上綱上線。最後貶去安徽合肥,出任中共安徽省委宣傳部副部長,這反而救了賴老一命。若然一直留在上海,又主管宣傳,丙午文革,丁未一月風暴,手下有兩位赫赫有名的姚文元、張春橋會放過賴嗎?貶官合肥,反得以苟存性命,蕭然物外。合肥有安徽省博物館,賴公常借館藏金冬心、垢道人之類名迹回家臨摹,畫藝大進。故賴老的山水得垢道人枯筆竭墨真傳,畫梅花和書法又有金農神韻。賴老老是因禍得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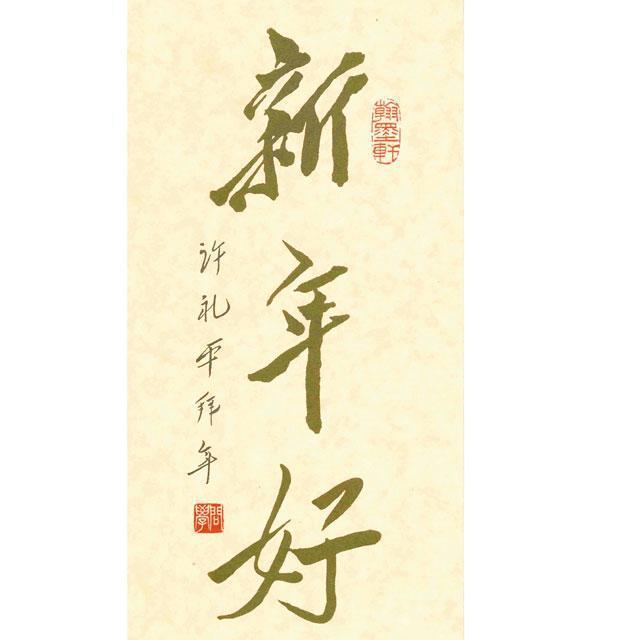
逮一九八六年賴老離休本擬住深圳,後改住廣州華僑新邨,不久遷水蔭路,均係細小居所,安享晚年。返回廣東與安徽大不一樣,目睹五光十色花花世界,「存在決定意識」(列寧語),賴老畫風為之一變,色彩繽紛,謂之丙寅變法。
八十年代,賴老伉儷經常出國。有次到香港大學訪問,做了場演講,聽曾菲說,連校長、藝術系主任、老師、學生加在一起的聽眾,只三二十人。曾大不高興。說賴老在大陸演講時聽眾逼爆會場,沒有一千也有好幾百人。過兩天來中文大學,也是到藝術系講演,系方大力發動學生出席。筆者時在中大服務,為了招呼曾菲,就聽不了賴老講話。筆者帶曾菲去范克廉樓(飯堂)飲咖啡聊天,叫了客法蘭西多士,曾菲咬一口,驚嘆不已說,想不到世界上還有這麼好吃的東西。曾菲吃得高興,閑聊間說見到馬臨校長,好奇馬校長俸祿,當面問他:「馬校長,你拿多少?」馬校長坦誠相告:「七萬五。」有一回賴老伉儷訪泰國返穗前路經香港,語筆者說那邊的華僑天天請他們吃鮑魚、魚趐、燕窩,吃膩了。我輩無產階級怎請得起這般大地主美食,只有帶他們上百樂潮州酒樓,點了凍烏魚,佐以賴老家鄉普寧豆豉醬,鹵水豆腐,小碟欖菜,扒碗白粥,也吃得津津有味。賴老嘗在中華文化促進中心辦畫展,也有銷售。據說新華社長王匡嘗上報中央謂賴老在香港開了銀行賬戶,違反有關規定。曾菲反擊之。此有關信件年前嘗見諸拍賣場。
一九九○年筆者創辦《名家翰墨》月刊,頭幾期重點介紹四王(王時敏、王鑒、王翬、王原祁)。賴老好心提了些意見,筆者為之悚然易轍。嗣後側重推介二十世紀大家,厚今薄古,令銷數為之激增。每一念及,又得感激賴老。
賴老早年錚錚鐵骨,連站籠都能挺過來。晚年身體較弱,又曾整理畫作時開了上格櫃門沒有關好,蹲下看下格的東西,站起來時被上格櫃門角撞傷後腦,要命得很。平日坐疏化斜着身子坐,更為傷腰。有次去巴黎坐十多個鐘頭飛機,也是如此坐姿,到達時站不起來了,要抬下飛機,坐輪椅參觀羅浮宮呢。賴老身子弱,膽子就細小。有一回去日本辦畫展,自己畫的展品依足手續辦申請,在積習難返的官府拖拉運作下,展期已到而展品仍運不出去。昔日舊部當今官員私下語賴老,你不辦申請將展品運上飛機,不就成了嗎。你正式申請,反而難辦。
六四之後,賴老老友千家駒遠走美利堅。九十年代初賴老去紐約辦畫展,碰到千老,打個招呼,不敢深談。太緊張了。
賴老的故事太多,扯不完的。說回這個「好」字吧。對着好字,又要感恩。
記得七十年代初常向《大公報》趙大哥(澤隆)請益,有一回在某外事(有日本人共同通訊社泉鴻之等在)飯局中趙問及我的家庭,知我上有父母,旁又有兄、弟、姊、妺,他說過去這就叫做「完人」,人家結婚都想找這類「完人」做伴郎或伴娘,會帶來好運,起碼好意頭。聽得我心花怒放,開心不已。嗣後娶妻,三年試用期滿(筆者見做教授試用期三年完畢才終身聘用,婚姻也似應仿效),遂生一女一子。(沒有再請教趙大哥,「完人」倘再加上下有子、女,有否更高層叫法,是否可稱「高級完人」?)而完人有緣,得一女一子,就是一個好字,賴老當時有意賞賜而未賜,本來是「糟得很」,最後由鄭兄搶救擲下,變成「好得很」。真要再次為「好」字感恩。
說開好字,再扯遠一點,民國四公子之一張伯駒藏有唐人杜牧書《張好好詩》卷劇迹,藏家和詩卷均姓張,張公子遂被戲稱為「好好先生」。五十年代這位「好好先生」捐獻《張好好詩》卷等一批劇迹與故宮,不久反右,「好好先生」沒有了《張好好詩》卷,處境就不那麼好了。繼之文革,日子就更難過了。黃永玉丈嘗撰文記述這位「好好先生」,寫得感人。看來「好」字是不能掉的。
身在香港,胸懷祖國,放眼世界,忽悟:「千好萬好不如逍遙自在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