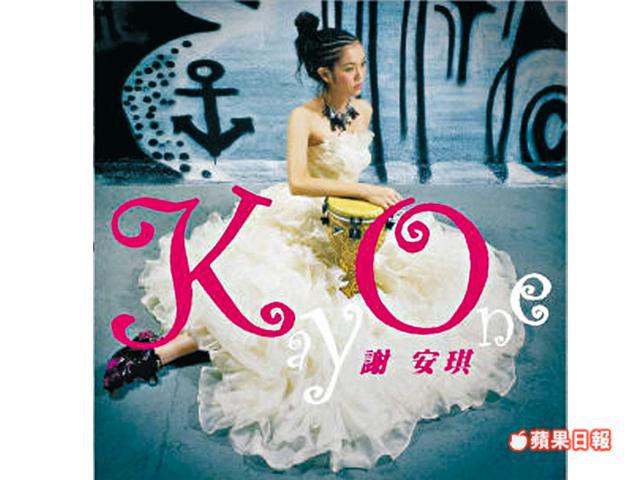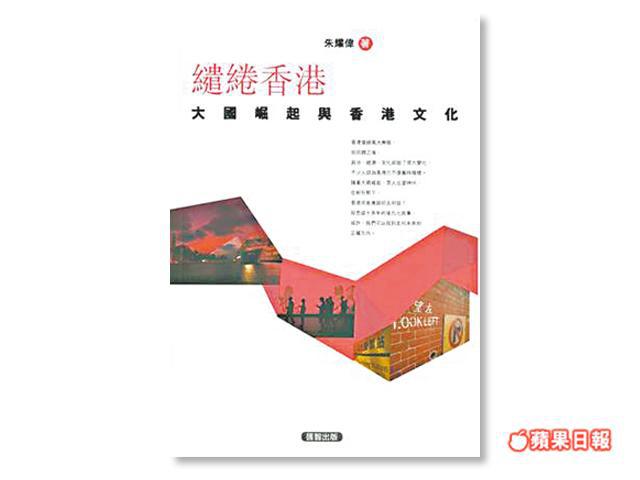
那年頭,香港流行文化威鎮四方,沒想過這些日子會去如黃鶴。年輕時,總覺得港產片、廣東歌太低俗,然後隨着回歸、強國冒起,才驚覺一切幾乎已消散。浸大人文及創作系教授朱耀偉新書《繾綣香港》,這本苦戀香港的情書,心情激動。我們長大了,但流行文化上的香港下沉了。
記者:何兆彬 攝影:蔡家輝
「香港三大Icon都失去香港特色」
蘋: 老師,讀你這本書,似乎你也是在香港流行文化漸漸褪色時,才回頭看:咦,原來從前香港的那些東西也不錯?
朱: 可以這麼說。流行曲也一樣,我記得訪問鄭國江老師,說起粵語流行曲最輝煌的日子都過去了,大家才回看,發現幾好。這幾年多了人來討論,與香港的本土意識抬頭有關,也跟我們這些文化人身份有關,例如馬傑偉、梁款,我們幾個人常常寫這些(香港流行文化)──我們身份不是甚麼偉大人物,不是華盛頓孔子,不是甚麼厲害人物告訴你才知道,而是文化承傳下來,點點滴滴,這些都是電影、流行曲告訴我們的。但這十多年,流行文化漸走下坡,港人對自己的身份認同開始質疑了。在過去,我們政治上沒有聲音,身份認同來自經濟、另一方面來自流行曲電影,從中找到認同,但這些年來,最後連周星馳都拍了《長江七號》──它很不香港,而且它在內地票房還好收得呢。流行曲呢?我的學生都不聽廣東歌了。
蘋: 你在書中提到,同一年,三個香港Icon(周星馳、徐克、陳可辛)都失去本土特色,你對他們都有情意結吧?
朱: 有,周星馳由細睇到大,徐克更早,早期看他《蝶變》、《第一類型危險》,但到近年徐克拍《女人不壞》……陳可辛九十年代拍的電影很香港、很城市。我對他們不是失望,徐克、陳可辛都到過荷李活,但再回來時沒有人能承繼他們,很多人甚至不認為這是個問題,這就令我好「揦住揦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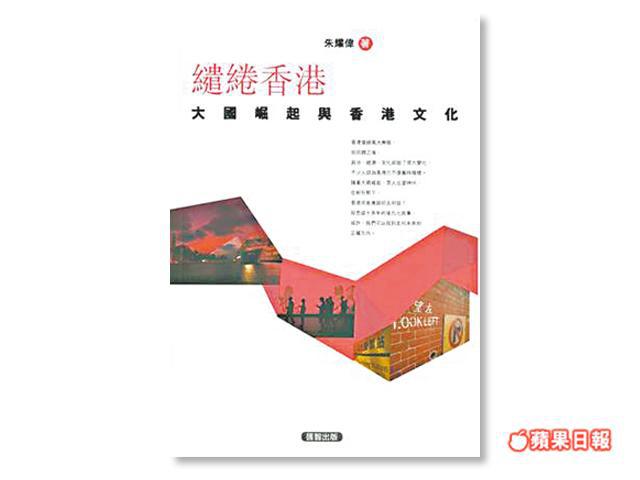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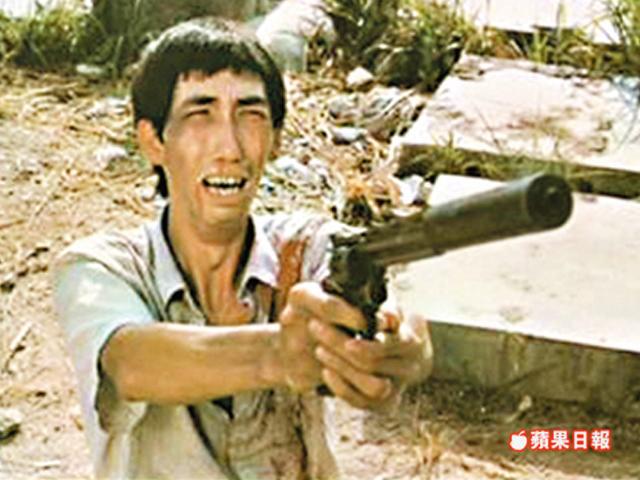
「年輕人認為聽廣東歌好辳!」
蘋: 你先是消費者,教書才開始研究流行文化吧?
朱: 也可以這麼說。八十年代只是消費,到了九三年左右我開始教書,對流行曲也開始研究,但到了近年,開始跟得不足,要找東西來研究,否則似乎那些歌我都沒有聽過。例如頒獎禮,那些(得獎)歌都不是平日我聽到的歌!不像八十年代,我是聽住那些歌大的,九十年代初,開始研究四大天王,那些歌也是我日常會聽到的,但如今,得獎歌我是一年聽不到三幾次的,當中尤以TVB的最嚴重,它那些歌特別騎呢!因為它沒有四大,有幾隻歌是得了獎我才聽得見。
蘋: 你意思是,為了要研究才去找那些歌來聽,否則就聽不到了?
朱: 這就掀起另一個大問題:粵語流行曲應該是港人最易接近的,為甚麼如今的歌香港人都沒有聽過?好像被割裂了。我的學生都只聽國語歌、韓文歌,我問他們,還有誰是平常有聽廣東歌的,舉手的人不到四分之一。另外一個經驗是我問他們有誰聽廣東歌,舉過手,落了堂,有同學靜靜來跟我說,他是很喜歡廣東歌的,老歌又有,新歌又有,但不好意思舉手!也就是說,如今聽廣東歌好唔型,他們會說「你仲聽廣東歌,好辳」!
蘋: 年輕人不聽廣東歌,是因為Peer Group Pressure(同儕壓力),還是因為其他?
朱: 我想是Peer Group Pressure吧。也關乎香港流行文化的形象,在從前,香港是流行文化的發源地,張國榮穿甚麼衣服,剪甚麼髮型,係好In的!大家馬上跟!但衰落後我們已不是潮流中心,如今的明星沒有認受性了。有一年Hong Kong Music Fair內有個展覽,找來了陳偉霆來表演,我以這例子來講課,同學就有過半人反問我:誰是陳偉霆?我的詮釋是:不認識陳偉霆才是有型的,識也要扮唔識。可見香港流行文化已失去了光環,變得老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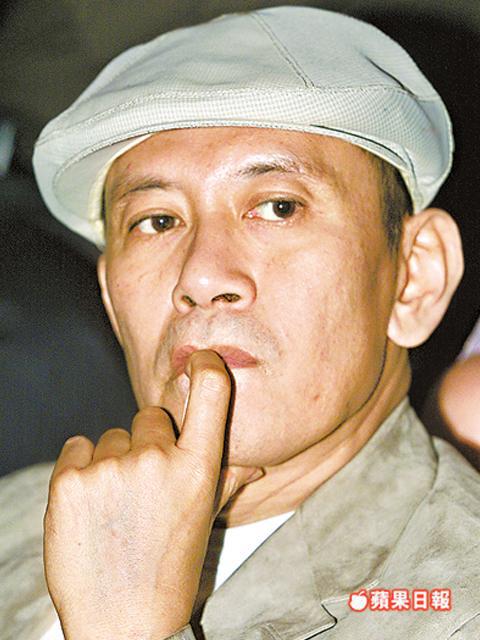


謝安琪曇花一現
蘋: 以你觀察,「聽廣東歌唔型」的轉變從何時開始?
朱: 我的看法,是千禧開始;霑叔(黃霑)的說法,就是九七,但九七後四大天王還有出碟的。後來有Twins,但走得出鯉魚門外的,其實也只有陳奕迅。Twins紅過,但只屬偶發,維持不了幾年。霑叔說過其中一個原因是盜版,但其他地方也有盜版呀,為甚麼別人能反彈?就是因為整體衰落了,給人的印象是Out了,結果形成惡性循環,唱片公司只願投資主流歌手,稍稍另類的都不願去做。
蘋: 記得05年左右,謝安琪等人出道,可曾令你抱過寄望?
朱: 有。05年謝安琪、王菀之一起出道。當時以為是一個轉機,但也許接受創作歌手的人都不聽廣東歌了,或唱片公司覺得賺得太少,好快就沒有了。早期謝安琪×周博賢的本土風格,是一時潮流,尚能轉型做主流歌手,留下來了,王菀之也一樣,但同期的藍奕邦、馮穎琪很快就轉幕後去了。我時常覺得香港的潮流文化都是這樣,短時間內被榨乾就算,但音樂文化應該要能持續,才能對樂壇有衝擊的。霑叔說得好:九十年代整個華語唱片生態已變,例如國內的開放,台灣有製造巨星的能力,但香港仍然食老本,沒有適應新環境的能力。
蘋: 你書中提到,七、八十年代香港亂,但亂中反而有活力,是因為大江南北的人都來了香港,這是否一種機緣?
朱: 我同意,霑叔的博士論文也提出這一點。當時內地封閉,台灣也未開放,香港在機緣之下,資金碰撞,所以也真的是可一不可再。也未必是香港人特別叻,但剛好那代人掌握到。其實現在仍有機會,但不可能再做以往那種偶像工廠了,現在台灣在這方面比我們更掂,內地呢,電影已學足了我們的模式了,香港有何特點?早期謝安琪×周博賢的《我愛茶餐廳》、《亡命之徒》我都很喜歡,而且完整,有內地交換生跟我說:「聽這些才是廣東歌!主流我不如聽國語歌?」但我覺得可惜,謝安琪紅了之後還算Keep到少少,但有少少曇花一現,雖然她仍有影響力。但如果市場再大一點,也許就能支持到早期的謝安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