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從轉行為動物謀福利,發現這個工作實在比想像複雜千倍。除了周旋在內地官員、動物保護機構之間、努力搞教育宣傳、籌款印書之外,這份工作附送的是一大堆人和動物之間的道德倫理哲學問題,往往要我扭盡腦筋,翻書上網,尋找更好的答案(永遠沒有最好的答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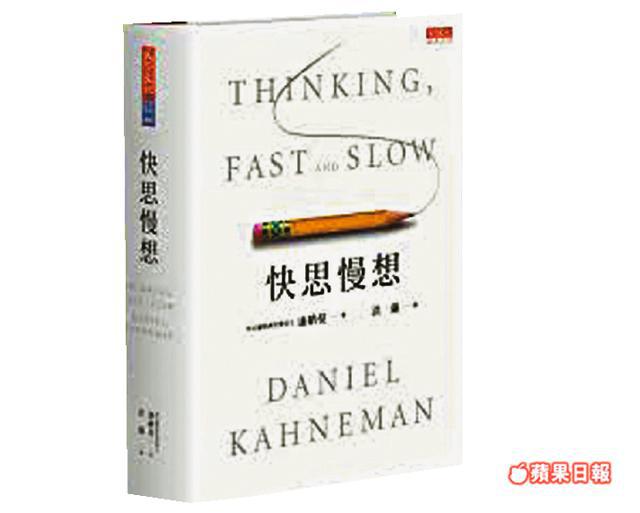
直至最近讀了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康納曼的《快思慢想》(Thinking, Fast and Slow),帶給我很多啟發。從心理學家對人類思考的研究,審視香港人一路以來對動物議題的思考方式,可以拿一些出來討論,目的只有一個:要改變,先思考。
要數最熱最值得討論的動物議題,大家都會想起「動物警察」。先旨聲明,我目前對「動物警察」的建議並不否定,只是聽着看着現在的討論,發現充滿偏見、情緒,不沉澱思考,不可能理出一套方法。
康納曼把思考系統一分為二,我們有快思系統(系統一),也有慢想系統(系統二)。系統一是快速的判斷,產生印象和感覺,例如愛動物的人聽到「動物警察」這個詞語,立即會有正面的印象。而系統二是需要花心智力量和時間的分析思考,例如試列出10個設立動物警察的好處,你需要停下來動腦分析,這時候你心跳會加速,瞳孔會放大。只依賴系統一,不一定引致判斷錯誤,但容易流於偏見,需要系統二協助分析,監控我們的思想行為。可惜,啟動系統二是費力的,而人性喜愛走捷徑,快速用系統一來下決定省時省力,所以偏見很難避免。
當人們不斷強調一些血肉模糊的動物照片是虐待所致,我們理應要思考:如何解決?可是當我們將「動物警察」這個很形象化的詞語同時提出來,系統一會自動把意念聯結,形成一個容易理解的因果關係(解決):動物警察=停止虐待。這讓你的心智放鬆,減少啟動系統二的需要。而重複地看到某些人把「動物警察」和「停止虐待」聯結起來,你們對這個因果的戒心放下,更加深信不疑。回想起來,你可能忽略了一些理據?例如不改變法例,誰人執法的後果都差不多?
經常聽說,歐美已經有動物警察,香港是時候急起直追。奇怪的是,當我認真翻查資料,發現世界上唯一有具規模動物警察隊的國家,只有荷蘭(洛杉磯有一隊聯合其他部門的動物專案組,不自稱Animal Cops)。幾年前開始,當地的一些組織發佈了一些不嚴謹報告,指荷蘭是世界其中一個虐待動物最嚴重國家。雖然當地虐待總體情況其實沒有惡化,但透過個別案例,用情感渲染增強讀者的危機感,和現在香港的情形近似。然後透過網絡主導輿論不斷重複議題,甚至成立「動物黨」(The Party for The Animals)殺入國會,最終推動動物警察成立。



心理學有所謂「月暈效應」:你喜歡一件事,你傾向喜歡它的全部,包括你沒有觀察到的東西。「我告訴你,動物警察可以制止虐待動物,外國很流行……」你自然傾向喜歡所有有關動物警察的概念。可是你不會花心力留意,甚至刻意忽略有違你喜好的細節:荷蘭本土增加動物警察數量的同時,破案率未見提升,反而削減巡邏警力,導致社會對動物議題兩極化。更荒謬的是,荷蘭動物黨這個「動物警察先驅」公開承認:動物警察的理念來自Discovery Channel的一個電視節目《Animal Cops》。
看到這裏,矛盾越來越大,系統一會告訴你不要看下去,也可能你啟動了系統二,分析以上的資訊。但康納曼也解釋:系統二除了批判系統一的偏見,更傾向於找證據支持系統一的良好感覺。於是乎,有記者打電話給紐約的「動物警察」(2012/12/18 AM730《動物警察全球大勢》),找證據印證香港的「落後」。可是,紐約的「動物警察」事實上不是警察,甚至從未自稱「警察」(你可以上他們的網頁看看),他們是美國防止虐待動物協會(ASPCA)的人員,其背景(由前警官領導的NGO)、職責(負責搜證再交由警察介入),基本和香港愛護動物協會的人員一樣。和香港不同的,是他們部份有槍(注意美國槍械管制跟香港不同),以及破案率比香港低。這位記者寫的故事是否完整,對受眾未必最重要,重要是他把故事和偏見編出連貫性,贏了話題,卻經不起驗證。
單從否定外國動物警察成效,不足以否定其可行性,但如何做、誰人做,必須要有人提出更有建樹的建議。有些人在推動這個議題期間,經常誤導和流於情感,有時更用憶測和武斷的方法,批評以往的案例,質疑攻擊警方、漁護署、SPCA,甚至政府法證。面對複雜的問題,人類傾向找最簡單的答案。動物警察看似解決虐待動物的捷徑,可是了解越多就越清楚:改善落後的法例、要求市民更主動協助舉報調查、管制動物買賣和過度繁殖等等,更複雜、更難「口號化」的問題,才是更好的答案。
大家同為動物出力,也是非牟利機構辛苦經營,理應是共同進退的朋友,不應在真相缺席下互相攻擊。避開情緒化、即食思考、避免被偏見左右,才能共同為動物謀福利,共勉。
作者:柳俊江
(mailto:[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