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近幾個月,梁振英的僭建新聞日日新奇日日鮮,他家那間消失的密室令我們大開眼界。不過,我今日並不想講梁某人,反而想說,我們雖然沒有消失的密室,但卻有很多消失了的公共空間。今個月初我的台灣之行,更加令我體會到,喪失公共空間的社會,很難令到人對其產生感情。
查實在台灣的會議,有一個講題是講到公共空間和公共藝術的關係,由來自台灣、深圳、上海和香港的代表,各自表述。又查實,大家可能會覺得,「公共空間」這四個字好像很學術很抽象又很悶蛋,其實所講的只不過是你我他都可以毋須消費、自由出入、自由享用的地方。簡單來說,那就是一處空地,你可以睡覺,可以跳舞,開心的時候可以和朋友坐着飲酒吹水,失戀的時候可以深夜在那裏喪喊。這處空地,就這樣記錄了你的生活點滴,而你,亦漸漸會對那個地方,產生感情,於是你會很願意去保護那個地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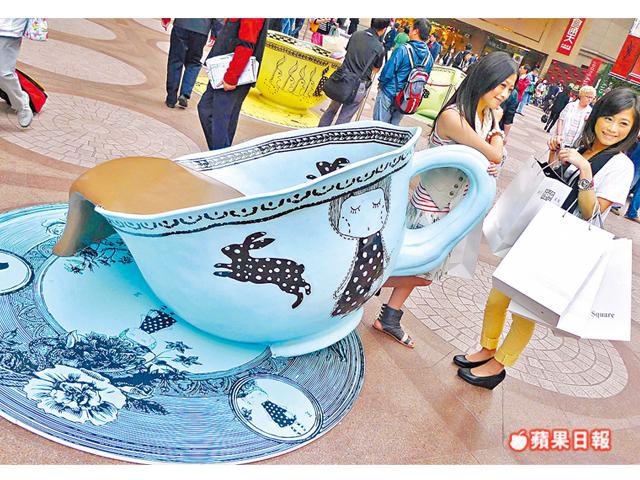
還記得,台灣的代表在講到他們怎樣去保護公共空間的時候,就提過「共同愛護」的觀點。話說,當地有人曾經為了保育兩條河流免遭破壞,於是就走去向河流周邊的農民、學校裏的老師學生下工夫,讓他們了解他們居住地方的點點滴滴,從而令他們愛上自己的土地、旁邊的河流,因為愛,所以懂得保育。
說來說去,就是怎樣令到一群人對自己所處的土地,產生感情。台灣這方面做得很好,況且台灣並不是大部份地方被地產商霸佔,有很多公共空間,再加上政府和民間在保存台灣歷史、原住民文化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代代承傳,所以不論是台灣的外省人抑或本省人,不論政見,都對自己所住的地方有很強烈的感情。
這就好像樹苗的成長,抓緊了土地,根也就能變得強壯。從來,根和土地是互相依附、不能切割的;沒有土地,我們很難找到根。

至於我們香港,說來真令人慚愧,我們的公共空間很多都落入了地產發展商的「管治」當中。由發展商去管理公共空間,很荒謬。結果,他們在賣樓之餘,就趁機將本來屬於大家的公共空間,據為己有。有些發展商索性將樓盤旁的公共空間封閉,禁止「閒人」進入;另外有一些發展商,就側側膊將公共空間變成路人很難進入的地方,路人要繞一個大圈才能找到,結果,本來屬於我們的地方,就成為了發展商的樓盤的後花園。
最經典的例子,當然要數銅鑼灣時代廣場,竟然將公共空間出租來謀利;另外也不能不提中環的長江中心。長江中心那裏有一條可以通到花園道的行車通道,本來就應該是讓公眾人士使用,但一直放了一道閘,結果被記者揭發事件。至於旁邊的小花園,也是開放給所有人的,但那個「Public Open Space」的標誌卻細得可憐。

我們住在市區的人,總不能一有甚麼喜慶事、失意事,就老遠跑到郊野公園去發洩一番,在城市裏面(包括最高地價、甲級租金的地方)總要有多一些能夠讓人自由聚集、透透氣的地方吧!
還有,城市並不是一定很乏味,其實我們可以將它變得很有人情味。深圳來的代表,在會議上舉了這一個十五年前的例子。話說,在深圳有一個公園,那裏放了十八個人物銅像,這些銅像不是甚麼領導人,只是十八名平常百姓。原來公園設計者在建構設計藍圖前曾就當地居民對公園落成後的願景做了一個調查,綜合結果後,設計者在十五年前某月某日的某一刻,找來在公園出現的十八個人,並向他們做了簡單的訪問,了解他們的工作、背景之類,更為他們鑄造銅像。在十年後,又再聯絡這十八人,了解他們的近況。當中,有南下找尋工作機緣巧合經過公園的小伙子,經十年努力成為著名設計師、有來自外省的公園阿嬸,十年來一直負責打掃清潔,居然成為了公園的代表人物,當然也有部份人是再也無法聯絡得到。

雖然有人說,公園裏那十八個銅像,早已日久失修。可是,當年的這份心思,記錄了那十八人和公園的緣份,實在令人感動。
很可惜,香港人講「地」,講的都是「賣地」;香港人發展「六大產業」,說穿了就是「六大地產業」。我們香港的土地,是用來出賣賺錢的,不是用來建立感情的。土地既是商品,我們也就成為了無根的一族。不過我相信,如果有一天,我們都能懂得愛護這片土地,我們就會生活得更好。
(台灣行系列之二.完)

作者:陳淑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