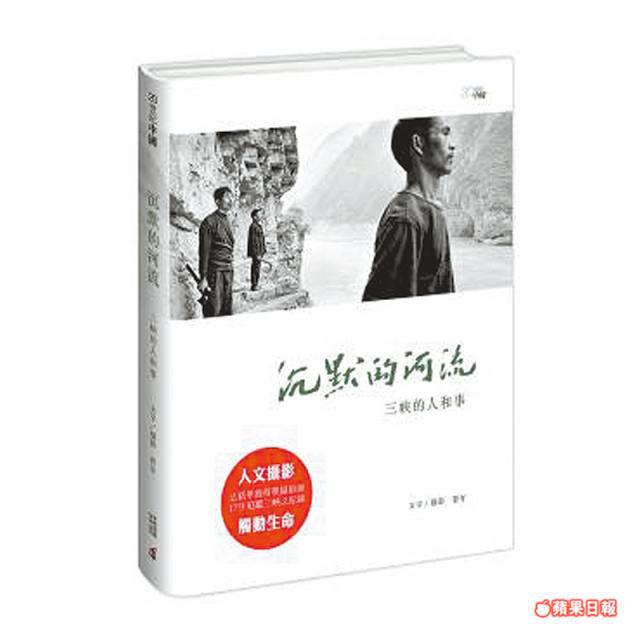
長江──世界第三大河流,四千五百萬年間,它見證了中華民族的興衰。從前長江令人敬畏,如今三峽卻一直被改動,人類不再恐懼大自然了。九四年三峽工程開工,數千年來沿着它生活的人民,遭逢巨變。長江無言,但攝影師曾年鏡頭下記載的河流,卻有千言萬語。 記者:何兆彬 攝影:潘志恆
人需要敬畏
「你知道楚國宋玉嗎?他是屈原弟子,曾寫過一篇《神女賦》、《高唐賦》,非常有名,寫得很美。宋玉在《高唐賦》中記述,有一天楚懷王去了雲遊高唐,晚上睡覺,有一神女來主動獻身予他。懷王問:那以後我怎樣可以見到你?女說:我朝為彩雲,暮為行雨,朝朝暮暮,陽台之下。」自此,「巫山」、「雲雨」等字,都帶曖昧。曾年指着他的新書《沉默的河流 三峽的河流》中一幀照片,這黑白照片上,遠景迷迷茫茫處有幾座大山,還算浪漫,但近景是個破爛廟頂,上有一高架鐵路,橫江而過。這是扇沱王爺廟,也就是賦中的高唐、巫山一帶。這本書,收錄了曾年十七年來鏡頭下的長江,人民生活面貌的改變。
書中其中一章,江水上漲,看到快把神像淹過,嚇了一跳,三峽工程下,諸神都不保了,「我重返雲陽,看到長江不流了,然後,這個唐代的封廟本來被毀了,在文革以後又被重建,漲水以後又淹掉,現在變兩個下岩寺了……寫到最後,我提的問題,是人需要有個敬畏,不敬畏的話,會出問題的。虛雲法師說,人心若無敬畏,無惡不作,禍亂而成。」雖然作品具批判性,談到三峽工程的得失成敗,曾年說自己也在反省:「其實我也在自我檢討呀,我為了幾張照片,封面這個人,千里奔行,無所不用其極!我的邏輯,跟對自然不敬重的邏輯是一樣的,所以我沒資格說甚麼,今年我往返法國跟三峽,就有三次。所以談到對大自然的敬重,其實我本身就做不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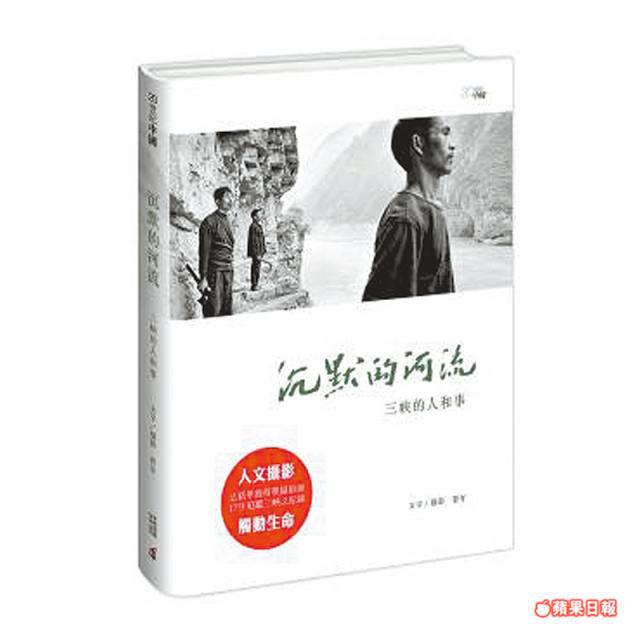
長江水手
很多人拍過長江,但曾年與一般攝影師不同,他與長江的淵源很深,移居巴黎多年的他,童年就在江邊生活。
「『煙籠寒水月籠沙, 夜泊秦淮近酒家。 商女不知亡國恨, 隔江猶唱後庭花』(杜牧《泊秦淮》)。」曾年:「隔江就是指長江,秦淮就是南京。我1954年在江蘇無錫出生,3歲到了南京。我對南京最早的記憶,就是父親帶着我,第一次帶我去坐輪渡,然後又坐回來,我印象很深。那叫中山碼頭,我們坐到渡口,再坐回來。」算起來,曾年今年58歲,一生都與長江有緣:3歲到南京、16歲開始在長江當水手、30歲到了北京,輾轉到了巴黎,當起攝影師,卻又因為工作回到長江,一直拍到現在。「我是1971年1月份在長江當水手,當年16歲。剛開始去的時候我在駁船工作,駁船沒有動力,只是載貨,我那駁船不載貨,它載石頭,因為碼頭在江水衝壓之下,會造成塌方,所以需要石頭整固。當時1971年就有大型的塌方,因為當年北方有煤,南方沒有煤,所以北煤南運,17號碼頭能把火車車廂翻過去,把煤倒進千噸以上大駁船。如果17號碼頭塌了,北煤南運就要停了。」71年時值文革,少年時代,書當然不用念了,「書沒有念完,也沒有書念,有一批學生去了煤壙,另一批人去了軍工廠。當水手的生活很苦,簡直匪夷所思,他們根本不讓你睡覺,你去船上工作,他一星期才讓你回家一天。其他時間都在工作,船上年輕人有四個,還有一批老的水手,大家輪流睡覺。這樣子我一做,就做了十個月,之後去了一條拖船,叫『永紅號』。」



搶回來的相機
父親是畫家,又是大學教授,生他時已屆耳順之年,在小資文藝家庭長大,曾年自然受影響,「小時候自己去買一點相紙、顯影藥,等天黑就在家裏冲洗照片。」相機哪來?「共產黨來了以後,最愛把人分等級,我爸是教授,等級就比較高,高級的還有老紅軍,都住在比較高尚的地方。我們住的周圍,鄰居有些小孩是當紅衛兵的,他們可以去打人,去搶東西,他們把相機搶回來,我就去借來玩。」你有當過紅衛兵嗎?「我太小了,第一我當不上,第二,父親是老紅兵才當得上。共產黨把人分成不同階級,階級鬥爭你聽過吧?」這個拿國際新聞獎的攝影師,最初接觸的相機竟是搶回來的。
既是小資產階級,文革來了當然被批鬥,「父親被關起來,人去樓空,母親自殺了,她是1968年10月份死的。」當水手的日子,母親剛被迫死三年,年輕的小伙子年年睡在船上,「當時心靈上孤單,但人不孤單,幾個年輕人常在一起。」當水手以後,有了一點收入,他就買了一台蘇聯機,開始拍攝,同年紀的少年之中,曾年也不謙虛說:「這方面是比較出類拔萃了,大家都知道這個人會拍攝,會洗膠卷,會印照片。」30歲時,父親偏癱,因為在北京有一房子,就舉家搬到了京城裏休養,「但認真的想當攝影師,是到了法國以後。」在北京時,他認識了由法國來京學中文的法蘭西年輕女學生,二人1984年結婚,然後到了巴黎生活。曾太太後來再進修,讀博士,目前是巴黎東方語言大學的副教授。


長江斷流
1988年去了法國,他才開展攝影師生涯,當然不容易。起初太太幫他搭上了SIPA(國際圖片社),「起初不順利。我要到1994年攝影事業才有較大的定單,去拍大選題──6-20頁的版面,我記得第一個選題,是拍西藏的淘金。這在95年出版了,我的攝影事業就開始進入軌道了。」1996年,他在美國攝影界開始有點名聲了,接到了《紐約時報》的定單,要他拍長江,「因為94年三峽開工了,找華人拍比較方便。我第二次去,1996年9月份的時候,我就決定要把長江發展成為一個個人系列。當時我帶兩個、有時是三、四個相機,拍膠片(菲林)。」他在2010年先在法國推出過法文攝影集,去年認識了深圳的中和出版,就談起了推出中文版。拍了多年,拍到水淹古廟,再目睹長江斷流,他說的確很震驚,「河流河流,就是要流嘛!我很震驚,但無所謂悲或喜。人類如今也需要空調、要電,搞不好這些電就是來自三峽的。我沒有資格評論,但如果有一天我能回到1994年,如果我像在法國一樣,有投票權的話,對於三峽工程,我投反對票!」


後記
由96年因工作重返長江,到現在出書,曾年對長江、對國家、對攝影的感情都十分複雜,打開電腦,給記者看他新作時,他順道開了一張在中國網上瘋傳的照片:一個女人軟癱在床上,旁邊有一初生嬰兒,血肉模糊,未知生死,「這就是國內的『強制生育』,這張照片可能只用個電話來拍,但影響力很大,比我的照片影響力都要大了。以往我們要拍照不容易,但如今人人能拍,我叫這做『照片的民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