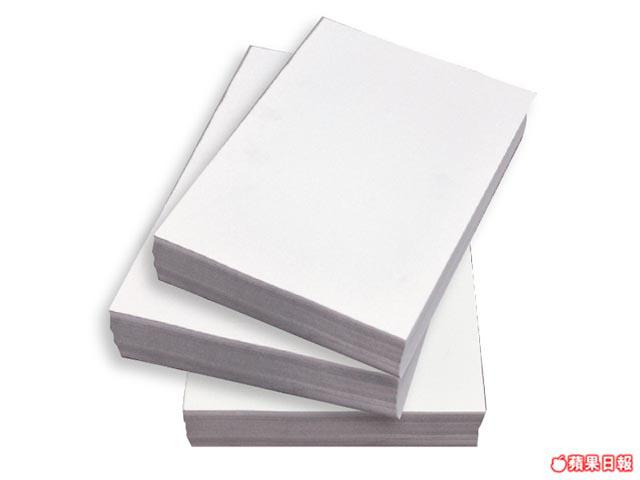人去旅行,我去旅行,眼睛卻總忍不住望垃圾。
北京頤和園,拎着一粒桃核找了好幾個垃圾桶,都寫着「可回收垃圾:瓶罐」,接收果核的,應該是「其他垃圾」。掃地的工人看見了,示意我隨便丟,一一探頭一看,所有垃圾桶的垃圾都混在一起,哪有分類?
慢着,一個老人打開垃圾桶,把膠瓶都撿出來,轉頭另一個女人也在撿,連工作人員亦悄悄收集一大袋,分類回收的速度,快得驚人。
陳曉蕾
關注可持續發展議題的記者,作品包括《剩食》、《有米》、《香港正菜》等,相信垃圾都是放錯位置的資源。

北京地鐵人來人往,幾位婦女大模大樣坐在地上:先把所有膠樽裏的飲料都倒在一個桶裏,再收集膠樽,經過的乘客隨手也放下飲品瓶子。連塑膠都能這般熱切回收,價值更高的廢紙、金屬更不用說,街上不時看見香港久違了的「收買佬」拉着車仔。好一個巨大的回收網絡!
只是看到當地如何回收廚餘,登時心情沉重,這網絡,是一雙雙人手扣起來的。
想像太古城一樣的大型屋苑,中產,每個門口都有保安嚴嚴守着,裏面公園、遊樂場、高級會所都不缺,但就在屋苑牆外一角的垃圾房,可是完全由人手撿垃圾。
那伯伯每天的工作,便是撕開成千的黑色垃圾袋,除了把瓶瓶罐罐紙張等挑出來,更會把裏面的食物拿出來:一整排巧克力、新鮮的番茄、當造的桃子、開都沒開過的醬料、白飯、剩菜、還有饅頭、饅頭、饅頭……
他連手套都沒戴。
「好浪費,甚麼都丟,我是種糧食的,看了特別心痛。」伯伯這樣說,然而臉上一點表情都沒有,似乎已經看習慣了。
滿地剩飯菜汁,中間一個鐵桶加一張木板就是凳子,一車車的黑色膠袋不斷倒在面前。扯開袋子,撿,金屬一堆、塑膠一堆、廢紙一堆,大多沾上食物殘渣好髒好髒,能用手挑出來的食物,放進麻包袋,一公斤五毛錢賣給養豬的。最後實在撿不下手的紙巾垃圾等,呼一聲,連破袋子丟在身後,那垃圾袋堆積如山!
站在伯伯身邊待了大半小時,臭死了!很難想像這樣從早上一直工作到夜晚,每一天。
臉書上人們留言:在菲律賓的貧民區,都是這樣撿垃圾啦;英國、美國這些地方,一樣有人撿垃圾啊。

可是,這不是貧民區,是高尚住宅的垃圾房,伯伯不是撿來去變賣,而是全職受薪的工作人員。物業管理處給了三萬塊一家公司處理,這間公司先以一萬元請大貨車把無法回收的垃圾送去掩埋場,再以七千五百塊外判給另一個回收公司,不同的收買佬開着小貨車,付錢買分類好的廢物,層層外判下來,坐在那裏撕開垃圾袋的伯伯,每月只是二千多塊錢。
伯伯在四川種稻米,農閒時來北京打工掙現金。
「回收」很容易變成神話,在街上隨手買一瓶樽裝水,「會回收啦。」彷彿那膠樽不再是垃圾,可是別說在香港塑膠回收無價,就算內地能夠回收,靠的也是這群毫無保障的人們。
酸餿的食物臭味,讓我記起更難聞的氣味,那是廣東省的貴嶼,汽車還沒駛進城,刺鼻臭味已經撲臉而來。
在這全球最大的電子廢物場,手提電話是這樣「回收」的:彷彿「烤魷魚」,工人就坐在街邊用鐵爐烤電路板,把焊接這些零件的鉛燒溶了,再用鑷子夾出晶片和各式各樣的電子零件。手機外殼的塑膠,打碎了,用鹽水浸完再「分類」,工人拿着打火機,燒每一塊碎膠,用的是鼻子和眼睛:會否變黑?會否冒煙?氣味如何?
燒板、燒膠,已經是「高級」的工種,通常是四川人才有機會,在貴嶼郊外的垃圾場,尿布、廚餘等各式各樣的生活垃圾都混在一起,安徽的農民工彎着腰撿破爛,最賤的街市背心膠袋,摔掉裏頭的髒東西便收集起來,回收價低至一毛錢一斤,到底要撿多少個才有一塊錢?
垃圾太多,有的垃圾場每晚都放火直接焚燒,那黑煙直衝上天,足球場大的火場,還看見有人影在撥動垃圾。
黑夜降臨,才是時候回收最值錢的電子廢物──電話、電腦、電視機等的電路板,上面的晶片都含有黃金,工人偷偷地在河邊,用純硝酸和純鹽酸等腐蝕液體要把這金「洗」出來。
翌日在那河邊,泥土是黑漆漆的化學物,空氣,是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