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陳曉蕾新書名喚《有米》,新書發佈會又派穀種,問她香港是否有人種米,她笑:「有呀,你要天真型,還是認真型?」所謂認真型,是真的有農夫想在香港復耕稻米,「我聽說剛剛有人租了塊農地,一租就三十年!」但她新書《有米》談的其實不是種米,而是香港人說的「有米」,即富有,「我的『有米』,其實是要用我的價值觀,指出香港人其實很富有!」
記者:何兆彬
攝影:林栢鈞
咁辛苦仲耕田?
因為想看香港本地種的稻米,記者叫曉蕾帶領入南涌看「天真型」農夫怎種稻米。早上還是陽光普照,中午落田時卻刮起橫風橫雨。我們到了南涌的農地,看到劃成一塊塊的農田,其中有幾格綠油油的稻穗,隨風飄揚。稻米剛結了稻穗,還是黃的。據業餘農夫介紹,一造米要種約120天,當稻由綠轉成金黃色,穗內灌漿,稻身變乾,就差不多是收成期了。這些稻田種了約三個月,「我的朋友業餘種米有十年了,失敗了又種,種了又不時失敗。」
雨剛下過,稻穗沾着雨點,更見鮮綠,不遠處,七八隻麻雀在稻田間飛舞。「看!雀仔要來吃了,所以農夫們要用帳篷保護稻米,如果沒好好保護,收割時可能只剩兩成。」耕田要睇天做人,又未知收成,還要餵雀,為何有些香港人這樣子一種就十年,況且農田沒多大,就是十足收成,也不過是幾碗飯!為甚麼這樣的儍事還有人做?這就要回到本篇的主題——有米。
曉蕾打自己工做獨立採訪,專攻綠色生活,她書中談的「有米」,其實是另一種生活形態,「有米即係有錢,我不是教人種米,我是想用我的價值觀講香港的富有,當然不是說有幾千萬也不夠分那種令人沮喪的價值觀!我可能在臉書多,年輕人很受這種價值觀影響,他們會覺得買不到樓就結不了婚,就沒有前途,很灰似的,雖然你也會見到他們很積極參與社會運動,但價值觀很單一。

悲觀地天真
「這本《有米》是從二十萬字之中,選八萬字出來,我很想擴闊大家的價值觀。」曉蕾回看自己的連載文章時,「我發覺自己建構了一個綠色香港,這是很少人見到的。我覺得香港社會已很灰心,公民社會不斷被收窄,不管是採訪自由,還是其他事情……我覺得,這是一本打氣書!香港是很有米的,例如自然資源。」她說,只要你夠硬淨,例如像龐一鳴,例如像示威番茄(一個在佔領中環期間常到現場煮番茄的廚師),那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不是沒可能。「茹國烈評我的書說,讀後『覺得充滿力量,我也可以做一點事』,這個我從來沒有想過,這本書對我來說,也是個開始。」
近年的她以獨立採訪生活,但在香港出書是沒多少收入的,《剩食》大受好評,賣了也不夠一萬本(作者一般只收書價十分一);另一邊廂,她接了幾個專欄,替報紙/雜誌寫報道,賺取生活,同時儲稿,「每星期寫一篇,唔覺唔覺,但結集成書,又好像有個群體出現了。」形容種米農夫,曉蕾會把他們分為「天真型」(業餘)及「認真型」(專業),她說自己也是sometimesnaive:「不過我不是幼稚地天真,反而係悲觀地天真!因為對大環境是十分悲觀的,我不會告訴你做記者好容易,我也不會告訴你在香港生活很輕鬆。人生只能活一次,你一係悲觀,一係樂觀!我當然是樂觀。」




我不會失敗
樂觀也總不能盲目。雖然人人都曉說「筆比劍更有力」,但你總得相信自己能改變世界,否則一切都是枉然。「從前我是較悲觀的,但到了三十歲,我告訴自己我要開心,要積極,我要看自己擁有的。」她樂觀,只是因為她今天的路是個人選擇。本來找她談綠色採訪,她卻多次忍不住講到公民社會的收窄,「看看近期的回歸十五周年專題,有無搞錯,為甚麼香港會變成這樣?當你見到所有事都這樣,社會行動當然很重要,但我覺得生活上,抗衡和找到自己的空間,同樣重要。」
如今被標籤為綠色記者,這條路,始於早年她在《明周》工作,「當年我寫教育及環保等。最先我想寫教育,但失敗了。我記得當年有個台灣教育家李雅卿來香港演講,有個孩子問她:『如果你失敗了,怎麼辦?』她答:『其實我不會失敗的,我只會遇到困難的;當遇到困難,你面對它就可以了。』在我的採訪路上,其實是沒有失敗的,但就不停的撞牆,那怎辦?惟有再站起來。」她一開始只想寫深度報道,但寫教育失敗後,去了教書,後來地球之友找她寫《夠照》,「那剛好是我最忙最不在狀態時,所以有點內疚,但它幫了我很大的忙,因為後來環保署也找我寫了四本環保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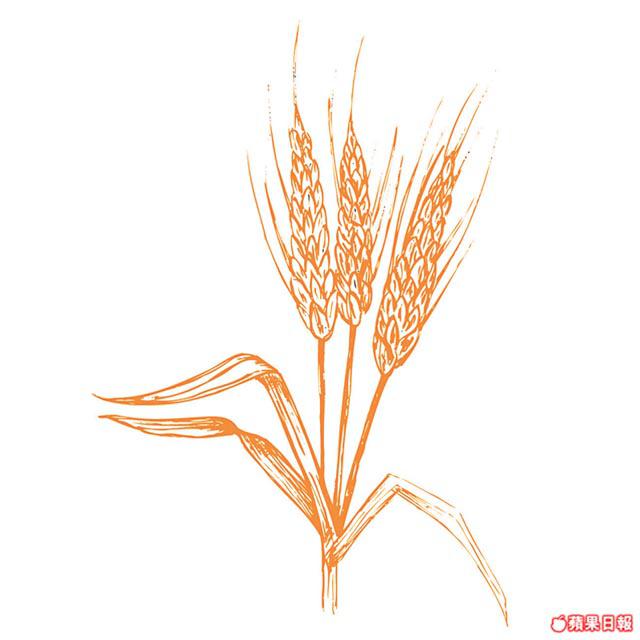
綠色採訪之路
誤打誤撞下,她走上綠色採訪這條路。「我真的被那些氣候變化的數字嚇怕、打動了,天氣怎變化,地球怎樣沒有魚,二氧化碳怎飆升呀、水怎樣不足呀、地球現在有幾人呀……這些之前都知道,但只要你認真面對,就不得不細讀。本來我也想過《剩食》後要寫別的,不想給人家看扁,以為我只會寫綠色,我想過寫本關於立法會的書,但時間有限。」今年選舉年,曉蕾看着大家很緊張選舉,又同時會比較另一議題:「我們的垃圾問題也很嚴重呀!你明不明,一個人你吃多少,跟你去不去拉屎是很重要的嘛!但在香港,人們不停的shopping,但竟然不處理垃圾問題。」
她剛去了台灣領獎,順便採訪,深受感動,「香港人去小店竟然是買大企業的商品,但台灣支持小店,是支持那些婆婆媽媽本土生產的醬料。我七一也會上街爭取普選,但除此之外,我見到環境議題不能再這樣下去,全世界講緊碳排放、碳稅,但這些題目香港竟然沒有人談。」她發現,台灣的綠色出版發達到有專門的設計師(王春子)。王春子一家來到香港,在曉蕾鄉郊的家中住了數天,「她們沒見過香港原來也有這麼大的鄉村,一住之下,就發現原來香港政府咁有錢。這麼大的公廁,有垃圾站,還天天有人來倒垃圾,因為在台灣鄉間是沒有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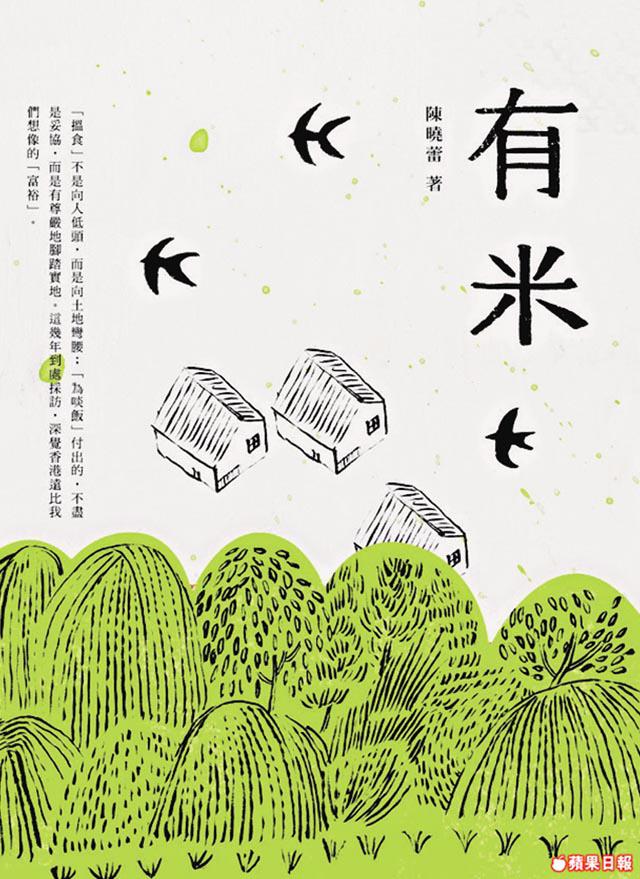
背靠大自然
訪問前,曉蕾剛由港台做完錄音過來:「主持人劈頭就問我:現在的工作方式是對你是最容易了吧?我不禁激動起來:都不是咁容易的,念念碎了一堆:連影印報告都不易,又沒有大學圖書可申請……做獨立採訪甚麼資源都沒有,未來我想寫本關於水的書,但旅費都不易籌集。我去申請資助,就怎麼都申請不了,很沮喪,有時我也想出月薪的呀!」她苦笑。
寫寫寫,會否覺得自己要寫的,剛好與地球浪費的大潮流相反,只會成為歷史的裝飾品?曉蕾豪氣的笑說:「不!我覺得未來十年,個個都要讀我的書呀,哼!為甚麼?不是因為我背後有大財團,而是有大自然。大自然想你珍惜水、資源、糧食時,這些提醒會越來越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