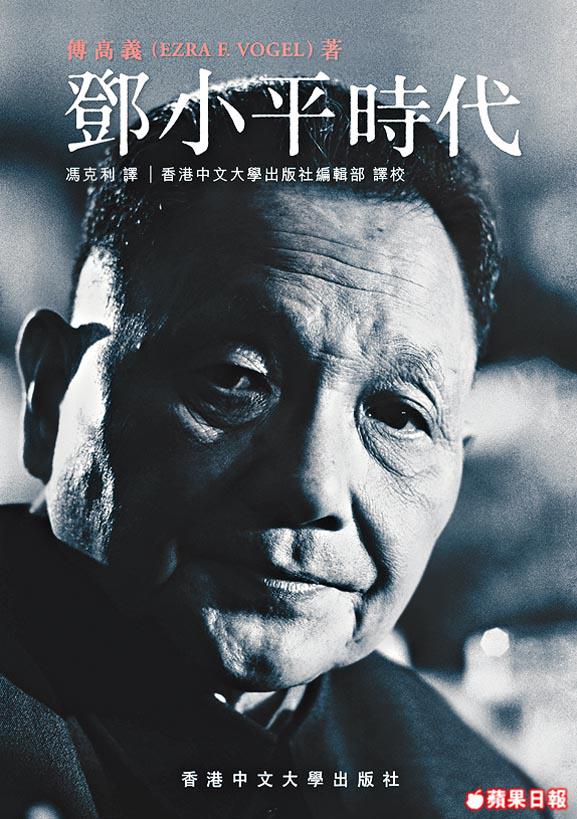
傅高義(EzraF.Vogel),哈佛大學亨利·福特二世社會學榮休教授,退休後,傾十年之力寫成一部迄今為止最權威的關於鄧小平的巨著DengXiaopingandtheTransformationofChina,中文版將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出版。本文是節選。
布熱津斯基訪華後,中美兩國開始秘密協商關係正常化談判的架構。雙方從一開始就認識到臺灣問題是決定談判成敗的關鍵。萬斯在6月28日將美方關於關係正常化談判的建議電傳給伍德科克,讓他轉交黃華外長:如果美國人民和臺灣人民的文化與商業交往能夠得以繼續,同時中國和平解決臺灣問題,那麼總統準備在中國宣佈的三原則框架內實現關係正常化。談判將在北京每兩周舉行一次,依次討論關係正常化之前需要解決的一系列問題。伍德科克還建議,在北京的例行談判中,雙方首先討論關係正常化之後美國在臺灣存在的性質和正式建交公報的性質。這就是說,雙方首先處理比較容易的問題,以便使談判取得進展,然後再處理更棘手的問題,例如美國的對臺武器出售。他們的目標是在12月15日之前,即美國國會選舉幾周之後達成一致。第一次會談於7月5日舉行,歷時40分鐘,雙方協商了程序,就各自對臺灣問題的立場作了初步的一般陳述。
在中國方面,鄧小平雖一直關注着談判過程,但直到最後才直接加入到談判中。最初參與談判的黃華外長在與美國人打交道方面經驗過人。1936年他曾帶着埃德加.斯諾(《西行漫記》的作者)從北平去陝北見毛澤東。他在毛澤東、周恩來和鄧小平這三位風格迥異的領導人手下都工作過,文革期間他一度是中國唯一的駐外大使。他對沒有得到授權的事從不多言,能夠如實傳達鄧小平的情緒,不管是憤怒還是善意。1971年他赴紐約擔任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任駐聯合國大使。在與美國關係正常化的談判中,他有兩個助手章文晉和韓念龍,二人都是擅長跟美國人打交道的出色外交官。
雙方派到談判桌上的都是一流團隊。卡特選擇伍德科克這個勞工領袖和專業調解人擔任大使級的駐華聯絡處主任,是因為他很看重伍德科克的談判技巧,還因為伍德科克在華盛頓政壇人脈甚廣,不管他與中方可能達成怎樣的協議,都將更易於得到國會的支持。伍德科克能利用他和華盛頓政治領袖的個人關係,協調那些一般官僚程序難以解決的政策問題。伍德科克有着強硬而可靠的勞工談判人的威信,素有誠懇正直的名望。萬斯國務卿把伍德科克稱為「天生的傑出外交官」,說他具有「照相機般的記憶力、周全的思慮、以及在這些談判中起着關鍵作用的精準措辭」。國務院和白宮都對伍德科克十分信任,因此認為沒有必要讓一名華盛頓高層官員來回奔波。談判開始時,伍德科克已在北京擔任了一年的聯絡處主任,也得到了北京官員的信任,他們願意接受這位談判對象。
芮效儉(StapletonRoy)於1978年到達北京,接替大衞.迪安(DavidDean)擔任了談判團隊的副手。他在南京長大,其父是從事教育的傳教士。他能講漢語,精通中國歷史,被視為國務院最能幹的年輕專家之一。在白宮,卡特總統、副總統沃爾特.蒙代爾(WalterMondale)、布熱津斯基和米歇爾,奧克森伯格通過高度保密的渠道直接與伍德科克和芮效儉聯絡。布熱津斯基的中國事務助手奧克森伯格是一個大膽而視野開闊的戰略家,也是一個有着無限好奇心與熱情、熟諳中國問題的學者。在華盛頓,白宮之外只有幾個官員是知情人,其中包括萬斯和國防部長哈樂德.布朗(HaroldBrown)。美方的談判策略是在伍德科克提供的信息基礎上由白宮制定的,白宮也同中國駐華盛頓聯絡處的柴澤民及其副手韓敘保持着接觸,但談判全部是在北京進行的。
鄧小平一直關注着黃華與伍德科克的談判(7月5日、7月14日、8月11日、9月15日和11月2日)以及黃華生病期間韓念龍與伍德科克的談判(12月4日),後來他又親自與伍德科克進行了談判(12月13日上午10點、12月14日下午4點和晚上9點、12月15日下午4點)。在談判期間,鄧小平繼續會見美國官員,向他們解釋中方的立場,並通過施壓推動談判。例如,7月9日,即伍德科克和黃華舉行第一次會談四天後,鄧小平對眾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主席萊斯特.沃爾夫(LesterWolff)率領的美國國會代表團說,同意與臺灣維持全面民間交往的日本模式,中國是已經作出了讓步的。鄧小平說:「我們會盡量創造條件,用和平方式解決這個問題。」他解釋說:「實現關係正常化,對我們雙方對付蘇聯都十分有利。」鄧小平絲毫沒有向沃爾夫暗示談判已經開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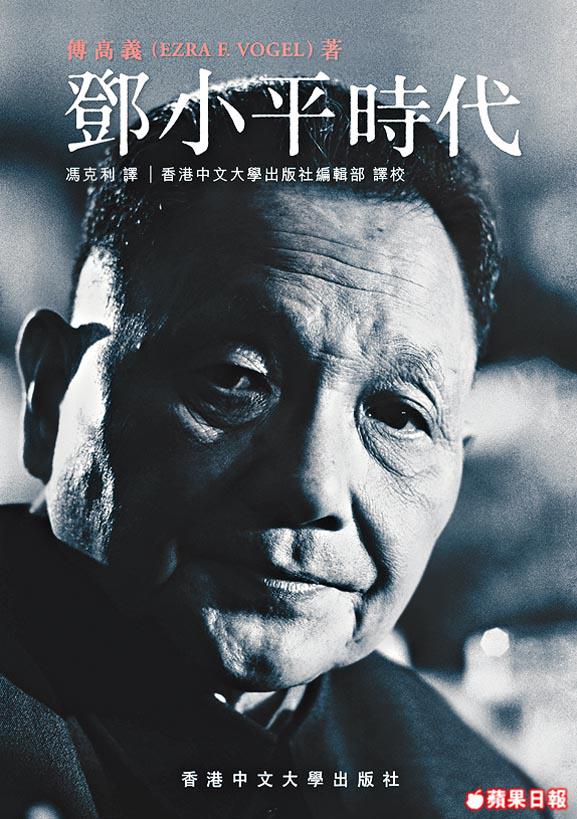
在談判中,中方通常傾向於從一般原則開始,然後再轉向細節。黃華在7月14日與伍德科克的第二次談判中說,中方建議不再一次只談一個問題,美方可以首先把全部重要問題都擺到桌面上,由雙方作出一攬子的評估。此後幾天,在華盛頓方面美方的意見分歧得到了解決,因為他們接受了伍德科克的建議,即為了給下一步會談創造良好氣氛,美方應當接受中國的提議。隨後雙方準備並互換了一些關於需要解決的關鍵問題的文件。在第三次會談中,美方概述了同大陸關係正常化之後美國與臺灣關係的性質:文化、商業和其他交往將會繼續,但是不會派駐美國政府官員。
談判中最大的難題是:美國是否繼續向臺灣出售武器。美方明確表示它打算繼續對臺售武,但是每一次提出這個問題,中方都回答說,他們堅決反對。鄧小平本來希望,只要美國同意停止對臺售武,臺灣會感到現實的出路只能是同意與大陸重新統一;他希望這件事在他當政期間就能很快實現。
在表明自己的立場時,中方堅持他們對《上海公報》的解釋,即美國支持「一個中國」的政策。事實上,尼克遜在簽署《上海公報》時只承認了海峽兩岸都堅持只有一個中國,美國對這種觀點不持異議。9月7日,副國務卿理查德.霍爾布魯克(RichardHolbrooke)對韓敘說,美國賣給臺灣的任何武器都僅僅是具有防禦性質的。韓敘則回答說,「對臺售武不符合《上海公報》的精神」。卡特在9月19日會見中國駐美聯絡處主任柴澤民時對他說:「我們將繼續與臺灣開展貿易,包括有限地出售一些經過仔細挑選的防禦性武器。」柴澤民說:「美國繼續向蔣經國集團﹝1975年蔣介石去世後,其子蔣經國成了臺灣的領導人﹞出售武器,這不符合《上海公報》的精神。」10月3日黃華在聯合國見到萬斯時,又在事先準備好的聲明中重申,繼續把武器賣給「蔣經國集團」違反《上海公報》的原則。
鄧小平在10月初出訪東京期間公開宣佈,只要能夠遵循日本模式,他願意同美國實現關係正常化。中國反對美國對臺出售武器的立場沒有動搖,但是他說,他不反對美國和臺灣繼續進行經濟和文化交往。
卡特和布熱津斯基在10月底開始擔心,儘管他們小心地限制談判知情人的數目,倘若問題不能很快得到解決,走漏風聲的危險將變得越來越大。布熱津斯基告訴柴澤民,中國如果不抓住這個機會實現關係正常化,由於政治糾紛,在1979年年底之前將無法再對這些問題進行任何嚴肅的討論。沒過多久,美國就宣佈與臺灣達成協議,美國將繼續向臺灣出售F-5E戰鬥機,但不會出售更先進的戰機。
這時雙方已經完成了大部份談判,伍德科克在11月2日交給中方一份計劃在次年1月公佈的建交公報的草稿。然而中國國內正忙着應對在11月10日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出現的戲劇性變化,因此直到12月4日才作出回應。鄧小平本人在11月5日後一直在東南亞訪問,14日回國後又立刻參加了中央工作會議,正是在這次會議上他成為了中國的頭號領導人。
11月27日,即華國鋒在中央工作會議上接受了對他的立場的全部批評、並實際認可了會議對鄧小平擔任頭號領導人的共識的兩天之後,鄧小平接見了正在亞洲訪問的華盛頓著名報紙專欄作家諾瓦克。自從1971年周恩來在尼克遜訪華前夕接見詹姆斯.萊斯頓(JamesReston)以來,這還是中國主要領導人第一次同意接受美國記者的採訪。鄧小平對諾瓦克說,中美兩國應盡快實現關係正常化,這不但有利於兩國,也有利於全世界的和平與穩定。諾瓦克向美國民眾如實公佈了鄧小平的談話內容,他的結論是:「我相信鄧小平花兩個小時與我在一起,是要向華盛頓傳遞一個信息,他要盡快實現關係正常化,卻不會為此付出很高的代價。」諾瓦克當時並不知道鄧小平不久就會訪問美國,而這次訪談有助於美國公眾對鄧的到來有所準備。
12月4日伍德科克與已成為外交部代部長的韓念龍(代替生病的黃華)的談判,是11月2日後的第一次會談。中方已經知道、但美國還被蒙在鼓裏的一件事是,華國鋒在11月25日已將第一把交椅讓給了鄧小平,而且接受了鄧的政策。12月4日中方突然變得十分積極。韓念龍交給伍德科克一份中方宣佈關係正常化的聲明草稿,其中只對美方草稿作了稍許修改,並提出將1月1日作為公佈聲明的最後期限。韓念龍明確地說,美方如果發表聲明,表示希望和平解決臺灣問題,中方不會加以反對。會談結束後,伍德科克正要起身離開,韓念龍對他說:「最後我想告訴您,鄧副總理近日希望見您一面。我們會通知您確切的日期。」伍德科克在給華盛頓的分析報告中說,韓念龍仍反對美國對臺售武,但他的結論是這個問題不太可能成為關係正常化不可逾越的障礙。由於美方不知道將與鄧小平見面的確切時間,伍德科克讓芮效儉取消了一次預定的出訪,以便能夠隨時和他一起去見鄧小平。
同時,華盛頓時間12月11日下午(北京已是12月12日),鄧小平會見伍德科克的前一天,布熱津斯基在華盛頓接見了柴澤民,交給他一份經過修改的聲明草稿,並對柴澤民說,美方準備接受將1月1日作為建交日期,美方邀請一位中國領導人在達成協議後盡早訪美。當時華國鋒的正式頭銜仍在鄧小平之上,美國估計中國會讓華國鋒或鄧小平出訪。布熱津斯基還提前通知柴澤民,美國可能在1月與布列茲尼夫舉行峯會。
鄧小平在12月13日星期二的上午會見了伍德科克,地點是人民大會堂的江蘇廳。彼此寒暄了幾句後,伍德科克交給鄧小平四份只有一頁紙的英文公報草稿。鄧小平沒有等待正式的譯文,而是請譯員做了口頭繙譯,在沒有中文文稿的情況下便直奔主題,他顯然不想拖延取得進展的時間。鄧小平問,既然廢除了美臺防禦條約,美國為何還要一年時間才從臺灣撤軍?伍德科克解釋說,美國打算在1月1日與臺灣斷交,現在的條約規定終止條約要提前一年通知對方,儘管美國事實上打算在四個月內從臺灣撤出軍隊。鄧小平說,這個方案可以接受,不過他希望美國乾脆刪除所有提到第10條(其中規定終止防禦條約要提前一年通知對方)的地方。他還表示,希望美國在這個期間不要向臺灣出售武器,因為如果美國這樣做了,「蔣經國就會翹尾巴,這將增加臺灣海峽發生衝突的可能」。
鄧小平注意到,公報的中文稿中有反霸權的條款,美國的稿子卻沒有。他說,美國的稿子令他滿意,但是希望美方在共同聲明中加上反霸權的條款,不然會讓世界覺得雙方存在分歧。伍德科克說,他會將鄧小平的意見轉告華盛頓並等待答覆。鄧小平同意1月1日是宣佈關係正常化的一個好日子。
在答覆美國向中國高層領導人發出的訪美邀請時,鄧小平說:「我們接受美國政府的訪問華盛頓的邀請。具體地說,我會前往。」當天下午,由於知道中美建交問題已基本得到解決,鄧小平在中央工作會議上作有關改革開放的劃時代講話時,顯得更加躊躇滿志。
次日,即12月14日,伍德科克和鄧小平預定在下午4點再次見面,但是伍德科克仍未收到華盛頓的指示。因為華盛頓那個小團隊正忙得不可開交,他們在努力配合卡特的新計劃,趕在次日即華盛頓時間12月15日完成關係正常化的聲明。此前由於白宮的人員全力以赴,急於趕在1月1日前完成所有細節,其他官員開始懷疑他們是否正在搞甚麼名堂。卡特為了防止洩密突然惹惱國會,致使整個計劃泡湯,遂決定加快行動,提前到12月15日而不是第二年1月1日宣佈中美建交。正式公報將在關係正常化之後的1月1日公佈。華盛頓那個秘密參與談判工作的團隊,需要努力在主要參與者之間取得共識,還要起草文件,籌劃對付國會的策略,並考慮商業、軍事和學術活動所必須的各種調整。為了趕上突然提前的新期限,他們正全力衝刺,已經被推到了崩潰的邊緣。國務院的中國問題專家羅傑.沙利文(RogerSullivan)也應白宮之邀向國務院告病三天,加入了白宮緊張忙碌的秘密工作,幫助準備所有必要的文件。
美方的北京團隊也在忙得團團轉。30年後,北京的美國大使館搬進一座新建築時,已有1,000多名工作人員,而1978年的駐京聯絡處只有33人,而且其中只有幾個人參與了這項高度保密的準備工作。此外,就像華盛頓的團隊一樣,他們本來也預期在1月1日前完成所有關係正常化的談判和文案工作,現在為了在12月15日這個新期限之前將一切準備就緒,他們需要全力以赴。
當鄧小平和伍德科克在北京時間12月14日下午4點會面時,由於華盛頓的指示未到,他們沒有談實質問題,只談了關係正常化的日程表和鄧小平未來的訪美計劃。鄧小平接受美國加快宣佈兩國關係正常化的要求,並同意在1月28日這個美方認為方便的時間動身訪美。然後兩人休會,同意在伍德科克收到華盛頓的指示後,於當天晚上再次見面。
在當晚9點的會談中,鄧小平和伍德科克討論了對聯合公報的措辭所做的一些微調,雙方很快便達成了一致,並同意由章文晉和芮效儉共同對措辭進行核查,以確保中英文文本的準確性和一致性。華盛頓接受了伍德科克的建議,同意中方列入反霸權條款的要求,因為《上海公報》中已經包含這一條款。會談的氣氛反映出雙方都相信他們已經達成一致。伍德科克在給華盛頓的會談報告中說:「鄧小平對我們的會談結果顯然十分高興,把它稱為最重要的事件,還希望向總統、萬斯國務卿和布熱津斯基博士轉達他的謝意。」伍德科克向華盛頓報告說,會談「進行得一帆風順」。
與此同時,布熱津斯基在與中國駐華盛頓聯絡處交談時,吃驚地聽到聯絡處主任柴澤民仍然認為美國已同意全面停止對臺售武,他擔心北京可能誤解了華盛頓要繼續售武的決定。美方答應鄧小平的要求,在1979年不向臺灣出售新的武器,但美國打算以後恢復對臺售武。由於卡特、布熱津斯基和奧克森伯格開始集中考慮如何向國會解釋關係正常化協議,他們擔心國會會立即將注意力集中到對臺售武的問題上。如果北京仍然認為未來不會再有對臺售武,那麼美國一旦宣佈出售武器,將會給正在恢復正常化的美中關係造成嚴重後果。
風險之大不言而喻。在這個關鍵時刻,對鄧小平宣稱的不可動搖的「原則」的誤解,足以使兩國關係出軌。因此布熱津斯基發電詢問伍德科克,他是否確信北京已經對繼續對臺售武表示諒解。伍德科克和芮效儉馬上擬好了電文,其中說,雙方已把各自在軍售問題上的立場明確記錄在案。伍德科克回覆布熱津斯基說,他們此前已向中方講明:「正式建交不排除美國人民繼續同臺灣人民保持一切商業、文化和其他非官方聯繫,我在12月4日已經就此向代理外長韓敘作了說明。」他在電文中又說,代理外長韓敘確實提出「明確反對建交以後向臺灣出售武器」。收到伍德科克的電文後,卡特總統和布熱津斯基認為,在鄧小平是否明確理解了美國將在1979年以後繼續出售武器這一點上仍存疑問。於是布熱津斯基又致電伍德科克,讓他再去見鄧小平,毫不含糊地表明,假如國會提出對臺售武問題,他們出於政治原因不可能回答說1979年以後不再恢復出售武器,但是美國在出售武器時會有所節制。
鄧小平答應了伍德科克要與他再次會面的緊急請求。他們在北京時間12月15日下午4點見面時,伍德科克感謝鄧小平願意這麼快就與他見面。他解釋說,本着完全坦誠的精神,卡特總統「要有絕對把握不存在任何誤解」。他接着宣讀了白宮發來的聲明,其中解釋說,鑒於美國政治的需要,美方會繼續對臺售武。鄧小平勃然大怒,但還是有所克制,他說,這完全不可接受。他發了十分鐘的火,然後怒斥道:「為何又要提出這個售武問題?」伍德科克解釋說,美方不想讓總統在其聲明中說一些讓中國感到意外的話。鄧小平接着說:「這是否意味着總統在回答記者提問時,會說美國將在1980年1月1日之後繼續賣給臺灣武器?」伍德科克答道:「是的,我們會繼續保留這種可能性。」鄧小平說:「如果是這樣,我們不能同意,這實際上會阻止中國以合理的方式,通過與臺灣對話解決國家統一問題。」他說,蔣經國會變得趾高氣揚,「臺灣問題將不可能和平解決,最終的選擇就是動用武力」。
這時伍德科克向鄧小平保證,美國將極其慎重地處理這個問題。鄧小平反駁道,中方早已明確表示不接受繼續對臺售武,他昨天就提到過這一點。伍德科克把責任攬了下來,他說,他本人大概有所誤解。鄧小平變得十分惱怒,伍德科克和芮效儉嚴重懷疑鄧小平是否還會同意關係正常化。
經過將近一小時的會談和連珠炮一般的反對後,鄧小平說,臺灣是唯一懸而未決的問題:「我們該怎麼辦?」伍德科克答道,他認為在關係正常化以後,隨着時間的推移,美國人會接受臺灣是中國的一部份,支持中國的統一––當時很多美國官員也和中國官員一樣,認為這會在幾年內發生。伍德科克說,頭等大事是完成關係正常化。鄧小平說:「好。」話音一落,僵局隨之冰釋。
會談結束時,鄧小平提醒說,如果卡特總統公開宣揚對臺售武,中方將不得不作出反應,任何公開爭論都將有損於中美建交的重大意義。伍德科克向鄧小平保證,美國將盡力讓全世界認識到,中美建交的意義正如雙方共同相信的那樣極其重大。鄧小平說:「好吧,我們如期公佈建交文件。」鄧沒有再和其他任何中國官員協商,中美建交一事就這樣塵埃落定了。
在美國繼續對臺售武的情況下,鄧小平依然決定實現兩國關係正常化。關於他本人在作出一生中這個最重大的決定之一時有何考慮,沒有任何紀錄可考。但他知道,這個決定將使他最珍視的目標之一––在有生之年看到臺灣回歸大陸––的實現變得異常困難。那麼他為甚麼還要同意呢?當時他剛剛在其勢均力敵的同事中成為中國的頭號領導人,他可能認為,實現中美關係正常化可以加強他在中國領導層中的個人地位。或許更重要的是,鄧小平還知道,與美國實現關係正常化,會讓中國更容易得到它在現代化建設中所需要的知識、資本和技術。布熱津斯基幾周前曾告訴柴澤民,美國政治提供了一個短暫的機會,如果他們不迅速行動,下一個機會就得等到1979年底了。多年以來,關係正常化的過程障礙不斷,鄧小平看到機會難得,他不想放過。
鄧小平當時的另一個重要考量,是蘇聯從南部對中國日益增長的威脅。他當時相信存在着很現實的危險:蘇聯有可能進入越南,經由泰國和馬來西亞向馬六甲海峽擴張。他認為,高調展示中美合作可以讓蘇聯變得更謹慎,還可以減少蘇聯對中國攻打越南可能作出反應的危險。鄧小平還知道,布列茲尼夫想在他之前訪問華盛頓,而與伍德科克達成協議很有可能使他搶在布列茲尼夫之前成行。鄧小平作出了深思熟慮的決定,因為他知道自己沒有足夠的力量使美國既同中國建交,又停止對臺售武。如果他想要關係正常化,他就得付出向美國對臺售武作出讓步的高昂代價。他並沒有放棄統一臺灣的目標。他會在中美建交之後,利用一切機會迫使華盛頓減少對臺售武。
中美建交協議在北京和華盛頓同時宣佈。北京時間12月16日上午10時,華盛頓時間12月15日晚9時,雙方發佈了聯合公報:「美利堅合眾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同意相互承認,並於1979年1月1日建立外交關係。」卡特總統向美國公眾作出宣佈。在中國,名義上仍然是國家元首的華國鋒舉行記者招待會宣佈了這一決定。這條新聞在北京播出後,不論在民眾中還是黨內,都呈現出一派歡欣鼓舞的氣氛。
蔣經國是在半夜被叫醒,得知即將發佈公報的消息的,臺灣人的憤怒一如北京人的欣喜。臺灣官員及其在美國國會的朋友怒不可遏,一些保守派也跟着聲討打算與「共產黨敵人」合作的美國官員。但是,文化差異極大的兩個大國將攜手建立一個更加和平的世界,這一前景無論對美國民眾還是中國民眾都很有吸引力。正如卡特總統本人所說:「我們本以為在全國和國會內部會發生嚴重對立,然而這並沒有成為現實……整個世界幾乎都是清一色正面的反應。」
傅高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