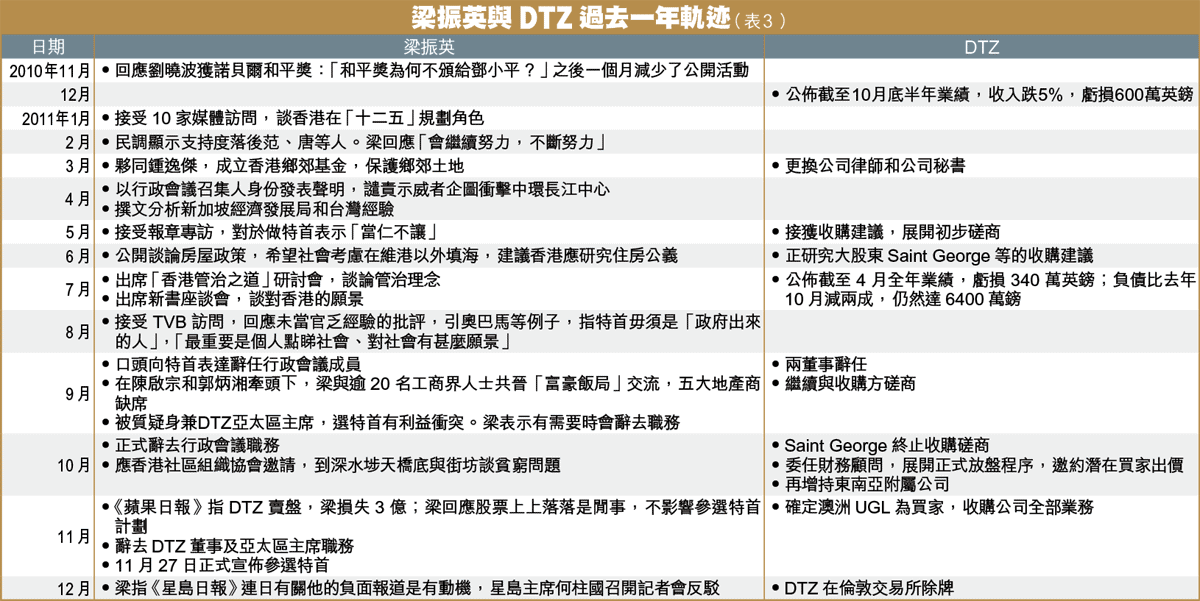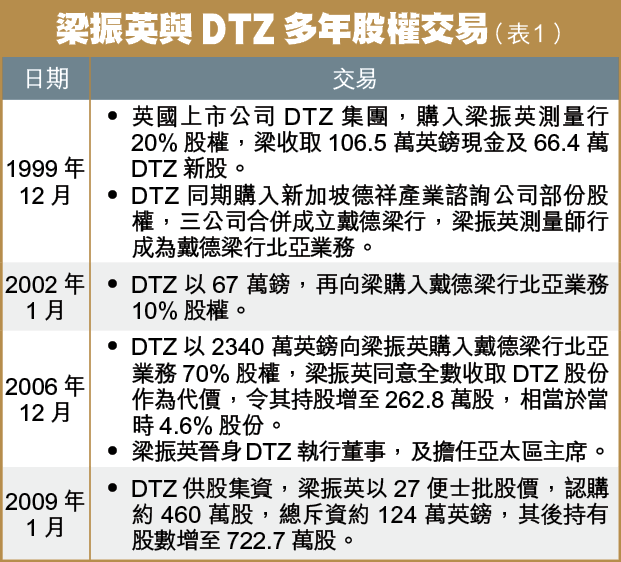
特首選舉的關鍵是政治,在《金融中心》版,政治課題我不敢在添馬男樓上班門弄斧。上星期分析星島集團主席何柱國在記招的言論,我主要從企業管治角度看,盡量避開主觀,特別是用上「狼」與「狠」等字眼。我本以為關於特首選舉的事情,我能發揮的地方不多,但過去1個月關於梁振英跟DTZ的關係,引起滿城風雨,很多人評論,但這些評論大都建基於零碎的事實,唐梁兩營在這事件上選擇性地互相攻擊,沒完沒了。
梁振英在DTZ的經歷,涉及到梁振英的管治能力,成為了特首選舉的一件大事。這件事覆蓋範圍伸延至上市公司企業發展、賬目分析、企業管治等課題,全是我的一杯茶,今日請其他欄目讓路,讓我以較大篇幅來分析梁振英DTZ之路。
梁振英跟DTZ關係重要之處,是他把半生事業上的心血出售予英國上市公司DTZ,選擇收取DTZ股票而不收現金作交易代價,兼且成為DTZ執行董事,所以DTZ的起跌跟梁振英有着直接的關係。首先要弄清楚DTZ最近發生了甚麼事,然後才分析DTZ過去一段時間為何會走上這條路,而這些事情跟梁振英有甚麼關係。
2011年11月8日,DTZ董事局宣佈澳洲公司UGL為優先收購者(PreferredBidder),雙方就關於收購DTZ事宜進行進一步談判,同時DTZ提出預警,由於公司債務規模龐大,股東能夠從收購獲得的價值將會有限。2011年12月4日,DTZ宣佈把所有業務售予UGL,並且進行清盤,即時在倫敦交易所除牌。DTZ出售公司得來的錢主要用來償還銀行債務,使股東持有的股票價值變成零,但所有DTZ屬下子公司的營運不受影響。即是說,DTZ的上市公司不再存在,它屬下子公司,包括負責亞太區業務的戴德梁行營運不受影響,只是控制權由DTZ轉為UGL持有。
亞太區業務正常 沒說錯
梁振英指DTZ亞太區業務運作正常,他說得沒錯,DTZ屬下子公司全部繼續正常營運,唯一牽涉清盤的公司是DTZ的控股母公司。因此,何柱國在記招指「阿媽都破咗產,個仔邊度有錢」,這說法是技術上錯誤。DTZ在進行清盤之前一刻把所有業務賣走了,的確出現資不抵債的情況,跟平常人心目中的「清盤」和「破產」無異,分別在於技術上而已。本文以「清盤」來形容DTZ的現況。
弄清楚現況之後,我想從兩個角度分析梁振英和DTZ的關係,從分析過程中可看到DTZ為甚麼會走上清盤之路,而梁振英在過程中扮演了甚麼角色。兩個角度包括:1、傳媒指梁振英「一鋪清袋」;2、親唐人士指從DTZ清盤,可推算梁振英的管治能力,特別是指他作風過份進取;對於這兩項說法,梁振英皆反駁是失實的。
1、梁振英「一鋪清袋」。梁振英把由自己創立的測量師行分3次售予DTZ,分別在1999年(出售20%)、2002年(出售10%)和2006年(出售70%)。採取分段出售方式,可反映梁振英是一個謹慎的人,先出售部份股份,建立關係,然後互相觀察,細看雙方是否合拍,再作下一步行動。
交易特別之處是,梁振英出售的代價以收取股票為主(表1)。3次交易中,梁振英合共收取了173萬英鎊現金和263萬股DTZ股票。在2006年的第3次交易,梁振英選擇全數收取股票。梁振英選擇收股票,原因一定是看好DTZ的前景,投下信心一票。
梁振英這些年來非但沒有減持,並曾經增持。2009年1月,DTZ開始出現財困,宣佈供股,梁振英斥資124萬英鎊,認購460萬股,持有股數增至723萬股。梁振英3次跟DTZ交易所得的現金,減去供股支出,淨收49萬英鎊。簡單說,梁振英把自己建立的事業全數售予DTZ,得回來的是723萬股股票,和49萬英鎊現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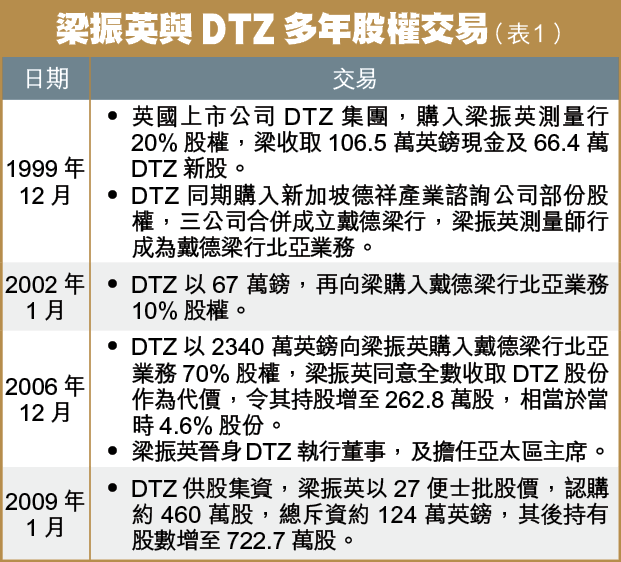
半生心血錯付DTZ 「一鋪清袋」非失實
DTZ股票的價值最後變成零,以「一鋪清袋」來形容梁振英在DTZ的遭遇,用詞可能刻薄,但並非失實。除了3次交易減去供股收購的49萬英鎊,梁振英在2006年從DTZ得到的,只是每年幾十萬至百多萬英鎊的董事酬金(表2),這是梁振英作為DTZ僱員的報酬,假如這段期間梁振英替其他公司打工,以他在市場的身價,收入肯定比DTZ的酬金高得多。梁振英把半生事業上的心血交託予DTZ,是客觀事實。
梁振英跟DTZ的交易代價,選擇主要收取股票,帶出一個很多人忽略的投資概念。交易中,賣方選擇收取股票,這決定其實包含了兩個動作:第一個是收現金,第二個是把同等金額現金買入股票;一個賣,一個買,很多人忽略了買的動作。
DTZ渴望打入中國市場,鎖定以梁振英持有的測量師行為工具,形勢是DTZ需要梁振英多過梁振英需要DTZ,我相信梁振英可以在收購談判中,要求全數收取現金。梁振英選擇收取股票,其實代表他把賣掉自己公司得到的現金,以市價買入DTZ股票,兩個動作同一時間進行。以2006年DTZ收購70%股權為例,梁振英全數收取股票,其實代表梁振英以當時股價每股7.2英鎊,購入263萬股DTZ股票(圖1)。
收取股票是一個由梁振英作出的投資決定,「馬後炮」看,這決定是錯。曾經犯錯的人可否勝任做特首?曾經作錯決定可否代表這個人其他決定也會出錯?我留給讀者判斷。
2、梁振英為DTZ清盤負上的責任:DTZ的業績於2007年到達高峯,股價最高升至8.3英鎊,市值達5億英鎊,梁振英在這時候進入DTZ董事局,DTZ往後發生的問題,梁振英需負多少責任?這是一個重要的問題,因為2007年至2011年是DTZ由盛極至衰的時期,這期間DTZ作出許多重要決定,其中部份決定「馬後炮」來看是錯誤,導致DTZ清盤,梁振英扮演了甚麼角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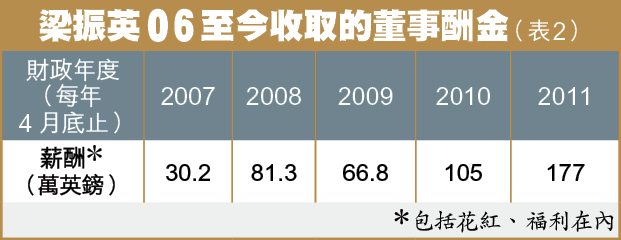
董事集體負責 梁責無旁貸
梁振英對於他在DTZ的具體權責問題,一直沒有作正面回應。我聽過有同情梁振英的人說過,他只是DTZ小股東,並且主力負責亞太區業務,而亞太區業務一直做得很好,是DTZ全球業務唯一亮點,DTZ清盤不反映梁振英的管治能力。
梁振英需為DTZ清盤負上甚麼或幾多責任,答案其實清晰,是全部,他的責任不比DTZ的主席和CEO小,因為他是DTZ的董事。董事局內實行董事集體負責制,不可能分割某董事負責某部份責任,兼且不能把責任推卸給下屬,亦不能外判,不管事情由誰弄出來,任何責任都必須由董事來負責。即是說,DTZ發生的大小事情,由DTZ董事集體負責,無分大小遠近。
梁振英在DTZ戴兩頂帽,分別是DTZ執行董事和DTZ亞太業務主席。他在DTZ期間,大部份時間處理亞太區業務。他為DTZ亞太區業務作出的決定,DTZ其他董事一樣要負責;同樣,DTZ這幾年在英國作出的決定,梁振英參與程度多少不是問題所在,他同樣要負責,是全責。
英國分析員指,DTZ清盤的禍根種於2007年至2009年過度擴張,以銀行借貸融資,作出多個收購,負上巨債,當經濟下滑,業務收縮,於是財政出現困境。從圖2見,2007年至2009年DTZ在收購方面融資近1億英鎊。從圖3見,DTZ盈利表現一直良好,2008年開始錄得虧損,原因應該是DTZ業務一面受到金融海嘯冲擊,一面須面對沉重利息支出。導致DTZ清盤的大事,大部份在梁振英加入DTZ董事局後發生。
從客觀企業管治角度看DTZ清盤,梁振英責無旁貸,他不可拿自己管理的亞太業務表現出色作辯護,因為他身為DTZ董事,擁有不可推卸和不可分割的責任。從主觀情感角度看,我非常同情梁振英在DTZ的遭遇,太多假如:假如他當年不收股票,收現金;假如即使他收股票,禁售期過後減持;假如他提早一兩年脫離DTZ,另起爐灶;假如他當年沒把自己的事業心血賣掉……
測量師行是服務行業,是人的生意,實際是出賣人的腦袋時間,特點是增長速度受到人的限制,商業用語是Non-scalable。加上企業全球化,令獨立測量師行經營出現困難,以併購壯大業務,高速加大地理上覆蓋,是熱門的企業策略,梁振英選擇行這條路無可厚非。Youlivebythesword,youdiebythesword,DTZ不是採取併購策略,可能不會遇上梁振英,而梁振英的公司業務規模,以至國際視野,亦未必可以快速成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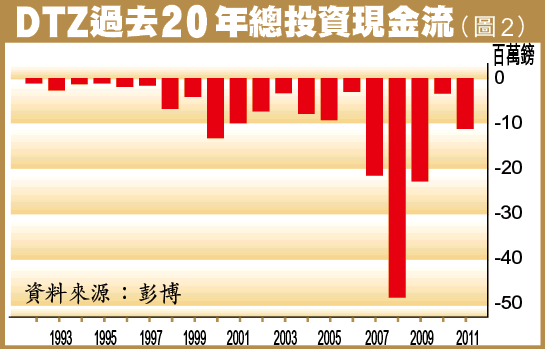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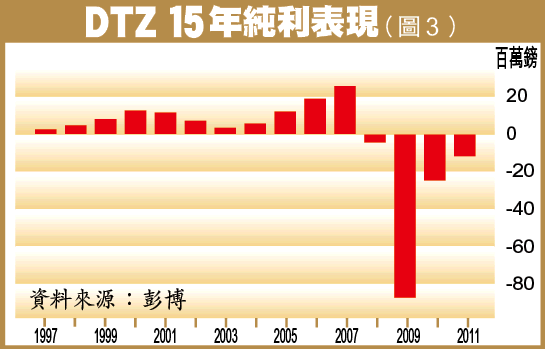
僥倖過關心態 博「一鋪翻身」
有一件事我百思不得其解,是梁振英為何不自我引爆DTZ財困的問題,把握主動權。梁振英部署參選特首不是一朝一夕的事,而DTZ財困也不是最近出現。我在表3平排分別列出梁振英和DTZ過去1年發生的重要事項,可清楚見到梁振英過去積極部署參選,而同時間DTZ早已出現財困迹象,他有很多機會可主動作出交代,引爆這個計時炸彈。
DTZ是上市公司,這件事遲早會在香港傳媒曝光,他的沉默令人費解。有一個可能性梁振英一定有考慮過,他可以提早「跳船」,辭去DTZ董事職務,理由是要多花時間去研究怎樣進一步服務香港,但他沒這樣做。
2011年11月傳媒揭發後,梁振英一直處於被動位置,被問到DTZ的情況,他從沒正面詳盡回應,最後牽起風波。我想到的唯一解釋是,梁振英把自己一手建立的事業交託予DTZ,DTZ對梁振英太重要,DTZ遇上困境後不斷找尋拯救方案,白武士彷彿出現過,只要存有一絲希望,DTZ仍有望翻身,他的想法你我何嘗不是經常存有,那僥倖過關的心態。DTZ的情況越惡劣,梁振英越陷於僥倖過關的深淵中,他跟自己解釋,結果未必一定是「一鋪清袋」,有可能是「一鋪翻身」。
丘亦生
金融中心fanpage: http://www.facebook.com/hkfincent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