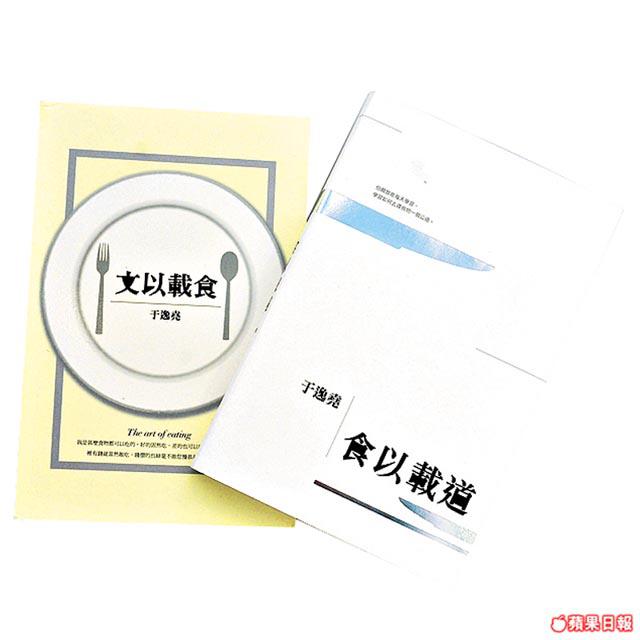
認識于逸堯,大多數人會因為他的音樂。近年,他卻相繼出版了兩冊關於食的文集。不是食評,沒有星星,題材由米芝蓮餐廳到地踎大牌檔,一杯香檳一串牛雜,都在他筆下化為思憶與情懷。
吃,不止飽肚,正如于逸堯所說:「沒有不好吃的食物,只有未開竅的味蕾;沒有不文明的食桌,只有未破解的迷思;沒有不溫良的安樂飯,只有未琢磨的平常心;沒有不世故的地方菜,只有未嘗懂的人情味。」
記者:曾凡
攝影:陳盛臣
鳴謝:君悅酒店
于逸堯
六十後,香港出生,原籍河北保定。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地理系,獲社會科學學士學位。曾任職亞洲電視配樂組及商業電台第一台,為獨立音樂廠牌「人山人海」創辦人之一。現為自由創作人,統籌各種音樂事務,為電影、錄像電影、廣告及舞台演出創作音樂。2007年開始兼職寫作,飲食專欄文章見於《MilkX》及《壹週刊》。2010年出版《文以載食》,第二冊結集《食以載道》近日出版。
外省口味
于逸堯成長於七十年代的香港,記得最多的,都是關於食的印象。「我家是外省人,父親天津,母親上海。」他那副典型外省人的樣子,小時候換來「外省仔」的稱號,都好正常,「但我們家是講廣東話的。外祖父年少時已來香港,所以他的上海話是很奇怪的,夾雜了很多廣東話,很不純正,從小到大也不懂他在說甚麼。」就是因為這個外省家庭背景,令于從小開始已經跟同學們有很不同的飲食習慣。
于家定居香港,但飲食方面,仍然保留天津上海特色,尤其是上海的飲食文化。「祖父是天津人,小時候已經在廣州生活,算是半個廚師,他還懂得打廣東麪條。外祖父那邊多煮上海菜,小時候比較多機會跟媽媽回外公家吃飯,因為她喜歡吃凉拌前菜,一小碟的鋪滿餐枱,跟我同學所描述的家常便飯完全不同。」于慢慢知道,自己吃的,與其他人有點不一樣。「我母親喜歡上館子,也很喜歡吃紅燒肉。有次跟朋友談論到『豬肉』這個話題,他們總是對我吃的食物感到好奇,他們從未吃過紅燒肉,也絕少上館子吃飯。」飾演餐桌上的兩頭蟲,吃盡左右茶禮,無論如何都是味覺上的一次寶貴經驗。
眼界,便是如此打開。
味覺初開
上中學後,結識了一班飲食同學,捨得花時間吃一頓美味的午餐,而不是三分鐘幹掉一碗飯然後衝往球場踢波去。「我們會花時間選擇去哪兒吃午飯,或放學後到觀塘掃街。」甚麼油炸魚蛋、快熟版蘿蔔絲酥餅、中間像芝士的臭豆腐,都是心頭愛,「現在的完全不像樣,沒有了舊時的味道。」
從此尋找美食,變得有趣。「記得有次考試後吃壽司慶祝。當年吃壽司是挺前衞的,那間日本餐廳在崇光百貨的地庫,叫浪花,壽司算得上正宗,不是玉子蟹柳,而是魷魚、八爪魚、三文魚子和劍魚等材料。」熟悉的材料,新奇的食法,一種從未感受過的味道和質感,啟發了于去想:究竟這些食物是如何烹調的。「當年偶然在家煮飯,便試過整壽司當實驗,用家中的米來做壽司飯,試過很多捻飯糰的方法,飯粒還是鬆散;飯粒味淡,便加鹽;飯上的材料,當時只買到蟹柳,至於玉子,想了很久也不知道怎樣做。」那年代,資訊不發達,要學得到一門煮法確實不容易。「我對食物的興趣和知識,便是由煮飯的過程中得到和學會的。」
食材深究
要知道更多食材的知識,另一個地方,便是街市。「我會跟爸媽去市場買餸,如何選擇靚瓜菜;如何挑選豬肉的不同部份;如何跟肉檔檔主指出想要的豬隻部位。」以前的人多在家煮飯,充滿生活小智慧。現在很多家常小菜,都被菲傭的菜式取代。「在中學時,我差不多每天也會自己做飯,懂得弄的菜式不少,如燜雞翼、紅燒肉、糖醋排骨。我會請同學來一起做飯過節。」大學時,于更會在宿舍裏煮飯掙錢,「每人每餐十五元,連洗碗就十八元,每場都有五至六個人參加。我煮的食物其實不是真的很好吃,但我總有那個耐心和興趣去研究食物。」
于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亞洲電視做配樂,「跟我同年畢業的同學,工資全都比我高。那時是92年,月薪只有六千多元,還要搬出來住,一個月真的沒有太多餘錢。」因為缺錢出外吃飯,于多數留在家煮飯,便「發明」了很多便宜省錢的煮飯主意。比如,一次過買夠吃一個星期的食物,然後帶飯盒回公司,回家後便回吃餘下的飯餸。「我想盡辦法煮一些擺放一星期而不會變壞的食材,又要三餐都營養均衡,不會吃壞人的菜式。那個時候是最多一個人煮飯的日子,廚房雖小,卻已足夠讓我試驗不同的菜式,我更會嘗試煮一些怪怪的餸菜。有時候,我會邀請朋友到我家一起烹調不同的食物。」當時于在電視台就是為《方太教煮餸》做配樂,每日都聚精會神看方太的廚藝,「對我來說,方太是我的煮食啟蒙老師,我很尊敬她。」
為食平反
愛食,也許因為貪吃。有些人連吞十碗豬油撈飯面不改容,有人總愛發掘新食材的味道,淺嚐即止。「我饞嘴的程度不算是貪吃,我沒有那種『癮頭』。」于對吃,有一種感覺,或者算是一種微妙的關係。「我對食物有一種感情,我跟食物可以互相交流,我可以寄情於當中。」于在中學的時候,爸媽常帶他上餐館吃上海菜,「那時我沒為意原來很多人不曾接觸過這些食物。到現在,有朋友還會覺得鹹豆漿很怪,覺得深心不忿。我很想知道為何人會抗拒他們從未嚐過的食物。我自第一天開始寫飲食文章,便有一團憤怒的火,想為這些食物平反。我覺得所有存在的東西也有它的價值,我不知道為甚麼人們總會冠上一些詞語給陌生的食物,比如『核突』。」
理論上,我們現在接觸食物的渠道比以前多,但實際上我們還是對陌生的事物存有很大的偏見。「前幾天我跟朋友談到內臟,人們不吃這些東西總有原因,但當中一定有一項叫到『惡心』。就好像吃內臟的人就必須承擔不必要的罪惡感。很多人不喜歡吃豬膶,但同時又喜歡吃鵝肝。鵝肝比豬膶乾淨嗎?鵝肝只不過是形象較為高尚,售價較貴而已。」于一直希望能透過自己的角度,將對食物的偏見和不合理平反。「我在這方面不斷學習,希望借這個機會學習一切關於食的知識多於要試吃每種食物。透過搜集資料的過程嘗試一些我從未聽過的食物,比如你平日不捨得吃,或者沒有那個陪伴你吃那種新奇菜式的同伴,所以我時常覺得那隻『飯腳』是很重要的。食跟談戀愛一樣,是無法勉強的。」
以文載字
由純粹的吃變為又吃又寫,當中的轉變由于的博客開始,「有一陣子心情挺糟糕,工作和人生都失去了平衡點,便開始嘗試寫Blog。最初用英文亂寫一通,純粹發洩。後來有了數碼相機之後,對拍攝食物情有獨鍾,我便把這些食物相片放上Blog,再寫一段文字描述。」之後,于一位做雜誌的朋友請他在雜誌上撰寫關於食的文章,「每次寫都要花心機,挑選一個角度去描寫自己對食的所見所聞。初期的文章比較像食評,着墨寫飯後感受和對一味菜式的看法和意見。後來我發現食物的味道並非重點,因為味道的好壞往往被很多外圍因素影響,例如環境、偏見、對一道菜式的認知。一樣食物的烹調手法的原因是最重要的,我希望能夠明白食物的原貌、來歷、廚師選擇的烹調方法。我的文章旨在啟發讀者反思枱上的食物跟他們自身,甚至社會的關係。」
食是一種文化,一種藝術。食物不是無中生有,背後一定有一個製作過程和人為因素,告訴我們人類的進步和墮落。新書《食以載道》所收錄的文章全都是由食物出發,探討食物跟社會大氣候的關係。「我本身不是一個對文字很敏感的人,平日也比較少用文字來抒發己見。」偏偏便出版了兩冊有關食的書籍。「正如我大學攻讀地理,想也沒有想過日後會成為一個音樂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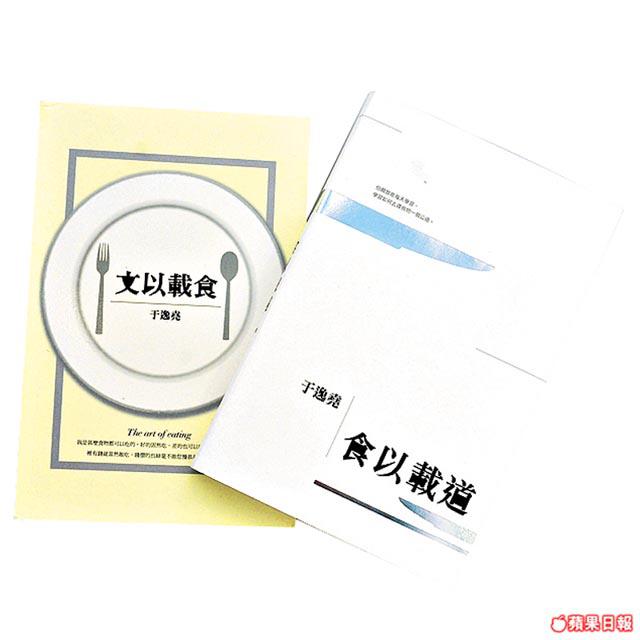
總結
「我喜歡寫食物所帶來的使命感,因為吃的過程本來就是很複雜的。吃一頓飯包括了社交、待人接物與思考模式的磨合。我不是寫關於味道的好壞,我只是介紹食材背後的故事。我比其他食評人更容易捕捉食物的精神,我不怕得罪餐廳老闆,又不需要介紹食物好吃與否。我的角色只是提供資訊給讀者,味道的判斷,還是留給他們自己吧!」
食有所思
餛飩
如果這輩子只能吃三種食物,我的首選是上海菜肉餛飩。我對餛飩有種情意結,像是屬於我們家的共同回憶,令我想起小時候的歲月和家人的感情。我們在加拿大住的時候,有一天,我和家人忽然想到了上海餛飩,於是便花了整天時間包餛飩,還拍了這張照片留念。

AppleQuicktake200
這是我第一部數碼相機,九十年代末在紐約買的,已經絕版很久了。因為這部相機的出現,令我開始拍攝食物相片,不管是吃過或見過的食物,都很方便記錄下來。在菲林相機的年代,我是不會花錢買菲林拍攝這麼無聊的題材。這部相機驅使我開始攝影、觀察食物。

《HowToEat》
NigellaLawson這本書,啟發了我對食物寫作的興趣。這書雖然算是一本食譜,有字典般厚,但我一直很喜歡讀食譜的,所以一頁一頁的翻閱。我很喜歡讀作者的文字,她有一個很清晰的角度,把食物和英國人的民族性掛鈎,影響了我寫作的角度和分析手法。

《蒲公英》
伊丹十三的電影,一直覺得它在影響我對食的觀念,無論是日本食物,還是審視食飯的過程和態度。其實中國可算是最早把食提升到比單純填飽肚子高的境界的民族,對吃的態度和觀念絕不遜於日本,卻逐漸忽視自身的飲食文化,為此我感到特別憤怒。

筷子
小時候因為頑皮,故意用奇怪的方法拿筷子,後來開始對煮食產生興趣,偶爾幫忙煎雞翼時,才發現沒有一種工具比筷子更方便輕巧靈活,比如在炸食物時,更只需一雙長筷子便能把食物處理得很好。之後便決心慢慢練習正確的握筷子手勢,過程漫長而痛苦。

滄浪庭
小店,永遠令人有種一吃再吃的衝動,雖然環境未必好,甚至偶有失手,但你卻樂意一去再去,混得熟了,與老闆夥計閒聊兩句,吃得出人情味。一直都喜歡去美孚這家小店,只有兩三個座位,只賣幾款麪食,所以經常有人龍出現。老闆很有態度,而且還挺兇的。

同枱吃飯
和人山人海的隊員經常出國表演,同枱吃飯的機會多了,有些當時沒特別,但過了一段時間,便很懷念當時的日子。例如某個陽光下在歐洲的午餐、猶如自助餐般豐富的後台用餐區,甚至只是很普通的一次長桌碟頭飯聚會,都是音樂和工作和夥伴們的感情和日子。

方太
我挺喜歡看方太的《方太教煮餸》,她在鏡頭前面有一種獨特的魅力,跟普通人不一樣。她示範過一味「肉末回鍋蛋」,名字很漂亮,但其實只是一道上海家常菜。因為很容易做,而且放得越久越好吃,那時我很窮,便經常煮這味菜,一吃三天,配飯配麪已經非常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