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問她覺得甚麼樣的女人最迷人。
李玉認真道:聰明,敏感。還有,頭髮少。
我們大笑起來。頭髮少?這個答案真是無厘頭。
「你不覺得頭髮少的女孩子看起來格外敏感嗎?當她們梳起一個小辮子,細細的,看上去很伶俐很倔強。」
能讓女人閃出光來的女導演,就這樣解釋她的審美觀。
撰文:鞠白玉
攝影:金與心
李玉,中國當代導演,1973年生於山東濟南,16歲開始入電視台任客座主持人,後闖北京成為紀錄片導演。96年紀錄片《姐姐》獲中國紀錄片協會大獎,97年的《守望》獲東方時空金獎,98年《光榮與夢想》獲中國紀錄片大賽金獎。01年處女電影《今年夏天》獲威尼斯電影節艾爾維娜塔瑞獎,及柏林電影節「最佳亞洲影片」獎。06年《紅顏》獲華語電影傳媒最佳新導演獎,07年《蘋果》入圍柏林電影節金熊獎提名,10年《觀音山》獲東京國際電影節最佳藝術貢獻獎,最佳女主角獎。

李玉構造的光影裏,那些平凡的女孩因為在命運裏的倔強,面目生動起來。她好像格外地愛着這樣的女人,不管她們身處何處,看似卑微不堪的境遇,她都要她們閃爍生光。
「我喜歡郝蕾(主演婁燁的《頤和園》)就是因為她頭髮少。范冰冰非常漂亮,遺憾的是頭髮太多了。」雖然李玉說遺憾,但范冰冰卻憑李玉的作品《蘋果》打爛了花瓶套路,確立了文藝氣質,又憑《觀音山》摘了東京影后桂冠。我問怎麼范冰冰只在李玉的戲裏有質地?她答:「這得問范冰冰本人,怎麼她演別的戲就那樣演?」
她看范冰冰的眼神,覺得仍能找回少女氣。「她十五歲出道,不得不像成年人一樣去跟人打交道,這個女人沒有少女期,我知道她一定懷念那些。她有很真實的東西,曾經被十幾年演藝生活掩蓋住了。演過《觀音山》以後,我看她比從前更率真,有些東西,回來了。」
這是她擅長的,看那不為人知的一面。是天性,也是經驗。
她個子嬌小,淡妝宜人,說起話來是山東大妞的耿直。《觀音山》是地道文藝片,卻也在國內院線賺了票房,在海外拿獎,她卻隱起來做下一部戲的劇本。我說怎麼你那樣低調?她皺起眉頭:哎呀,侃侃而談的導演太多了,講了半天拍出來的戲很差,我老跟自己講,別丟人,話少一點。
上月在國內公映的《觀音山》熱度未減,她已經覺得是浮雲。說是在籌備懸疑片:「我生氣,怎麼中國就沒有一部像樣的懸疑片?我想試試看。」

是殘忍?是幸事!
當年,從山東濟南出來,她年輕,精力旺盛,覺得家鄉城市的生活實在太苦悶。實際上那時她已經在山東是小有名氣的主持人,光環籠罩着,旁人寵愛她,她卻要當「北漂」,做個自由人。並沒有紀錄片的經驗,別人讓她跟着有經驗的人學習她卻不肯。她靠直覺和悟性,拍出來的片子在當時中央電視台的紀錄片風氣之下顯得獨特,有人形容是「像一隻蒼蠅一樣緊緊叮住現實」。這是她紮實的生活帶給她的。就像有人批評《蘋果》脫離現實,范冰冰和佟大為的打扮長相不似洗腳妹和清潔工,她反問道:你可知道現實是甚麼?
現實是她在紀錄片生涯時一直在底層摸爬滾打,她知道那些清潔工裏有漂亮的精緻少年,有知識淵博的小學老師,洗腳妹裏有玲瓏單純的少女,他們的夢想不比任何一個人的乏味單調,他們的生活平凡也驚心動魄。普通人的愛與哀傷,她自己是觀察者,也體會咂摸過。
所以她不必刻意細節,細節就在她心裏。比如《紅顏》裏的骨灰是成片狀的,她說:火化以後很久,那些片狀才能變成粉末。
初來北京時,住的地方緊臨解剖室和殯儀館,每天下夜班時路過冰冷陰氣的地方,她不怕,好像生死本就在一界。小時她時常冷不防地問母親:你會死嗎?母親沒好氣地說:當然我會死!所以《觀音山》中她讓張艾嘉扮演的失子母親,在結局裏從高山跳下。「很多觀眾說死太殘忍,我卻覺得她去找她兒子莫非不是幸事?她高高興興了無牽掛地找尋另外一條路,為甚麼是悲哀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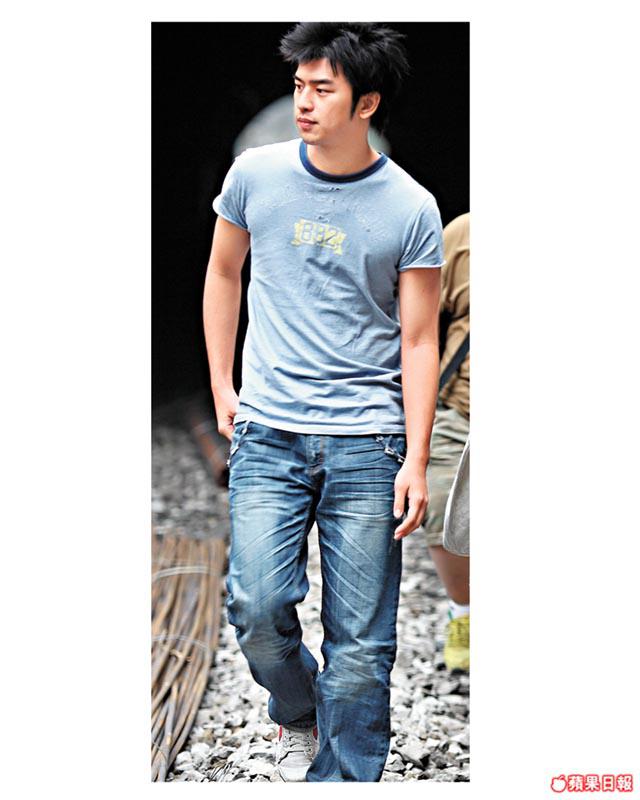
從影崎嶇路……
賣了房子拍第一部電影《今年夏天》,女同性戀題材,被禁放映,她就此知道還有電影審查這回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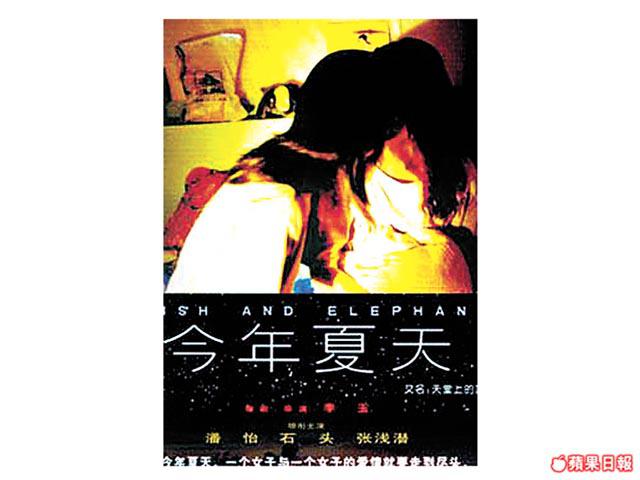
再拍《紅顏》,中途資金斷裂,勉強撐下來,口碑是好,但永無公映那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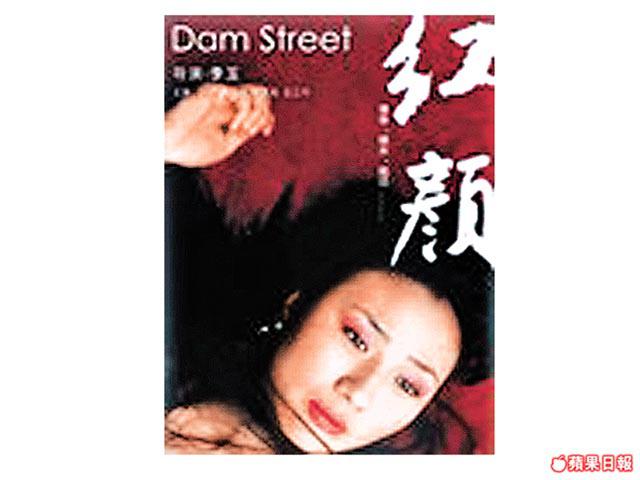
直到《蘋果》,票房報捷,卻定罪為「三級色情片」被禁,責令兩年內不能拍電影。


看着想抽煙
死未見得不幸,但生也不可怕。她着迷生命的韌性,如她自己,很是吃過些苦頭。
《觀音山》若不是在東京意外得獎,也未必能在國內有票房。說意外,是因為今屆和它相比的有大熱日本小說改編的《白夜行》。「反正電影節也不是跑步比賽,誰拿這藝術貢獻獎也不見得是最佳。」她和影人們惺惺相惜着。
據說製片人在首映禮時向記者請求:千萬別說我們這部是文藝片。但確實文藝,是人們認為的傷情的結局。她從前電影裏人與人關係的疏離,這部片又是萍水相逢的溫情,她試圖讓人心回到一個最本質,正面和負面的極端。「這兩種滋味我都嘗過,人和人的遠與近我都知道是甚麼,兩個我都相信,我只是把我一直獨享的體會拿出來分享了。」
有人寫信給她:應該在一個沒有禁忌的電影院裏看,因為這電影讓人想抽煙,想喝醉。「拍電影就是拍情懷,你看我每部片風格不同,情懷一致,都是我李玉想說的。」
她過往一定有過殘酷的生活,也飽嘗過溫情,如她的電影,冷暖交織。她這樣城市裏長大的女人,不曾拍過矯情的小資題材,沒有假裝描繪過做作的都市愛情,她是現實主義導演,是她個人獨守的現實主義。賈樟柯和婁燁也有獨屬的另一種現實主義,但李玉的是更沒有隔膜感的現實。「有一天人們想知道2006或2010的中國人的生活是甚麼,我希望能在我的作品裏找到。」
她沒專門學過電影,理論那套全是個人經驗,懶得借鑑,她想自己去摸索體會,生活也一樣。和安穩的情感生活比,她更依戀於漂浪中的人際關係,她有許多至愛親朋,見到人的第一個動作總是張開手臂想要擁抱。「我把自己打開了。」
她穿衣打扮是精緻的,正是十足女人味的年紀,卻不期待婚戀關係。「怕害人,我總喜歡未知,別的女人想要一個明確的未來,我不要。這輩子不想結婚,生活一旦看似已知,我就逃跑,這樣會負了別人。活該一個人。」
鞠白玉,
滿族女,
八十後,
達達主義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