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7歲成為職業作家,她形容是孤獨所迫。在新加坡時清貧且規矩的求學生涯,並無興趣的專業,寫作被當成寄託。28歲的張悅然身上仍找到那隔絕感,更令人注意到的是一種穩定性,不是人們期待的女作家式的瘋狂。沒有瘋狂的生活,只有一份簡單的戀情,還有隔幾年出現的新小說。
撰文:鞠白玉
攝影:陳偉民
決心做這一書系,也是因為太孤獨。製作這書的過程,也看到了更多孤獨的人。孤獨原來是如此遼闊,如此恒久。這本書是獻給孤獨的,我們強大而溫柔的敵人,也是獻給你的。彼時我在和我的孤獨作戰,而你正和你的孤獨對峙,我們忽然被打通了。孤獨,原來也可以是一座橋。
這一年是張悅然主辦的雜誌《鯉》誕生近三年。她從不提及辦雜誌的艱難,輕描淡寫地說這雜誌的意圖,她想留一塊文學的淨地,想讓孤獨的人有一塊空場,互相交滙,彼此安慰。
她是少女時代便成名,當時與韓寒郭敬明是紅遍南北的八十後作家,他們三人文風全然不同,卻不約而同辦起了雜誌。在新加坡讀大學時,記者訪問她,她說願望是擁有自己的雜誌。當時她年少,談起來像縹緲的夢想,卻順理成章地實現了。沒有編輯部辦公室,採用約稿的形式。她耗費了很多心力,卻心裏感激,它真的幫她解決了個問題,就是往日那隔絕感。因為辦雜誌,她必須要和人們打交道,去瞭解她陌生的領域。

總是灰濛濛
在去新加坡前,她生長在濟南的一所大學校區裏,她的教授父親對她的要求嚴格,她笑着說:「回到北京其實學壞了,抽煙,喝一點酒。上學的時候我完全不能,所以父親說寧可我在新加坡呆着。」
和大學時一樣,她仍然留着童花頭式的髮簾,目光清澈,我說她像老派人,顯得乾淨。這種人像是生來就成熟了,有穩定的價值觀和特性。她有特有的行文語言,在小說中建構一種理想生活,與世俗拉開了距離。好像八十後一代格外厭惡柴米油鹽的日常,但又時常因為被世俗生活丟棄下來感到恐慌。所以她和我提起了另一個女作家虹影,她佩服她,「她在生活裏那麼生動,甚麼事情都帶着一種四川女人特有的韌性。她可以嫁人生子,可以歷盡磨難,她可以養花做飯,之後,甚至她仍然可以寫作。」但她在銀行排隊交費都不耐煩,幾乎所有的日常都令她覺得不安,對生活本質裏的東西變得吝嗇,這是很多職業作家的通病。起初他們依靠寫作試圖和世界接近,最後發現越來越遠。
我問她,寫作像個秘密通道,自有一種暢快,但是可否也有一種傷害感?她痛快地承認了。令她和世俗生活的隔絕就是一種傷害,甚至她羨慕那些熱情奔放的女孩子,而她「總是灰濛濛的」。

拒做流行焦點
她的潔淨是一種慣性,從頭至尾,她都無法把文學當成一種工具,獲得名利財富的工具,她誠惶誠恐地熱愛着它,寄全部的理想給它。二十歲前紅遍中國,全國各地做簽售,「那時我真的是有點飄飄然,那麼多人注視你,喜歡你,我甚至不想回新加坡繼續上學。
「但是這一切過後呢?你仍然要繼續寫,而且愛你的讀者們,他們並不會替你寫作,仍然要自己面對。而且那種喜愛也並不能保證你能寫得更好。」我讓她回憶最初的夢想生活是甚麼。她說的仍舊帶着詩意:離藝術和文字非常接近的生活。
那麼現在丟失掉了嗎?「我慶幸這保留完好,對物質我實在沒有過多渴望,有時我奇怪為甚麼在這個時代我沒有這樣的慾望,我想還是因為我對文字的尊重。如果我當初寫作只是為了表達自己,現在我竟然也有一種責任感,能不能為我們自己的中文寫作留下點甚麼。這可能也是辦雜誌的另一個理由。」
對文字的尊重,成了一把利器,最起碼她對現實生活不用太過掙扎。過早出名並沒有使她黯淡下去,相反,她並不努力想成為某種流行的焦點,她不希望自己是時髦的寫作人,不希望自己的名字留在某一個年頭裏,她想文字的力量能持久一點,或者永恒。這是寫作人的高貴願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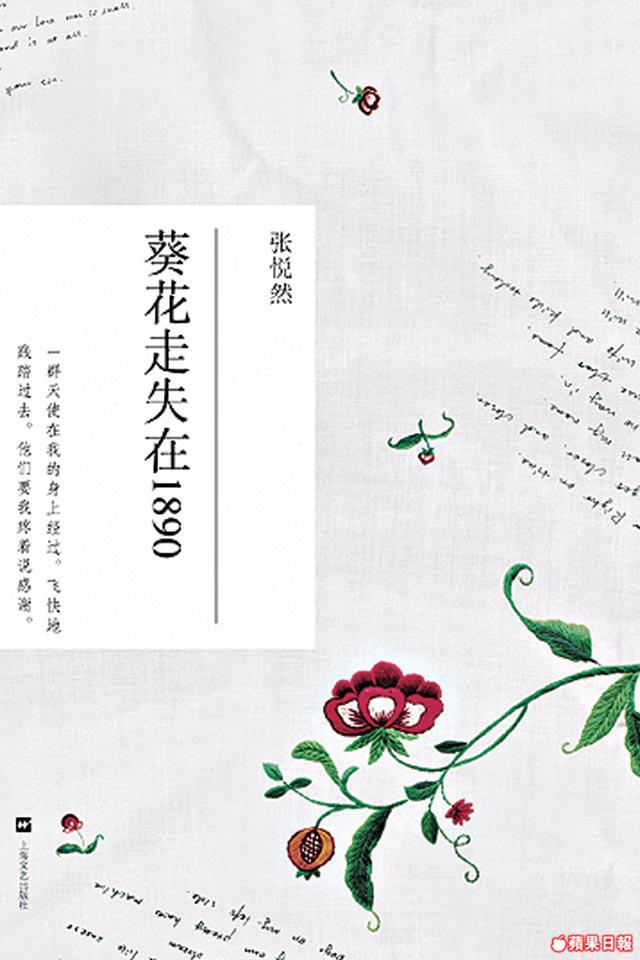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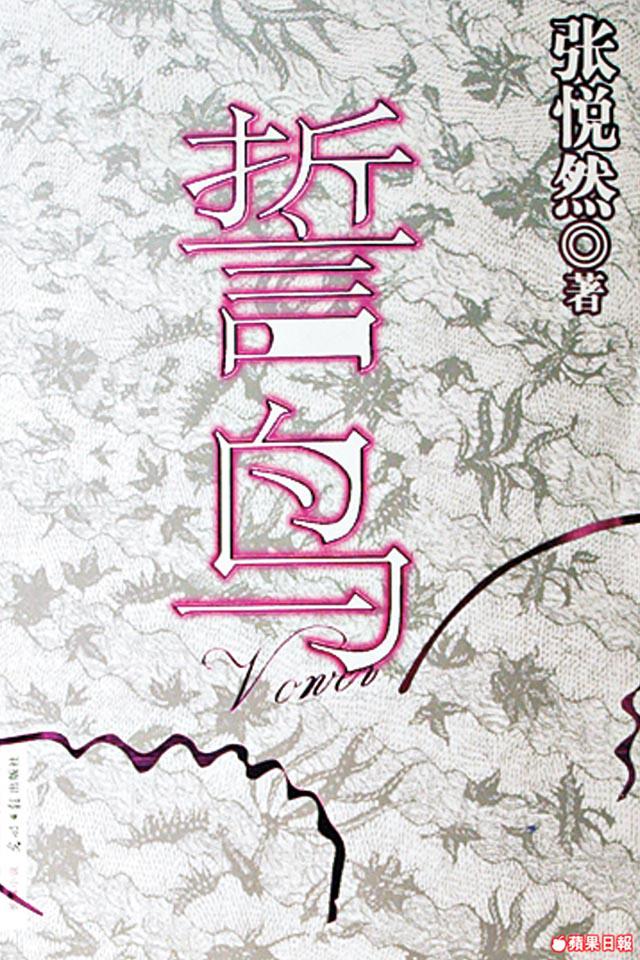
逃避微博
有時候她也懷念新加坡的生活,那時她忙碌緊迫,寫作是奢侈的,餘下一點空閒便能運筆自如,可當她成為一個職業作家的時候,理所應當用大量時間寫作的時候,卻一片茫茫然。她刻意住在郊區,理由是出行不便。她想保持着與熱鬧城市的距離,她和她的作者們在雜誌上描述的一種情景,的確與世俗生活對抗着,這也是大部份讀者想看到的。讀者們並不是寫作人,她們是白領,學生或是其他職員,每個人都渴望能從自己的生活跳脫出去,這是她的雜誌至今得以存活下來的重要原因。
純文學雜誌漸漸被淹沒,她的《鯉》倒是因為年輕化而受注目,她卻為那些小時看的期刊而悲哀,好像看到了自己的雜誌在十年後的處境。總之,一代代的更迭,所能留下的值得珍視的文字記憶是浪裏淘金般。她活在自己建構的生活裏成全着自己的理想,不算微小,踏踏實實地堅持下來。她刻意逃避時髦的微博,想要一切精粹唯美,艱難地,堅持着。
夜深了,她的男友來接她回家,她穿着復古款的外套,腳踩着復古款的鞋子,像是也存心保持着一種和喧囂的隔絕。

另類女性雜誌
08年,張悅然開始創辦並主編《鯉》系列,這是個出版物的全新概念,可稱之為主題書。書系的形式與外形上像一本書,但編輯和設計、以至定期出版的模式,都有雜誌的影子,事實上,是部文集。《鯉》每期有不同的主題,但都傾向以女性趣味為主,取向清晰。首部《鯉·孤獨》至今,已出版了十部。
上月出版的《鯉.來不及》,主題是對抗時間和生命的流逝,韓松更在此發表他的最新短篇小說《閉幕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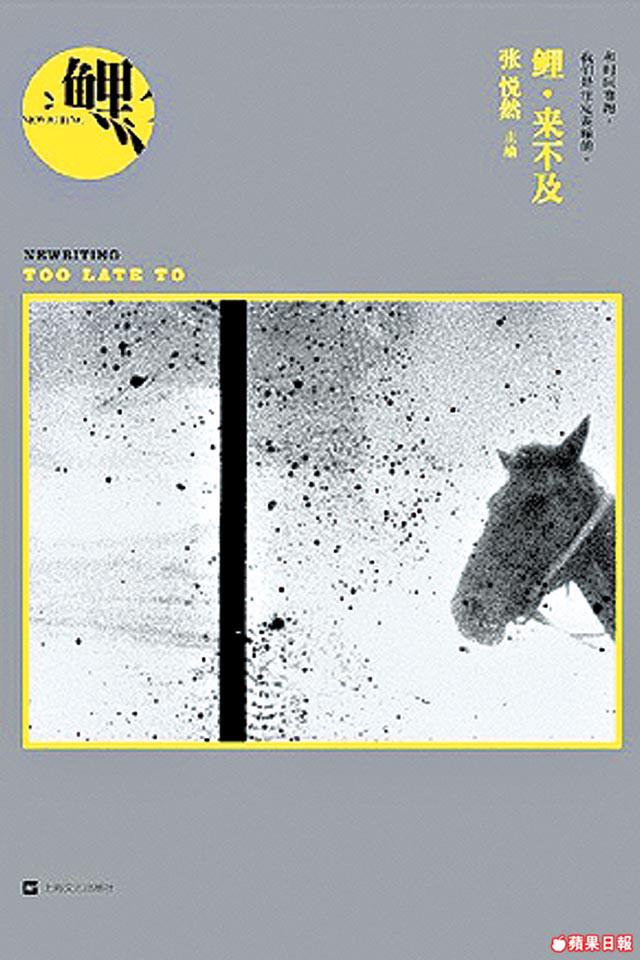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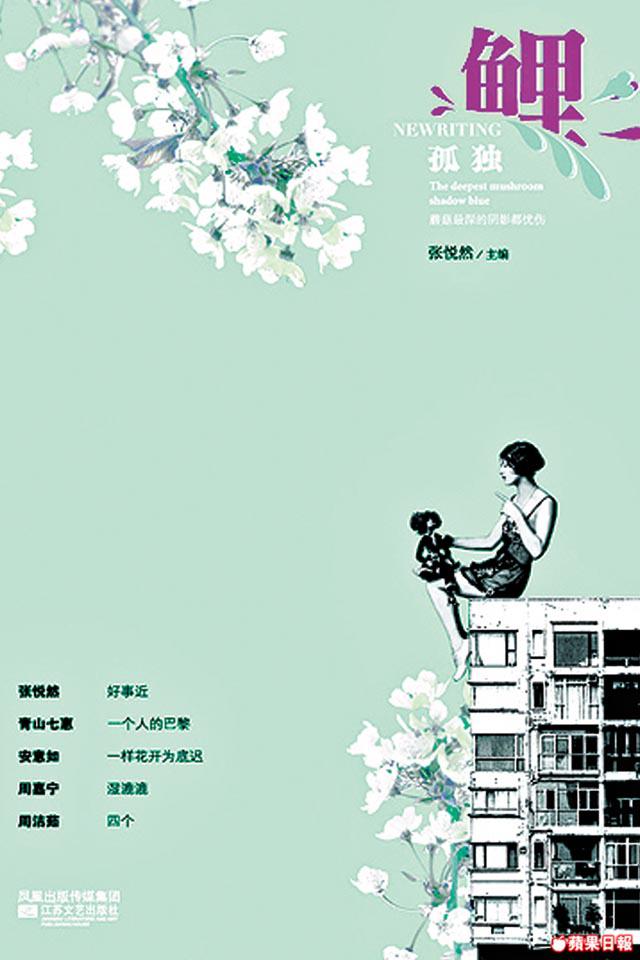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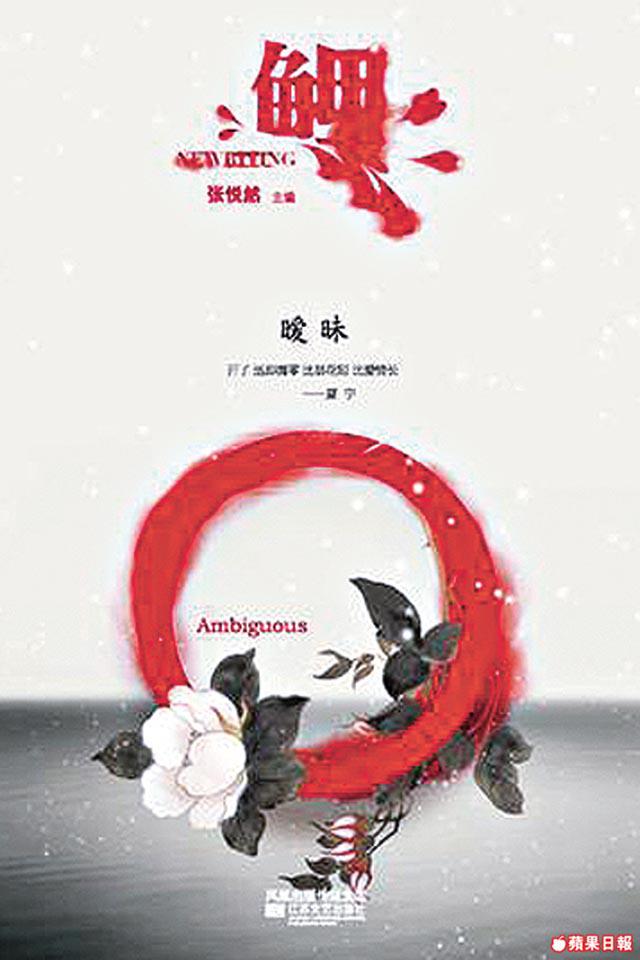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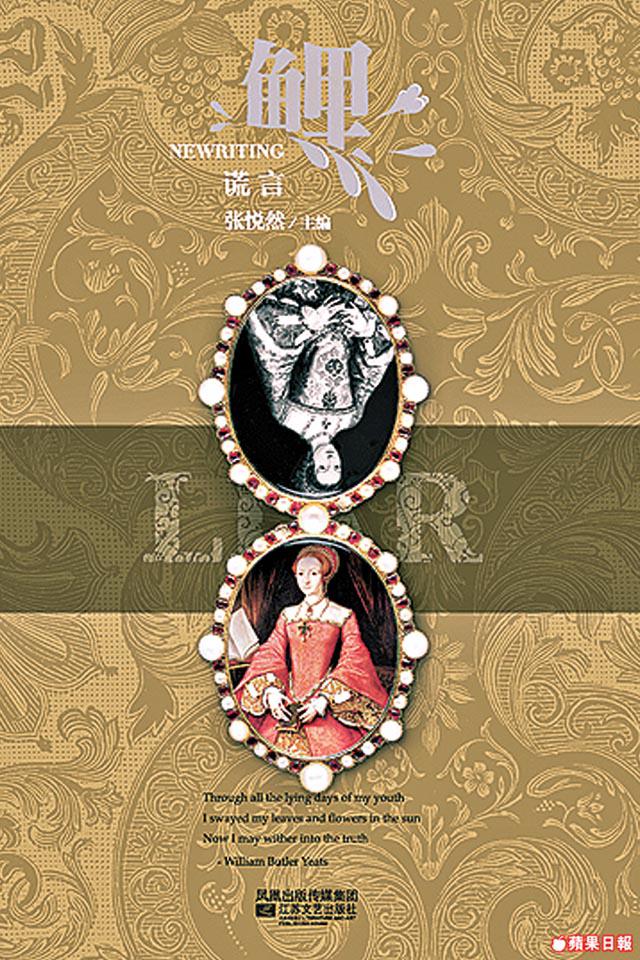

八十後思潮……是甚麼?
同時代的作家她仍欣賞韓寒,認為他做到了一種對抗和跳脫,但是令人失望的是,那些熱衷韓寒文字的人們並沒有追隨他。他們仍然自顧自地活着,仍然綿軟地躺在體制裏享受着安全。十年走過,被捧為八十後作家代表的她說:「所謂八十後思潮,原來是只有潮,沒有思。這代人沒有留下任何思考的種子。」包括她自己,盡力為之,卻不得其果。十年信息膨脹,我們所知的甚多,所思的卻甚少,只被漂亮的句子和高度儀式感的文字打壓和淹沒……

張悅然,1982年11月生於山東濟南。山東大學英語與法律雙學位,新加坡國立大學電腦系畢業,14歲開始發表作品,19歲獲中國「新概念作文」一等獎(韓寒也因此獎項成名),24歲時,作品《誓鳥》獲年度中國小說排行榜最佳長篇小說。08年創辦文學雜誌《鯉》。作品有短篇小說集《葵花走失在1890》、《十愛》,長篇小說《櫻桃之遠》、《水仙已乘鯉魚去》、《誓鳥》,圖文小說集《紅鞋》,主編雜誌《鯉》系列等,是中國最具影響力的青年作家之一。

鞠白玉,
滿族女,
八十後,
達達主義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