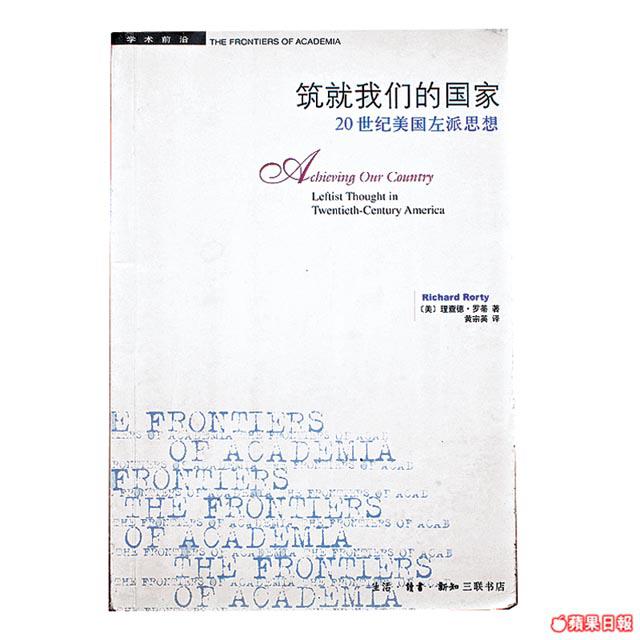「我曾經跟中學生說,你也可以寫社評的,現在很多社評都是這樣寫的,三個步驟:一,引述新聞;二,集合各方意見,之後說『我們表示憂慮』;三最緊要,『如何平衡各方呢,就很考驗政治人物的智慧喇。』」《頭條新聞》主持曾志豪說。簡單幾句,道出了評論的優劣,誰說年輕人不懂評論?
記者:何兆彬
攝影:梁細權、王文忠
拿政府錢照鬧政府
「其實《頭條新聞》影響力唔係咁大啫。相對來說,台灣的《全民最大黨》就叫做有影響力,扮蘇貞昌的演員,可以與蘇貞昌一同登台合照。」
他任《頭條新聞》主持已有5年,觀眾愛看它極盡刻薄、戲謔之能事,但看過近日《頭條》要換主持的新聞後,笑得越開心,就越擔心幕前幕後。不少人說好看因為「節目越來越掯」,曾志豪答:「死,我剛好相反。未加入之前,我覺得這節目好得罪人,但做了以後,我覺得也不特別啊,做完節目上網一看,還有很多更激的言論。我常不覺得尖銳,但有人跟我說:『嘩,呢集掯呀!』不知道是否身緣此山中。」曾志豪有點激動的說:「到底,是因為有人認定我們『身在港台,不應該這樣講。』有一陣子,常有討論說港台應該轉型為公共廣播機構,我不同意!誰說我拿了政府錢就不應罵政府?如果這樣,審計署不是應該解散嗎?他們也不是在監察官員?像BBC收牌費,自負盈虧,結果他們就要做出像《BigBrother》這類節目,在屋內Set好閉路電視,偷拍大家私隱。我會問:這不應該是公共廣播機構做的吧?但它不做這,又哪有錢營運?」
在港台工作多年,他坦言感到氣氛有變:「前線員工心態沒有分別,但我知道有人係想有變化的。會覺得既然最嘈的(兩支咪)都不在了,你還罵甚麼呢?」講到今次事件,他說:「近來,有人假冒《明報》發假新聞,說周小川潛逃了,翌日《明報》嚴正澄清:絕無其事!你會發覺,如果有機構好珍惜自己名聲,它絕不容許半點謠言,就會出來,但這一次我們這事情鬧大了,該一早出來說:『絕不容許有人干犯編輯自主』,是吧?但並沒有!」嘩,曾志豪你好大膽,竟然繞圈子說港台高層不珍惜機構名聲?「哎呀,我敏感度又低咗,我只是覺得自己以事論事。」他補充:「其實有時我家人也勸我──我媽與我政治上是相反的,她看節目後,常叫我:仔呀,你都唔使咁刻薄吖。」




為大陸荒謬新聞着迷
「勃起的特點是,受到越多刺激,便勃起得越厲害;沒有刺激,便會軟下來。而弔詭的是,刺激去到最高點時,便是軟下來的時候。」曾志豪在新書《大國勃起》中寫到。
曾志豪對中國很着迷,始於他還在初中時,「我平日剪報,中二寫周記,我綜合了報章的報道,寫到:『鄧小平退而不休是不對的,他好像太上皇一樣。』回想起來真好笑。」問曾志豪為何對中國新聞如此關心,他說:「原因有兩個,一是大陸新聞實在太千奇百怪,荒謬性太大。我對大陸的社會生活也很有興趣,其實就是香港的內地問題專家,我也不覺得他們對大陸人的生活──吃甚麼聽甚麼歌有何深入了解,但大陸人的思維,也一定與他們聽甚麼歌有關的;二,我父母都是從大陸下來的,他們在香港也看很多大陸節目,小時候過年,人人都看TVB之類,但我記得會跟父母返大陸旅行,看《春節晚會》。」在這樣的背景下,曾志豪自小已是另類兒童,他會着迷的看國內的相聲、曲藝影碟,「近期大陸流行講『反三俗』,如果你不了解他們的流行文化,又怎理解這裏面的內容?譬如說這新聞的主角郭德綱,他就是被反三俗封殺了,這新聞一出來,我就喊:他死定了,因為我從小就看他,他既得罪相聲界,又常諷刺官場。」
他關愛大陸,又愛相聲,卻原來太太也是用相聲追回來的,「當年是追求階段,我在大學圖書館,拿了一本《相聲大全》,坐在她身邊說:我念些笑話給你聽,我一個人扮幾個角色的講,她笑了!我就覺得她是同路人。」
曾志豪說自己的職業是「好管閒事」:「我寫過一篇小說(沒發表),叫《評論員之死》,我寫到評論員的特色是專管閒事,專管別人的事,專管自己控制不到的事。」


推介:
《河殤》
「這是中學時啟蒙自己的節目,當年老師在課堂播!我看了節目及解說詞,它有一些很新的東西,例如說黃河是空廢的象徵,原來河跟中國人的命運很相似。我對大陸的興趣是由此而起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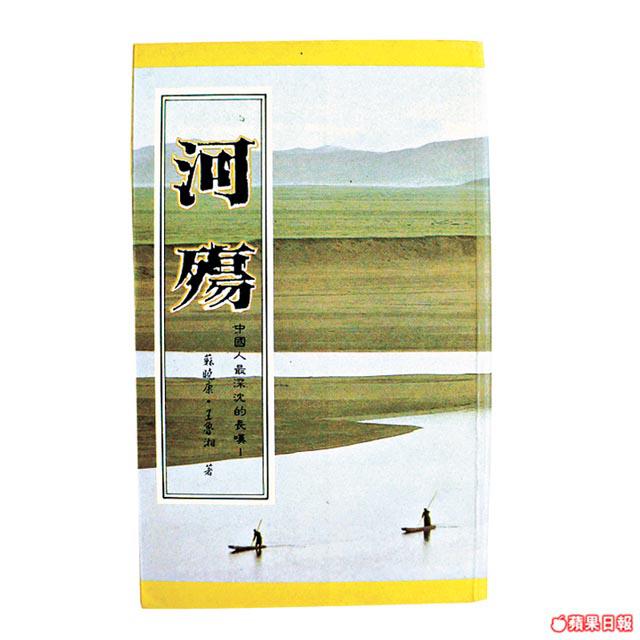
《中國影帝溫家寶》
「看完余杰覺得他好孤獨。這書不單止官方會禁,民間也沒有幾人喜歡讀,因為大家會說:有無搞錯,你咁話溫家寶,佢已經好好o架喇!你仲想佢點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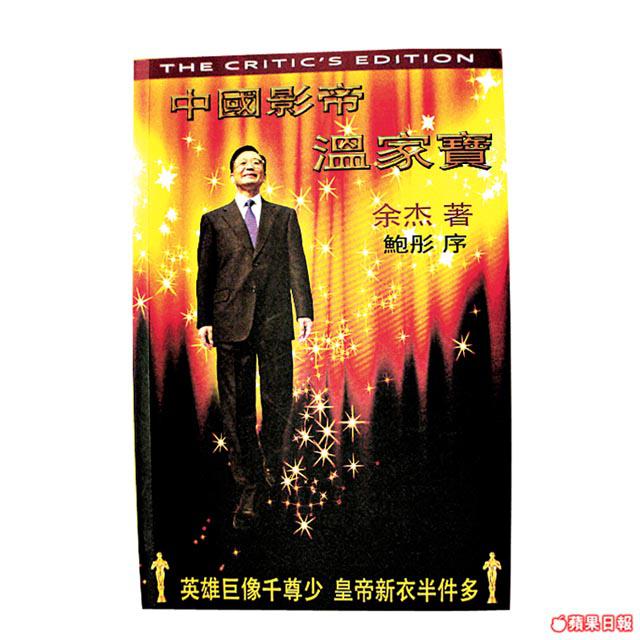
政治與社群的成熟
陳景輝,社運中堅分子。記得年初反高鐵期間訪問他,問職業,他說「評論人。我同時做三份工作」。評論未能賺夠生活,但他說:我視此為志業。
作為評論人,陳景輝也是最忠實的評論讀者,「近年香港的政治變得成熟了,例如陳雲及吳志森的評論,都是面向社群的,是以社會對話者的身份來寫。」他強調,讀者愛看,是社群成熟了:「評論有幾種,早期寫評論的人都有作家心態,文字是寫給少數人看的;而現在有些評論家,是教阿爺怎拆彈,例如他會寫:『政改一定要畀民主黨,否則激進派會抬頭,要三思!』這根本不是寫給市民看;另外,例如宋立功、蔡子強,三點半發生的事,四點半他們就評論了,他們的評論是講給媒體聽。」他強調,評論人要面對公眾,要關懷社會,毋須扮中立,要對這個地方的歷史有認識,對公共事務有判斷力,而不是阿諛權貴。陳景輝以評論為志業,評論為何這麼重要?「寫評論是建立新語言的過程,政治生活是由政治語言建立的。」
他自05年起在兩份免費報紙寫評論,現在,他約每十天在《明報》寫一篇評論,另在OurTV.hk主持《政治解毒》,不過因負責剪接的朋友離職,後者將會停播,「我與余在思正籌備把它變成一個論壇,集合不同界別,論壇後就把錄影剪輯,放在『獨立媒體』上。我中學時去很多論壇,那段日子幾乎是每天都有民間團體辦的,但近年越來越少,網台反而好多。我們想把網絡與論壇結合。」

香港人不自覺被壓迫
陳景輝說他的評論思想是源自六四:「當年老竇話鎮壓,他的道理是『要穩定,否則會亂。』常說『你若為王』,你都會咁做。當年我年紀小,不會反駁,就不斷看評論人的論據。」他的中學年代,開始培養出獨立批判思考。他說,讀評論學習到在緊要關頭,唔會兩邊都得,「我那民主意識也是來自讀評論的,通過政評,你會看到政策原來唔係咁,開始對政府有要求。CommentSense(批判意識)是來自對社會的體驗,例如中學規定男生要短髮着褲,女生要長髮着裙,同學就順從,但我看了台灣的青年權利理論,明白到身體自主與校服的關係。」明白了,還不是要服從?「對,但處於清醒狀態。我們自小就被灌輸不平等的觀念,香港的社會很像中學,我們被灌輸了未能有普選,大家就服從,被壓迫了還不自覺。」他說評論就是公共生活的一環:「香港社會流行犬儒,常有人說:『大家都係唔同觀點啫』,那就沒有行動的可能了。評論反而令我們更有決斷力,或者說,維護了我們的判斷。」他補充:「我們先要有公共生活,蘇格拉底說:未經過檢視的生活是不值得過的生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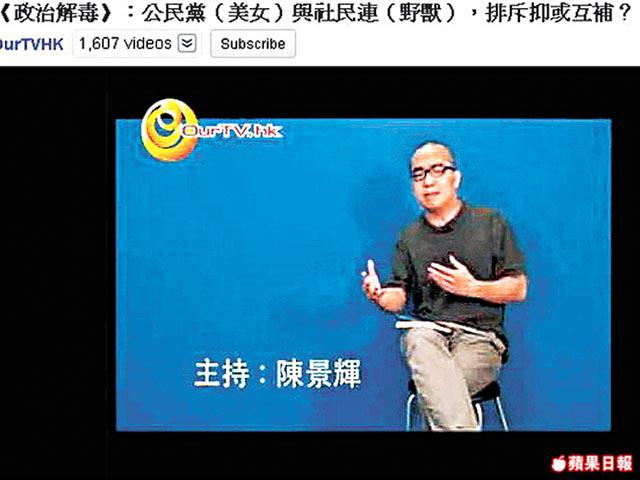
推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