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已經10年沒有做過專訪,竟遇上了訪問好朋友田原的機會。我們都高興,都珍而重之,與其說這是個專訪,不如說是一場互動的生活紀錄。翻開難忘的一頁,去年冬天,在北京,在田原的書房內,偶然看見她19歲時摘下的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新演員獎座,心裏莫名感動。從19到25,我看着她一步步的走來,由被推着走到主動向前,用青春歲月,畫出別有個性的才女軌迹。
撰文:李慧慈
攝影:郭帥、王男
李慧慈,香港出生,相信整個世界,都是腦海反映的幻象。

田原,原名趙田原,85年生於武漢,02年以跳房子樂隊主唱身份,推出唱片《Awishfulway》,被稱為中國最具國際化魅力女歌手,同年發表小說《斑馬森林》。屬環保素食主義者的她,也是音樂人、作家、主持人及演員的綜合體,04年憑《蝴蝶》奪香港金像獎最佳新演員獎,曾參與《青春期》及《高興》等多部電影的演出。10年推出個人專輯《田原》及自稱為微幻系列的長篇《一豆七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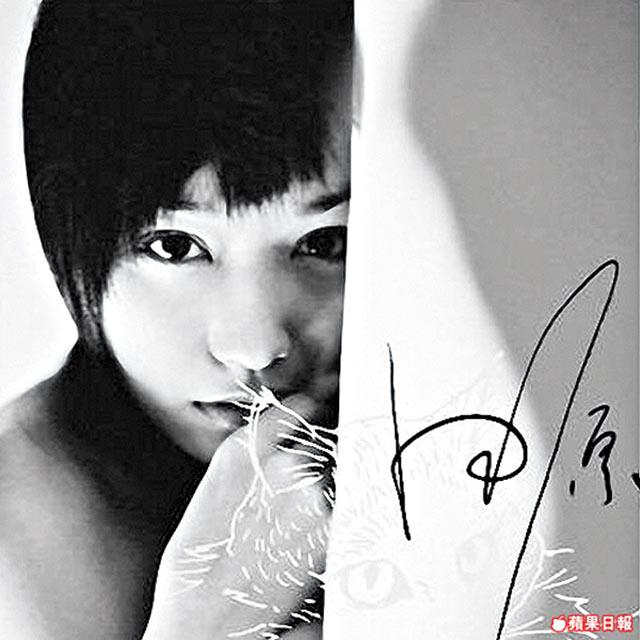
田原經常走神,有次和她走在澳門的路上,她突然蹲下來,動也不動,凝視着地上的蝸牛。坐下來喝東西的時候,她會突然盯着飲料出神,久久也不會說話。她雖然沉默,但如果你剛巧和她的頻率接近,會被這種精神游離的狀態吸引過去,甚至可以互動交流。接通了,就可以和她成為朋友。
她也是一個很會入神的人。入神的意思是,她懂得透過天賦的,安頓好內心的平靜,在繁亂的生活中,她有一定的沉澱能力,茹素的她說:「我心情好的時候,可以把家收拾得很美,而且喜歡泡茶、做飯、做手工、畫圖、攝影。」泡茶、做飯、做手工、畫圖、攝影,也是創作。
全屬意外
該是個不少人都想遇上的「意外」。一個學生的暑期班結他課老師,在完課後一年多,突然記起她自彈自唱的歌聲,致電邀請試音。於是,十來歲的女孩便成了樂隊主音,出了唱片,更發表了小說,然後,一舉成名!田原通過試音加入樂隊「跳房子」,用一個月時間參與唱片《AWishfulWay》的唱作,此張全英文唱片推出後,驚喜國際樂壇,當時某些外國樂評人甚至驚訝這位來自中國的小女孩,如何能營造出如此獨特的英文唱腔及曲風。因為推出了唱片,又被發掘成為演員,完全沒有演戲經驗,就憑參演的第一部電影《蝴蝶》,摘下第24屆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新演員獎。對於這些成果,田原解說是「意外」的被給予很多機會。一切來得太快,來不及反應,一張唱片及一個獎座已被她捧在手裏。
一切真的只是意外?身上發光的星星,就算躲在最遙遠的角落,總會被有心人發現。而這顆星甚至不知道自己有光。演藝生活開始時的狀態,田原解說成是「意外」,當事人這樣闡釋,觀眾也順理成章接收。然而一年、兩年、三年過去,這邊廂,意外的被給予很多機會的說法,在大家心中漸漸定形。田原被看成是被動的,幸運的。
那邊廂,小女孩逐漸成長,走向比原來更接近真正自我的軌迹,換上一個比以前更主動的表現方式。究竟,甚麼令田原由被動走向主動?「是成長令我知道一切得來不易,小的時候可以靠一些靈感和天賦過活,長大了就得努力。不過,話說回來,只要開始主動起來,就得全部主動,當自己真的開始組織安排事情之後,別人也就不管你了。哈,不過這是善意的不管,沒有惡意的。」別人要用多久才能適應你的轉變?田原說:「瞬間!」我哈哈大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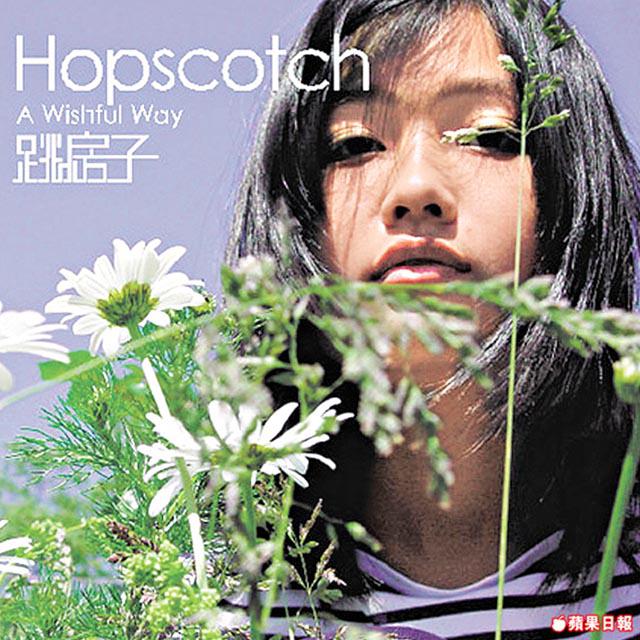
香港人需要微幻
也真是的,作為田原的朋友,我覺得她不被形式所限,像空氣,透明卻又令人感覺到她的存在。她不是善變,而是不斷開拓,正如她說:「我喜歡意外,不喜歡常規,但是不想浪費意外。」就正如視覺、聽覺、嗅覺、觸覺、味覺,感官是相通的,在精神生活裏,她開拓感官的連接線;在現實生活裏,她成為演員、音樂人、作者、主持、攝影繪畫及手工愛好者、甚至小廚師,來實現這種相通。在她的世界,無論唱歌還是演戲,都是一體的,是一種心的反照,透過不同頻道呈現。精神生活和現實不斷接通的互動,令田原神秘,卻又實在;游離,卻又貼近生活。
精神生活和現實不斷接通,令接近這種頻率的人,不受距離之隔,遙遠又親密地和她溝通着。田原稱這種頻率為:微幻。田原讓微幻潛入生活,頻率發放到香港,剛在香港書展出版第一本微幻系列長篇小說《一豆七蔻》,描寫一個少女由13至19歲這7年的內心激盪。田原說:「我覺得香港地方很擠,人更需要微幻。」
除了寫小說,她去年更成立田原工作室,建立一個平台,把頻率接近的創作人,凝聚在一起,創作好的作品。田原說這是一個開心的互動。她在工作室的身份,就像是一個執行監製,磨合及平衡各方面的細節。例如要做一本圖文書,她要和插畫師溝通,和作者聯繫,充當編輯,甚至繙譯。當每個人都有自己想做的事情,會激發起一種互動能力,帶動大家去更遠的地方。面對繁瑣的人事,當然也曾有失望的時候,不過失望令她知道,自己更需要甚麼。「現在做着的,都是自己喜歡的事情,所以要堅持着。」我問她,喜歡了,為何還要堅持。「世界複雜,堅持就是保護所喜歡的,維持裏面的純淨度。」突然,我心裏湧出一股感動。



一直在遺憾
說到維持喜歡作品的純淨度,令我想起創作人的堅持。田原和我都覺得,創作沒界限,沒有分主流獨立。被外界認為是獨立創作人的她說:「客觀來說,外界給我獨立創作人的定位,在我來說,其實就是許多事情是要自己落手去做。例如找贊助,推廣、和記者聯繫等等工作,我也都試過自己做,盡量參與其中。另一方面,現在發放消息及作品的頻道,日新月異,有別於傳統,這些對於我來說,都意味着一種新鮮的互動。」
夾着多重身份的田原,常被問道:田原到底在做甚麼?這得從她最基本的生活開始切入。田原告訴了我一周工作行程表。我發現她這七天行程,基本上沒有假期,田原說:「是」。一星期工作七天,每天大清早開始,就排得密密麻麻,只覺得這緊密的行程,加在由被動開始的田原身上,產生出來的化學作用比較大。
認識田原以來,一直發覺她每次做完作品,或者完成一個演出,總自覺有不足的地方。她的創作,總帶着一連串的遺憾。「這是我的性格,每次總覺得作品或演出有不足的地方,不足就是遺憾。一個遺憾,就是一種可能性的誕生。當作品出來了,知道欠缺了甚麼,帶着這欠缺,到下一個作品,就是一個可能性的創造。」我也是一個愛遺憾美的人,明白田原所說。
「遺憾的路走長了,可能性多了,會不會調高對作品的滿意度?」我問田原。
「不會的,遺憾是作品的一部份,一直會在。」
「即是說,就算創作到六十歲,遺憾都一直在?」
田原說:「是的。」
這一刻,我感受到一種永恒,遺憾且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