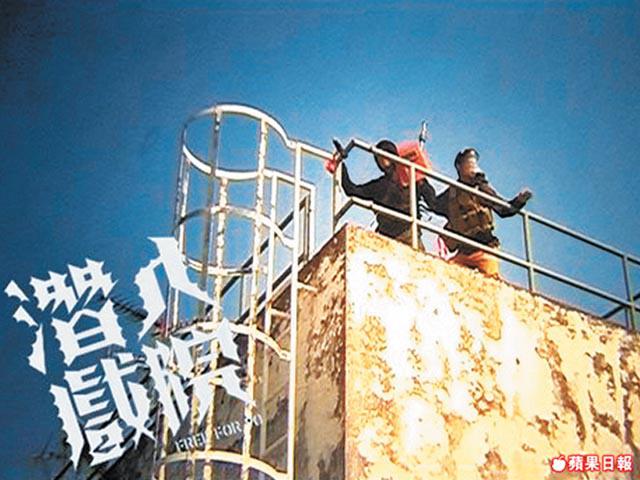
為弱勢社群發聲,你可選擇用文字口誅筆伐,這班電影和準電影人卻選擇透過影像,帶出對抗主流反建制精神,香港亞洲獨立電影節,就是這樣的一個平台,雖小眾,卻有味道。
記者:梁佩芬
攝影:陳盛臣
場地:牛頭角下邨興記荼餐廳
1.崔允信:創辦「影意志」宣傳獨立電影,為香港亞洲獨立電影節出力。
2.許雅舒:曾執導《如果天使不死》,《慢性中毒》成為電影節開幕電影。
3.蔡潔鈴:近作《生日》是個鬼故事,作為送給自己的生日暨入行十周年禮物。
4.陳浩倫:遠赴北海道採訪八國高峯會,拍攝紀錄片《洞爺外傳之祝君安好》。
5.汝樂:曾做電視台助理編導、與李思捷監製《金國民》,近作有《誰收容我的淚》。
蛋散新力量:有別於主流電影資金來源全靠大電影公司,獨立電影多靠政府資助,又或籌款自資拍攝,風格比較明朗,畫面可能流於粗糙,卻能充份表達導演的真情。為鼓勵更多人入行,今屆香港亞洲獨立電影節新增「獨立蛋散新力量」項目,蔡潔鈴的《生日》也有份入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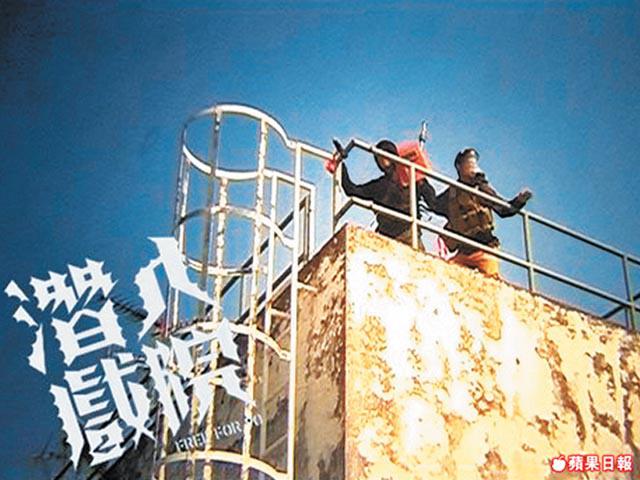

a.李孟熙《姣妹日記》:姣妹安琪愛談情更愛做愛,一次不慎懷孕,決定捧着肚子尋覓如意郎君,重訪各疑似意中人,卻不自覺地搭上詭秘男,以為今次真的戀愛了。

b.許雅舒《慢性中毒》:阿眉丈夫在車禍中失去雙腳,阿政妻子從來只當自己是人家的老婆,媽媽和情婦,兩件事,由一頓喜宴串連一起。

c.楊文穎《塵歸塵,土歸土》:美國華僑Raffi去了墨西哥七年,因母親去世返回老家。母親死於謀殺,Raffi誓尋兇手,被迫與無能警察和不知底蘊的家人周旋,至真相出現,才發覺不問真相反而更好。

d.陳序慶《後來》:堅強未婚媽媽Iris,天真已婚媽媽Janet,萍水相逢成好友,後發現兩人肚裏塊肉竟來自同一人,純真友情頓變猜疑背叛。

e.馮國基《無風詠》:父親失蹤,Jee傷心落淚,Koo的女友突然消失,生活變得無所適從,兩個陷入困局的人沒理由地相遇,又沒結果地分開,人和人居住的城市雖然很小,但心和心之間,距離卻很大。

f.杜紹玲《瞳真》:程川讀完小學,自願把讀書機會留給哥哥,可惜,五一二四川大地震奪去哥哥性命,為紓解愁困,他帶着儍瓜機,把地震後的創傷和希望一一紀錄下來。

崔=崔允信
許=許雅舒
陳=陳浩倫
蔡=蔡潔鈴
汝=汝樂
為自己發聲
崔允信自言已過了憤世嫉俗的年紀,比起許鞍華一代,少了份對社會的使命感及責任感,又慨嘆下一代,不知自己想做甚麼。今天,他帶領一群新進獨立電影導演,解釋人要有獨立精神,才有進步空間。

崔:每人對「獨立」有不同定義,但方向是一致的。
蔡:哈哈,「獨立」就是等於無錢。
崔:與主流和建制相對立,等於在一個國家裏,弱小的一方才會出來對抗,獨立精神,就是要站出來發聲。
蔡:我沒想到那麼遠,只知道想找人投資和申請資助拍攝獨立電影,絕不容易。
崔:無論在言論自由的歐美抑或中國內地,都有反對聲音,有的是地下組織,堅持為弱勢站起來。
陳:我很認同,身為公民,應有權發聲,亦應該發聲,拍電影,只是用另一種方法去表達訴求。
崔:但,香港人真的少了一種獨立精神,原因是看事物的方式及價值觀問題。
許:這是教育問題,我們亦沒爭取更多獨立精神及空間。
汝:獨立精神是一種任性,不用想結果,只求多享受過程。
崔:十多二十年前,若你以獨立反主流自居,是件很有型的事!現在呢,大家不再在意了。有次看記者訪問一批學生,問他們為何看獨立電影,答案竟然是:「這些電影拍得差,很快會落畫,現在不看,日後找不到地方看。」以前,人們還視獨立電影有兩分藝術價值,現在,拍得不好的,統統歸類為獨立電影。
許:十多年前,我們已開始為獨立發聲,到今時今日,仍要說獨立精神,好像沒進步過。
崔:我們的市場太依賴大陸了,太多事情想做想講,但怕得罪人沒後路就停止發聲,令自己越來越邊緣化。
陳:情況有點似崔允信去年的獨立電影《三條窄路》,講及香港和大陸人在不同崗位上,都發揮不到自己所長。
蔡:我一向有做主流電影的製片,到自己走出來拍獨立電影,才知連思維及手法也有所不同。
許:獨立精神,更要包容,所以我不會刻意說自己拍甚麼獨立電影,只想邊拍作品邊磨練技術。嘗試模糊所有既有定義,不界定自己是某一類型人,才可擴闊眼界。
陳:現在傳媒被主流制衡,獨立精神就是要反對主流找出新路向。我的電影想說財團壟斷全球經濟,對社會造成不公,拍戲就是要表明自己立場,旗幟鮮明。
外行人領導內行人
早在政府提出甚麼創意產業前,由崔允信創辦的「影意志」電影團體已着手籌備香港亞洲獨立電影節,實話實幹,把創意變成真正工業。

蔡:我出錢,拍了一條九分鐘短片《生日》,花二萬元,基本上,大部份幕前幕後都由朋友義務幫手。
陳:若給我十萬元,我反而不懂怎使用,如今次去北海道洞爺湖拍G8紀錄片,我一個人拍攝訪問剪輯,去到高峯會,我跟南韓示威者一起睡一起吃,一起行二十公里路抗爭申訴。如果有大電影公司想推出我拍的電影,我應該不會答應。今天我對抗主流,無理由明天要靠攏主流,為曾經反對過的人發聲。
崔:好簡單例子,因為《三條窄路》有黃毓民參與,你們《蘋果日報》才會報道。
陳:去年出發北海道洞爺湖前,一個《蘋果日報》記者找我訪問,我不斷說關於G8紀錄片事宜,記者只說:「如果你被人拉了,我們才會報道你。」
崔:你說我們能否獨立於政府呢?又好像很難,畢竟我們是由香港藝術發展局贊助,但我相信政府是有責任去維護獨立電影的生存空間。
許:我贊成,我的電影都是由藝術發展局贊助。
蔡:不一定要拍在大戲院播放的商業電影,票房勁賺才代表叻。拍我們這類電影,要的是一個播映機會,能讓公眾知道電影內容訊息,這已經足夠。
崔:外國沒有藝術家會覺得向政府索取資助等於領綜援,只有香港人有此想法,出名如法國導演高達,仍是靠政府資助拍電影,獨立不代表與別人毫無關係,如鄭保瑞說:「如非要作出太多妥協,我樂意拍主流電影,人多錢多好辦事,視乎題材吧。」
許:可惜藝發局的資助,完全不足夠拍攝一套九十分鐘電影。我剛去完南韓釜山電影節,看到政府如何正視電影工業,會場最當眼處有個「獨立電影」攤位,讓導演與觀眾會面,又可以在會場賣版權甚至DVD!現在香港只有商業電影,獨立電影竟不被列入為香港電影,真的完全「獨立」了出來!
崔:說到政府推動,別說電影,連政策都有問題。
許:說甚麼創意產業,連「創意」一詞定義,也與現今搞創意的人背道而馳。
崔:沒辦法,永遠是外行人領導內行人,領導香港電影發展局者竟是前港鐵主席!藝發局算好了點,審批過程順利,電影及媒體藝術組主席由杜琪峰擔任,至少是個懂電影的人,但長遠來看,前景仍不明朗,因為兩局完全沒溝通。
許:他們沒長遠計劃,完了一年才預算下一年。
香港出了個賈樟柯
今天在大陸被捧成新思維導演的賈樟柯,也是在香港獨立短片比賽中獲獎後才嶄露頭角,證明香港小團體辦的節目一向不差,有主題有焦點。
崔:你出街問人何謂獨立電影,答案是:「甚麼來的?」
許:事實上,真的有群人為獨立電影努力,每年的獨立電影節都有一批新血,只是沒有人留意。
崔:這跟傳媒有很大關係,無論我們做甚麼,都不及彈出了一個彭浩翔和一個黃精甫,至少有短暫風光。
汝:你每拍一次獨立電影,朋友就會問你:「何時拍一套商業片?」或「何時拍一套勁片?」
崔:香港人生活模式太快,甚麼都是霎眼嬌,現在問人誰是陳果甚麼是《香港製造》,十之八九答不出來。
許:有沒有人提起賈樟柯?
崔:最近一個訪問,有人提出究竟香港何時才可出一個如賈樟柯般人才,但……
許:賈樟柯根本是從香港獨立電影節走出來!
崔:他是第三屆,我是第一屆。香港人價值觀很奇怪,剛過去的香港電影金像獎,我與一班年輕電影工作者談起《天水圍的日與夜》,問他們為何未看過此戲,答案是:「拍得如亞視電視劇般,怎樣看?」
蔡:哈哈,因為有鮑起靜,有很多不知名的演員。
崔:一心關心社會,想拍套電影反映實況,卻難找到有共鳴的人,唉……當然,要好幸運才找到有知名度的人拍戲,我很開心自己的《憂憂愁愁的走了》有余文樂擔正,但不能次次靠出名演員提高號召力。
陳:我覺得有說話想講,就得拍電影!我得閒無事都會拿攝錄機周圍拍,最後能否變成電影是另一回事。
蔡:我一向有寫劇本,電腦裏隨時有十套八套劇本,只是沒有人要,我不會如陳浩倫般機不離身,我的短片《生日》都是靠朋友攝錄的。
汝:我也一樣,今日寫一些,明天又寫一些,最終可成為一個劇本,接着帶機出街拍攝。
陳:我覺得,獨立工作者總有種奇怪性格或態度,如崔允信的《三條窄路》,不少基督教朋友都大受感動。
崔:但我要重申,這不是一齣福音電影。
陳:但始終有人感動,尤其那些對宗教動搖的人,看完後竟能解決疑慮。
崔:九十年代電影業仍興旺時,如果我一天用二十小時,絕對可以拍幾套爛片來,或者往後發展會不一樣,至少多了經驗多了競爭力。
蔡:為何沒這樣做?
崔:就是知識分子那種無謂的包袱,又不習慣制度。
許:別想太多,年輕人有的是時間,放膽做一定有回報。
香港亞洲獨立電影節
日期:11月14至29日
地點:ELEMENTSTheGrandCinema、香港兆基創意書院及香港青年協會
網址: http://www.yec.com
查詢:219681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