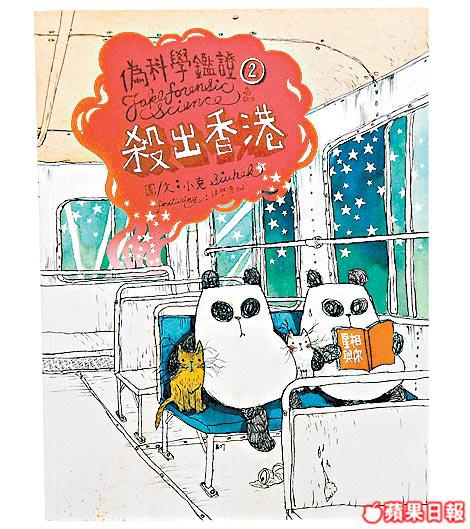
小克自稱「插畫家」。其實不,他走的創作路,是近文學多一點,他的畫有對話時是漫畫,多字的時候,就變成了插畫,旁邊的文字才是主角。與他談話,發現他跟一般繪畫人很不一樣,小克寫、談都條理清晰──而一般插畫/設計人總愛說「我係Visual人嘛!」來掩飾自己思路不整、文字表達力不足。
小克畫風雋永,帶點童趣,Unfinished的鉛筆水彩作風意猶未盡,真人作風卻是大不同,雖然談吐同樣斯文有禮,卻是言無不盡,而且帶着年輕人對社會的不滿與憤怒,談到政府的保育、談到灣仔復修的破廟,他青筋暴現,怒罵:「你看看那座洪聖古廟,它的外牆本來是由青磚砌成的。青磚造法複雜,現在要到內地才能找到人製造。復修這座古廟,理應先找人造青磚,但政府竟然使用三合土把牆完全封閉了,然後用白色漆油畫上白英泥磚縫!」訪問過後我也到廟外看看,不禁失笑,但訪問時看着怒氣沖沖的他,我不禁問:「你都幾憤世嫉俗?」他答:「梗係!我三代都在灣仔居住,看着政府的一些處理手法,實在好激氣。」問小克他的朋輩會不會覺得他很維園阿伯?起初他答不會。訪問過後他再致電補充,「其實談得到這些的,都是創作界的朋友。」
他的怒氣,其實在畫中也隱約可見,只是藏了起來。「我看龍應台的書有很大的感受,她可能也憤怒,但採取了一個相反的形式去做。她的寫法,就像是個媽媽在跟你說話。看看胡恩威,他的書就比較憤怒,再看看陳冠中,他可能採取學術性一點的角度,但有一種關懷的態度。以上三人要說的內容可能都一樣,只是關乎作者怎樣去Output。」於是他採用了一個畫/字融合的方式去表達,愛上了文字以後,繪畫出身的他發現畫面不是從前想像那麼重要:「所謂最勁的畫面,原來都係文學上、音樂上的。在你心目中的畫面比畫出來的更厲害。」
愛上文字──如同他的職業生涯,其實是個意外。小克畢業至今沒有返過一份正職工作,先在畢業展覽上獲攝影師WingShya青睞,被羅致到王家衞的工作室去,集體創作,卻不只限繪畫,頭幾個Project其實都難產了,卻是他生命中獨特的訓練,「例如在《2046》,當時幾個創作人一起,一個來自台灣、一個新加坡,然後就由一個概念──例如『承諾』開始去想,想到些甚麼再交給王導演。」小克坦言其實自己如同其他繪畫人一樣,本來都只是看漫畫看卡通看電影,少看文字書的,因工作開始讀了起來,卻越讀越有味。「做電影不找書看不行,例如他給你的題目只是『杜月笙』三個字,其他一片空白,你便只好找一叠書回來猛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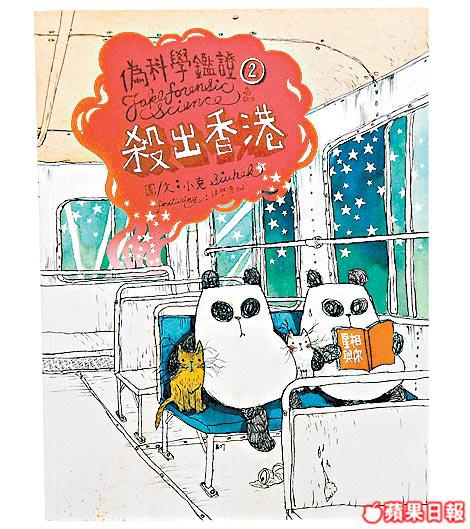
後來他為李碧華的《煙花三月》作攝影師,到大陸採訪一個星期。意外接了這個Job,也意外地影響了他一生,「當年要影菲林,都驚㗎!」此書寫的是慰安婦(袁竹林)的一生,當中牽涉整個中國近代史,回來後看了不少關於文革的書。「以前亦聽過文革,但去了才知道我們今天的一切,很多都受到文革影響。」
再之後,他與林海峰合作,連年合寫了幾個廣播劇劇本,最著名的叫《鴿子園》。
他顯然不甘心當個插畫家──他有太多話要說──在漫畫中,他大篇幅寫家中老貓(寫感情)、嘲弄他認為是錯的(《維港系列》寫環境保育,近日又在嘲笑本地潮流雜誌的日式中文),以上種種,寫的都是一種已給送到填海區的舊價值觀。問影響他最大的作家,他想也不想先答手塚治虫,「他說的,都是導人向善等等的舊價值,一些永恆的東西。再回頭想想近年最紅的漫畫,卻是《死亡筆記》,講述一個年輕人怎樣殺人的漫畫,是不是有點心寒?」
微妙的是,他的漫畫在年輕人潮流雜誌上連載,雜誌前半部叫人買甚麼才「潮」,到他的漫畫卻是老舊才有的價值。他說:「甚麼是潮流呢?我想了好久,其實這些舊東西/舊價值才是潮流啊。它們永恆不變,不等多久它們又會再回來了。」要等這個潮流回來我有保留,而如果它們真的回來,小克/楊學德可算是英雄了,他們的漫畫總滲着這種訊息,而且由小眾變得越來越有影響力。
以為他一定對新一代很不滿,現於理大作長期客席講師的小克,卻很維護後輩。「年輕人與我們一代相比,是欠了一點自信,我們的年代,接到功課,不是到圖書館就是去競成,找不到資料,就只好馬上開工了。現今資訊太多,隨便上網就可以看到一眾大師作品,然後一拼之下就沒有信心做了。連我都會上網看短片看到朝早6點,再加上𠵱家一部NDS竟然有800幾個Game,畀我係佢哋都會係咁!」
記者:何兆彬
攝影:林栢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