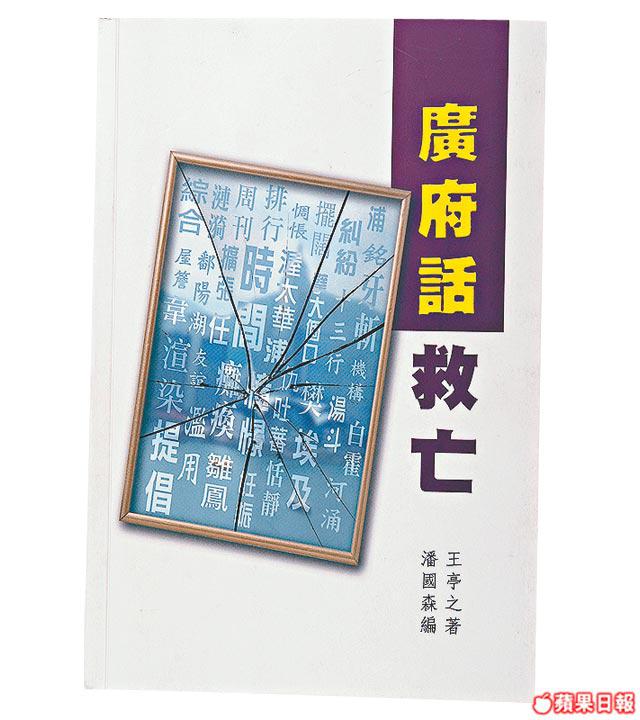
開着電視收音機,都在談「正字」。正字本來只是指寫白字、讀懶音,後來卻慢慢變成了「粵語正音」。活了幾十年的老香港,忽然發覺自己的廣府話大都「讀錯」了,甚至連自己的姓氏都讀錯。這種聲音,似乎慢慢變成了「主流」。
主流以外卻有另類聲音,「為甚麼要跟一千年前的《廣韻》來發聲呢?」是不少人的疑問。
潘國森是這個聲音的領軍人物,而祖宗人物卻是已移居加國的王亭之。在上月推出的《廣東話救亡》(潘國森編、王亭之著)中,他更向何文匯教授提出公開辯論的邀請,題目包括:
1.中原音傳入廣府,分為周秦;兩漢;魏晉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及現代六個時期,何以獨取《廣韻》為標準?
2.廣府話共有9聲,倘依照廣韻,則只有五聲,豈不是要廢去《廣韻》所無的聲調?
問潘國森,何教授可有反應,他說暫時未有。「不過我哋可以等,大家都知道何教授退休了。而亭老(王亭之)8月將會返港到北京去。就看大家能不能協調出一個時間來。」
翻開這本《廣府話救亡》,當發現文章大都是90年代由王亭之撰寫,而亭老談到「正音」,每每相當激動,更用上「邪音」、「病毒音」等字眼。出書有何緣由?「二十年前我跟亭老學過紫微斗數,後來他移民了。最近『正音』運動又再興起,其實民間有零星反對聲音,亭老的文章亦散見於網頁上。於是我提議出版這本書,一則為評論,二則希望做點教育工作。」除了出書,潘國森還辦了個「粵音文化傳播協會」,目前協會雖然有會址有電話,但潘國森說只是借用人家地方,暫時只製作網頁,做點教育工作,經費方面還不是問題。
「成個『正音』運動,據知最初係80年代由港大中文系一位教授開始的,他認為現今好多廣府話都讀錯了,應跟隨《廣韻》的讀法。到90年代『正音』運動漸漸滲入傳媒,電台、新聞主播開始將『時間』讀作『時奸』,不過反對聲音太大,沒多久這又銷聲匿跡了。」
「現時推行的正音錯得太多了,希望各界可以關注。第一件事好重要的是,今年起,會考改了Syllabus(課程),現今考會考,就如同英文考UseofEnglish一樣,只考中文應用。學生不再必須背《出師表》。但就需要考讀、講、聽、寫。」他翻開一本中五中文讀音課程,「你試讀讀,我想,我同你去考一定唔合格。例如佢會叫你棟樑讀『凍樑』、撰寫讀『賺寫』、僭建讀『佔建』……」
「讀音在考試是沒有準則的。有老師同我講,話同一個字,例如時間『諫、奸』兩個音佢都接受,咁遇上這個老師考生分數就會唔同。特別要注意係廣府話是方言,這樣子考試根本唔公平,考評局、教統局都需要注意。」
「另外,就係破壞家庭和諧。學生讀完返屋企,會突然發現老竇讀咗幾十年嘅字好多都讀錯,但係咪讀錯咗呢?老師、家長都有學問,都讀過書,怎可以就咁否定咗。《廣韻》當年只係一本語言手冊,而且方言,唔同鄉下都有唔同發音,語言又係會變化嘅。方言無所謂『正』。我們認為應尊重番老師所教嘅發音。」
訪問前他應邀到港大出席一個討論會,與會者包括「正音派」歐陽偉豪,「我問佢:正音派說會計應該讀『繪計』,咁如果畢業生去應徵會計一職,同人講話我『好鍾意繪計』,你估佢會唔會獲聘?佢答我:咁可以應徵時答會計,平日講『繪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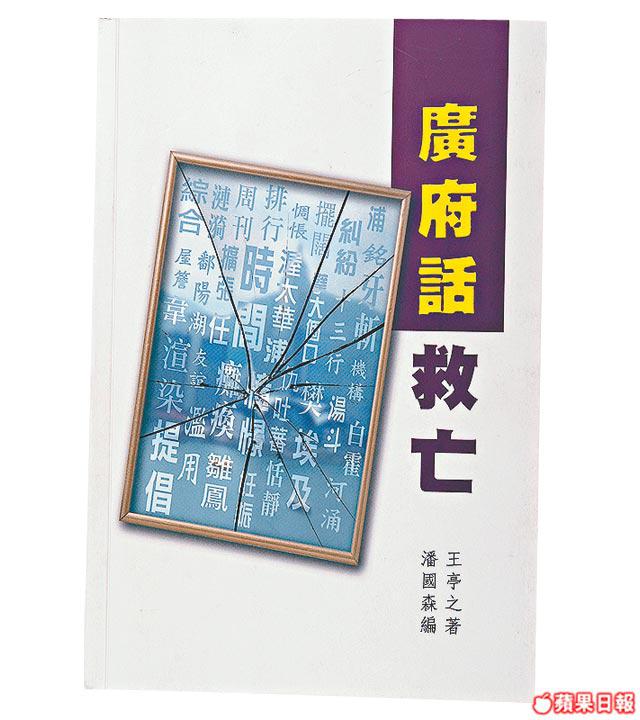
如是說,就沒有正音不正音之分了。
潘國森說,就是英文這樣規格化的語言,發音也沒有對錯可言。「喺英國,英國人最鍾意笑蘇格蘭人嘅發音。於佢哋來講,唔同嘅發音代表唔同階級。你有看過《MyFairLady》(窈窕淑女)嗎?主角Higgins會以發牛津音為傲,但亦無辦法迫窮等人跟佢發音!這種關係其實同經濟有好大關係。」
翻查潘國森的著作紀錄,近有《修理陶傑》、《Critiqueon陶傑》、《修理葉劉》之後,今年編排由王亭之撰寫的《廣東話救亡》,似乎好幾本都有「撩交嗌」之嫌。他很平靜的說:「讀書人就是應該這樣嘛,遇到不對的事情就寫出來。批評陶傑,部份是他資料上的錯,部份是他翻譯上的錯。」這倒令人聯想到俠義精神,也記起他是個「金學」專家,更自稱是二十世紀第二金學專家(他心中的第一是陳世驤),「當年寫第一本書就是評論金庸。因為覺得倪匡先生有些部份寫得唔係好啱。結果投稿香港出版社沒出得成書,倒是台灣出版社替我出版了。」在他心中,倪匡只是「讚譽金庸小說天下第一」。

記者:何兆彬
攝影:陳盛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