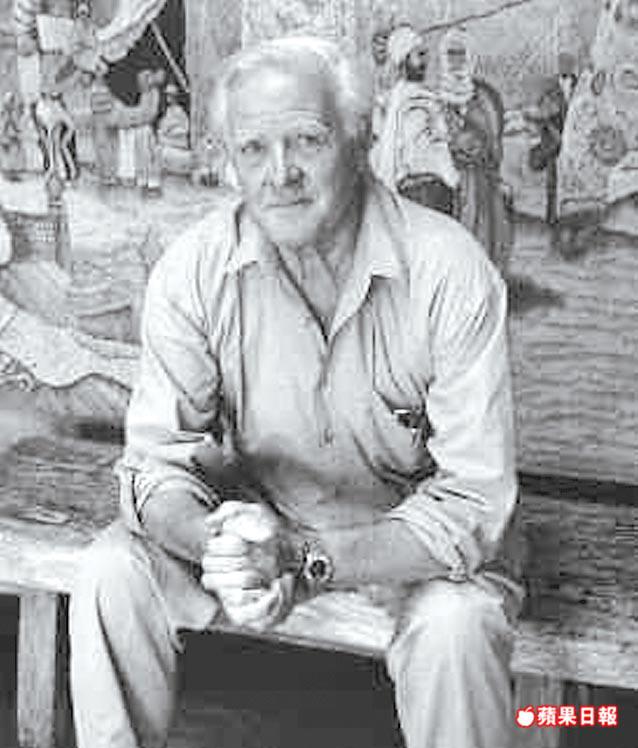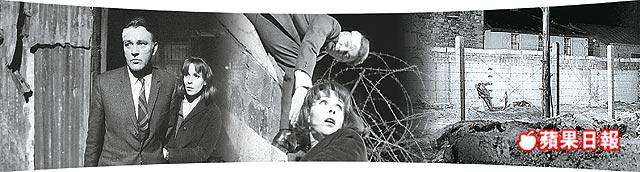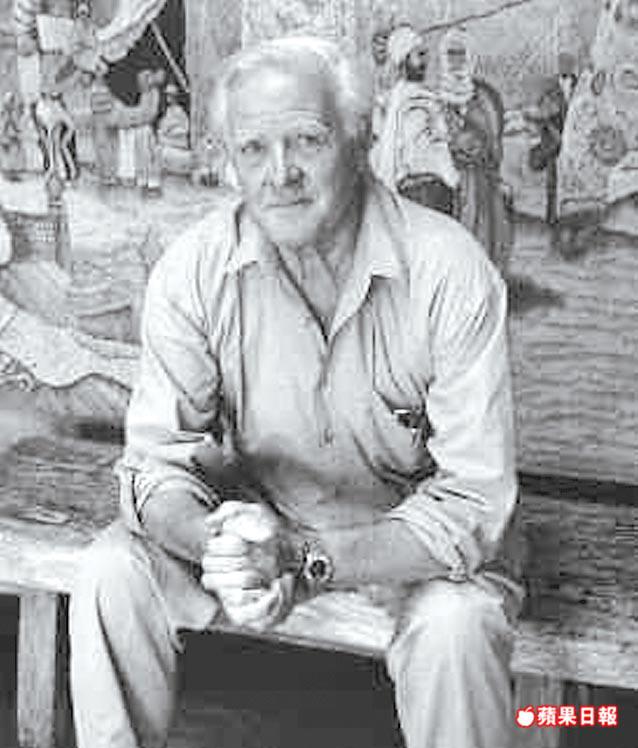
李歐梵
美國哈佛大學榮休教授
香港中文大學客座教授
我幾乎看遍所有的「007鐵金剛」影片,卻從來沒有看過一本佛萊明(IanFleming)的原著小說。此次新的占士邦影片在港上映,我趁着假期忙裏偷閒,先買了一本英文原著來看,卻大失所望。《皇家賭場》(CasinoRoyale)是佛萊明的第一部作品,初版於一九五三年,十多年後荷里活借用了小說的名字拍了一部同名電影,是個鬧劇,也僅用了書中的那個法國某小城的賭場作背景而已(這部新片中卻換成原南斯拉夫屬下的Montenegro)。這部新片《新鐵金剛智破皇家賭場》雖然較忠實於原著,但也加油加醋,改了不少,特別是片子開頭五分鐘的非洲追逐場面,也是全片最精彩的部份,其餘則乏善可陳。新任「鐵金剛」DanielCraig已不復前三任占士邦的瀟灑(見本報本版拙作),乃一介魯莽武夫而已,身手勇猛,但已無何風度可言,連在賭場中叫一杯特調的馬丁尼酒(是此書的最重要貢獻)也全不是味道,還差一點被毒死!然而此片賣座鼎盛,可見大部份觀眾早已嚮往另一個「肢體」占士邦的新典型,看來我的口味是落伍了。
沒有想到佛萊明的原著小說也同樣的粗糙,更缺乏幽默和智慧,全不是我想像中的文筆。也許他後來寫的占士邦小說較精彩,但看了這本小說之後,令我不得不更加感激在拙文中談到的第一位占士邦辛康納利和早期「鐵金剛」影片的導演泰倫斯揚,原來這份瀟灑竟然是在銀幕上創造出來的,為小說所無。原著中的賭局也簡單之至,全不須要動腦筋,佛萊明在書中的解釋也笨拙得令人失笑。如果和另一位英國間諜小說的名匠里加萊(JohnleCarr囗)比較起來,實在相差甚遠,於是我不禁又懷念起當年看過的這位小說家的早期小說來。
里加萊的《冷戰間諜》(TheSpyWhoCameInFromTheCold)出版於一九六三年,後來拍成電影,由李察波頓主演,大為轟動。然而他的第一本小說《呼喚死亡》(CallfortheDead,1961)卻似乎被遺忘了,他在此書中創造了一個和占士邦完全相反的主人翁──喬治.史邁利(GeorgeSmiley),貌不驚人,既矮又胖,娶了一個貴婦,卻又被她嘲笑玩弄,她在婚姻上不忠,屢有姦情,兩人終於離異。在此後的里加萊小說中,他皆以單身漢和公務員的身份出現,成了英國情報局的頭目,不過這部《冷戰間諜》小說和電影的主角卻不是史邁利,而是另一個「冷血」間諜,名叫Leamas,也是一個頹唐憤世的人物,但最終卻因愛上了一個圖書館員而犧牲自己,雙雙死於柏林牆下。記得初看此片結尾,令我不禁神傷。後來才看原著小說。我故意將書名中的「cold」一字譯成「冷戰」,其實原來語意雙關,背景既冷又是冷戰期間,英蘇對峙於東西柏林,而有名的柏林牆則是於一九六一年八月矗起的。據作者自己說,他寫此書的靈感就是得自於一次到柏林旅遊時目睹柏林牆的經驗,那股陰森氣氛,在全書最後一章──和影片最終一段──表現得淋漓盡致。
此次重看此片後我又買了一本此書新版重讀,二十多年前看的全忘了,只記得主要故事大概,此次我亁脆從最後一章──〈從寒冷中過來〉──讀起,文字簡潔得無與倫比,但卻處處照顧到細節,譬如描寫這對亡命鴛鴦在東德逃到柏林牆,牆的右邊七十碼處有一座守望塔,探照燈「枯黃又粉灰」(sallowandchalky)的燈光掃視牆外的無人地帶。接着是兩個短句:"Therewasnoonetobeseen;notasound.Anemptystage"。這類簡單句子表面上毫不顯眼,為甚麼在里加萊筆下顯得如此驚心動魄?然後兩人開始攀牆了,突然燈火通明,警笛大鳴,「他緊握着她的雙手,要把她拉上來,一吋又一吋地拉,他自己也幾乎要跌下去了。然後他們開槍了──單發子彈,三響或四響,他感到她的抖動,她細瘦的兩臂從他的手中滑了下去,他聽到牆那邊有一個說英語的人在叫:"Jump,Alec!Jump,Man!",他聽到的是史邁利的聲音,很近:"Thegirl,where'sthegirl?"。」
看到此處,我知道大勢已去,女友必死,但初讀時卻沒有料到Leamas竟然稍作遲疑後又爬了回去,站在女友旁邊,與她共同受難:「她死了,她的臉躲開了,她的黑髮落在面頰上,像是在為她自己遮雨」。最後他也在兩三聲槍響下倒斃,死前的最後幻象是「看到一輛小汽車被大貨車撞碎了,而孩子們卻在窗邊招手。」
這種句法和意象,佛萊明就寫不出來。也難怪此書出版後,英國名小說家格林(GrahamGreene)讚道:「這是我看過的最好的一本間諜小說」。里加萊也大有格林之風,以精闢的語言文字營造氣氛和人物,而且字裏行間蘊藏着一股哲理。
如果把佛萊明的《皇家賭場》與之相較,高下立見,佛萊明全不是對手。第一章一開始還不錯:「賭場的味道,煙味和汗味,在清晨三點鐘的時候令人發嘔……占士邦突然感到他累了」。但到了第二章就不忍卒讀,用一紙「備忘錄」交待俄國壞蛋人物和情節,還加上幾句法文。公文有甚麼好看?偶一為之尚可,但竟然全章都是公文!我耐心地把全書看完,實在感到無聊之至。情節當然有高潮起伏,但占士邦影片看多了,也不覺得驚奇,甚至有些細節──譬如占士邦把自己的一根髮絲偷偷繫在旅館房間門上──早被電影用過了。直到最後一章,寫的是這個俄國女間諜死了,留下一封遺書,第一句就讓我倒胃口:"IloveyouwithallmyheartandwhileyoureadthesewordsIhopeyoustilllovemebecause,now,withthesewords,thisisthelastmomentthatyourlovewilllast.Sogood-bye,mysweetlove,whilewestillloveeachother.Good-bye,mydarling."
這種「廉價英語」有甚麼好看?當然,俄國女間諜只有美色而沒有文采,但既然如此為甚麼又寫下這麼長的信?交待真相也!這三句英文也很簡單,但第一句太過冗長,最糟的就是用一個軟弱無力的連接詞「while」,最後一句既肉麻又俗套,豈可與《冷戰間諜》的結尾相提並論?所以在新版的《皇家賭場》影片中亁脆省掉,只留下手機中的一個電話號碼。占士邦小說最可取悅讀者,總是令這個「鐵金剛」所向無敵,最終當然勝利,沒有太多人味,新片更是如此,更無所謂「智勝」皇家賭場。然而「鬥智」卻是里加萊小說的主題:爾虞我詐,互相出賣(betrayal),這就是間諜遊戲的本質。
四十年前他已經織造了一個「卧底」的人物和情節,後來被其他小說家和編劇家一抄再抄,竟然港片也將之發揚光大,《無間道》發明了相互卧底的絕招,也立刻被荷里活抄了過去,其實這本是《冷戰間諜》的傳統。
論起情節,里加萊的早期小說並不精彩,《冷戰間諜》只是在製造一波又一波的出賣和不信任而已。只有到了《Tinker,Tailor,Soldier,Spy》(補匠、裁縫、士兵、間諜),情節才曲折起來(該書曾被拍成電視連續劇,轟動一時),但基本上還是以人物為主,特別是這個其貌不揚的史邁利,從《召喚死亡》到《史邁利的人物》(Smiley'sPeople)一路發展下去。里加萊本擬以此人為中心寫十數本小說,卻發現史邁利這種人物早已落伍,冷戰結束了,史邁利也終於見到了俄國對手Karla,原來兩個人差不多半斤八両,皆是同一型的人物。這是里加萊自己說的,我沒有看過他的所有小說。
他的小說中有一本卻引起了我極大的興趣:《榮譽學童》(TheHonorableSchoolboy),我正在閱讀中。此書是他在七十年代到香港和東南亞各國實地勘察後寫的,和往常的「閉門造車」方式不同。我迫不及待地看到第七章,寫的是香港快活谷的賽馬,倒真是描寫得入木三分,不但把馬場的實地描述得十分細緻而幽默──「快活谷的賽馬場的草地必定是世界上最昂貴的草地,因為草太少了」──而且也創造出來一個華人富翁人物,DrakeKo,O.B.E.,此人來自上海,但又是祖籍汕頭,表面上不問政治,卻私售軍火到中國大陸,因而致富。此節描寫他和夫人看賽馬贏後,又私自和一個金髮美人揚長而去,在故事的主人翁──一個假扮記者的英國間諜──冷眼旁觀之下,饒有風趣。至於是否影射真實人物,此處就不便多作揣測了。
香港影迷當會記得最近在港上演的影片《TheConstantGardener》(無國界追兇),也是根據里加萊的近作改編的,他在此片的DVD版中現身說法,大讚此片的改編手法,認為用原著最少情義作最大發揮,但仍忠於原著精神的才是最成功的影片;換言之,小說和電影是兩種毫不相同的藝術品種,這當然盡人皆知。然而,為甚麼《冷戰間諜》幾乎原封不動地將原著搬上銀幕,而依然出色?他卻沒有回答。我認為里加萊近來的野心太大了,他想逾越間諜小說的類型,去大談「全球化」引起的資本主義侵略或種族文化糾紛的大問題,非但史邁利不見了,而且根本沒有甚麼間諜味道可言。《紐約客》雜誌最近刊登了一篇書評,由名小說家JohnUpdike執筆,提到里加萊的幾部近作,皆是和剛發生的世界大事密切相關,從《Single&Single》(1999,主題是蘇聯解體)、《TheConstantGardener》(2000,非洲人被大資本的藥廠當實驗品)、到《AbsoluteFriends》(2003,作者對英美出兵伊拉克大為憤怒)和剛出版的《TheMissionSong》,又回到當年名家康拉德(JosephConrad)筆下的剛果,但Updike認為此書主題先行,說教之處太多,已不復當年的雄風。我本也想買來讀讀看,但假期已過,又要返工辦正經事──教書──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