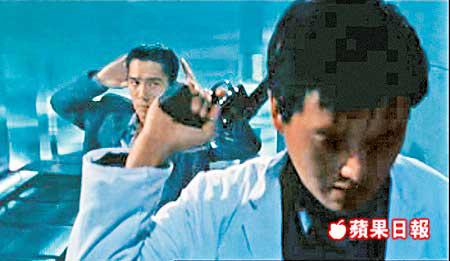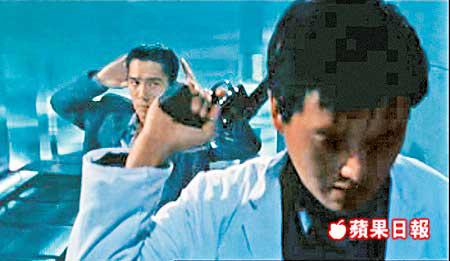
李歐梵
美國哈佛大學榮休教授 香港中文大學客座教授
在梅維爾導演的《紅圈》的雙碟DVD版所附帶的資料中,有吳宇森用英文寫的一篇短文,最後一段話是這麼寫的:
「《紅圈》是一部對白甚少而充滿氣氛的影片,Jean-PierreMelville是一位紳士,他相信一種(很像亞洲哲學)榮譽的道德規律,他會剪接,更會運用開麥拉,非任何人可及。他給予我不少靈感的時刻,我用之於自己的一些作品中,譬如《英雄本色》、《喋血雙雄》和《辣手神探》。他的作品有一種冷峻和一種風格與其他同一時期的導演不同。」
這段話,也可以說是吳宇森的自我見證。他在文中再三講到朋友的義氣,並且說他特別喜歡片中依夫蒙丹(YvesMontand)飾演的角色,頗為認同。這個窮途潦倒的警探詹森,也是神槍手,最後在阿倫狄龍飾演的科里邀請之下,參加半夜打劫珠寶店的計劃,一槍打中安全系統的鎖孔。這場戲也是吳宇森最喜歡的兩場戲之一:詹森把槍架好,一切就緒之後,卻突然把槍從預先備好的毫釐不差的射擊架上拿下來,以雙手舉槍瞄準,一擊中的!這場經典戲,在吳宇森看來,是因為他交了這個朋友科里,在友誼的支持下,使他重拾自信,所以當科里事後來他的斗室拜訪的時候──這是吳宇森最喜歡的第二場戲──他就說自己不要分贓了,而要感謝科里才是,而當科里望着壁櫥時,他笑了,因為他已不再懼怕壁櫥內(也就是他內心中)的魅魑魍魎。吳宇森認為是友情救了他,不錯,但我覺得朋友只不過是一種「導體」,把他心中的勇氣和自信引出來了。詹森的奮鬥掙扎,從頭到尾都是孤獨的。我個人喜歡的第三場戲,就是詹森在作案之前的夢魘──蛇蠍蟲蜥,一個個從櫃中爬出來,有的爬到他床上,這場戲的場景調度真不得了,因為大部份的怪動物是真的,梅維爾自己要指揮動物演戲。我第一次看,見到蛇就閉上眼睛,此次重看,才發現除了蛇和老鼠之外,還有幾條綠色的蜥蜴,爬到床上,和床單的驂綠色合在一起,搭配絕妙,原來這場戲的美工作得如此仔細,禁不住叫好。
吳宇森得梅維爾真傳,把那場槍擊安全鎖的鏡頭幾乎照搬到《辣手神探》中的一場戲中:周潤發和梁朝偉被困在醫院地下,必須把鐵牆中的一個鎖洞擊穿;周潤發一舉而稍氣餒,再舉時有了自信,才一發而中,可是片中卻缺少了一份孤獨者內心掙扎的過程。可見吳宇森更重朋友之間的肝膽相照,而非個人的孤獨感。但片中梁朝偉飾演的卧底警察──也為多年後的《無間道》定了型──卻是一個真正孤獨者的典型。他和《喋血雙雄》中周潤發飾演的獨行殺手相似,而周卻角色互換,在《辣手神探》中成了警察,換來換去,依然是一個模子。然而這份個人的孤獨感,在友情和義氣支撐之下,也逐漸消失了。在這方面,吳宇森是一個徹頭徹尾的中華文化的信徒,所以他在此文開宗明義地說:「我相信我的世界,我相信兄弟義氣和一切與此有關的東西,例如榮譽、忠貞、友誼。《紅圈》之所以成為盜匪片中的經典就是它體現了這種浪漫精神。」不錯,然而在西方世界中,朋友之間的義氣也可以是互相疏離的,每一個人有自己的世界,而每個人的命運不同,但轉來轉去,因緣際會,終有一天,幾個人的命運會碰到一起,所以佛祖以紅粉筆畫了一個「紅圈」。這是片首梅維爾引用的一段出自佛經的話語,是否有此說法,有待考證。在此片中將三個孤獨者的命運連在一起的就是偷劫珠寶的計謀,這才是全片的關鍵所在。就像中國武俠小說之中所說,不能有勇無謀(但吳宇森影片中的角色往往如此,在《英雄本色》中張國榮所演的警察弟弟,更猶有過之)。而這種「謀略」,卻反而是梅維爾手法的最大特點。
梅維爾為了這場盜寶戲,真是老謀深算,煞費周章。全部搶劫過程整整二十分鐘,皆在靜默中進行沒有對白。而且地點是巴黎塞納河邊最繁華的市中心──PlaceVendome──猶如太歲頭上動土。梅維爾早就有拍這段戲的念頭,但偏偏無獨有偶,另外兩部名片──美片《夜闌人未靜》(TheAsphaltJungle,1950)和法片《Rififi》(大陸譯名「男人的爭鬥」,1954)──內中皆有劫珠寶店的場面,只好延擱下來,等到一九七○年才拍《紅圈》。其實現在看來,戲中的動作沒有甚麼了不起,但氣氛和場景的掌握,可謂獨一無二,再加上依夫蒙丹那一槍,遂永垂不朽。
梅維爾的冷峻風格在此也表露無遺,可用一個字來形容──靜。靜是一種冷漠,是把人物放在肅穆蒼涼的環境中(《紅圈》的整個故事都在秋冬雨雪中進行),更顯其孤獨,也發人深省,所以一位西方影評家認為:梅維爾的電影是「深思」(contemplative)型的。如何思法?這就牽涉到梅維爾的人生觀了。他自己也個性孤獨,不拍戲時,自己關在家裏寫劇本,他是夜貓子,整夜不眠工作,而且親自設計一種隔光板,放在窗上,陽光射不進來。《紅圈》中偵探的辦公室就是如此。這種「自閉」手法,也不完全是個性使然,我認為和他的人生哲學有關。他那個年代還是法國存在主義鼎盛的時期,我猜他有意無意之間吸收了法國戰後存在主義的基本觀點:人生是荒謬的、虛無的(沙特),意義是人創出來的,而且是悲劇(卡謬)。梅維爾的作品,貌似商業電影,但內涵卻有深刻的一面,特別是人物不出聲在街上走、搶銀行,或出門前在住宅室內四望,總覺得這一切都是生離死別……。這一套理論,西方研究梅維爾的影評家早已說盡。
然而吳宇森呢?七十年代他在《中國學生週報》撰稿時,想也看遍法國「新浪潮」的電影吧(在當年大會堂的StudioOne),而「新浪潮」的主將如高達和杜魯福,也師崇存在主義或汲其餘緒,所以他們也喜歡梅維爾,高達在《斷了氣》中甚至還引了梅維爾的另一部影片《BobLeFlambeur,1955》的名字。吳宇森不會不知,連他自己也在《縱橫四海》中把兩個男主角說成「祖與占」(JulesandJim,杜魯福名作)。然而吳拍的所有警匪片都熱熱鬧鬧,打打殺殺,毫無孤獨感,甚至連《喋血街頭》中的獨行殺手也是如此。只有在《英雄本色》第一集的少許場面──如潦倒Mark躑躅街頭──才略有孤獨味,是否完全為了「票房價值」?但吳宇森的確發揮了梅維爾影片中「浪漫」的一面,然而他卻把「浪漫」建構在榮譽、忠貞和男人的兄弟友情之上。看多了,覺得有點過份,甚至整個劇情架構也有「氣」而無力,內中極少發人深思的「空白」,這恰是梅維爾影片最出色的地方。梅維爾很少用慢鏡頭,動作也不多,然而他的剪接法和鏡頭運用卻把他獨有的「靜」景發揮得淋漓盡致──在一片孤獨的空間中包含了另一種人性的孤獨,而其終極就是死亡。所以梅維爾影片最微妙的鏡頭往往用於死亡的象徵中。《紅圈》中有一場與故事無關的過場戲:在夜總會的舞台上一群女郎正在跳非洲舞,鏡頭轉到一個賣香煙的女郎,她拿了一朵紅玫瑰,若有所思,然後轉身交給坐在旁邊沙發的阿倫狄龍;他一個人坐在那裏,正等待一個買珠寶的陌生人,從此自投羅網。他接了那朵紅玫瑰,輕聞一下,我想就在那「浪漫」的一刻,他早已預知自己的身世──步向死亡。在梅維爾前一部名作《獨行殺手》中,狄龍飾演的殺手更孤獨,也在夜總會的舞台上看到一個黑人女歌手,受其蠱惑,甚至她就是死亡的象徵或「導體」。這一個主題,在吳宇森的《喋血雙雄》中改頭換面,歌女被周潤發飾演的殺手無意失手打盲了,於是殺手為她而求救贖。這是托爾斯泰或杜斯陀也夫斯基的體裁,被吳宇森浪漫化了。在全片的最後一場戲中,教堂出現了,白鴿子也出現了,這個「宗教情操」也成了吳宇森的「商標風格」之一。然而我們如把這場戲──在大開殺戒之前──與《紅圈》的最後一景比較,則會發現後者也有一個教堂式的別墅,在長鏡頭中燈火通明,但前景的樹林則是黑暗的,三個孤獨者,一個接一個轉了回來,在此接受死亡,沒有得到救贖。全片結尾的那一股蕭颯之氣,令人低迴不已。
據聞吳宇森有意重拍此片,如果屬實,當是令人興奮的好消息。然而,時代不同了,在今日荷里活是否還可以拍出像《紅圈》這樣的法國片?如何拍法?以「動」制靜或是動中取「靜」?宿命感和哲學味是否還拍得出來?有很多人說:梅維爾一生崇拜美國電影,他只不過是流落在法國的美國導演。吳宇森呢?他自願流落美國,如今是否還能拍出一點「港味」和法國味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