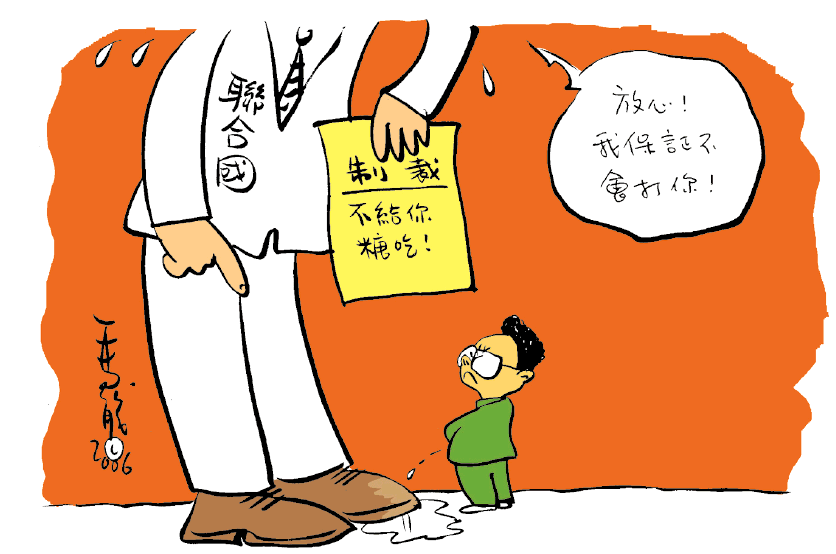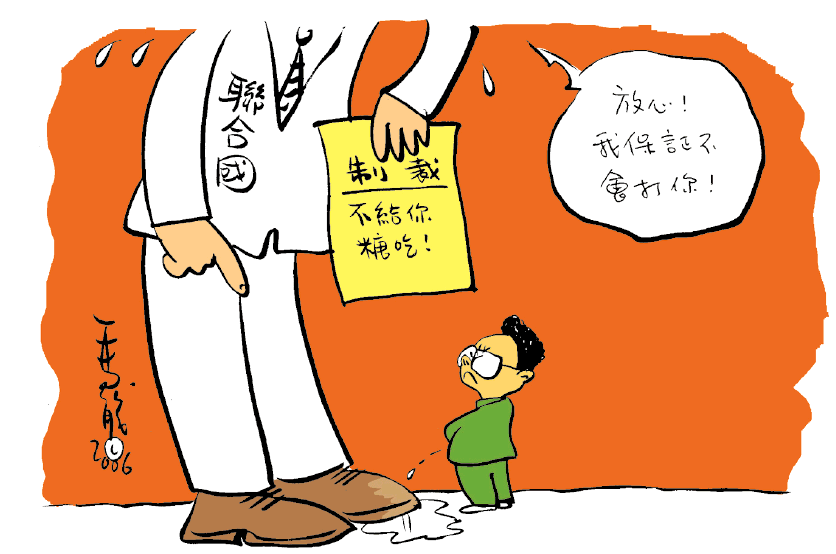
只要古巴向西半球任何國家發射核彈,我們就應視之為蘇聯攻擊美國,並採取全面報復措施回應蘇聯。此事應訂定為國家政策。
約翰.甘迺廸總統一九六二年十月二十二日
柯翰默 CharlesKrauthammer 《華盛頓郵報》專欄作者
這,才叫威懾。
以上這段談話中,甘迺廸矢言只要古巴發射核彈,美國甚至不必報復古巴,直接找源頭算賬,以大規模核武攻擊,和蘇聯決戰。在一九六二年,如此威脅極為可信。更確切地說,其可信度維持了冷戰期間半個世紀的和平。
當你無法讓敵人裁減軍備時,你要做的就是威懾。你不能奪走他的武器,但你可以讓他們不用這些武器。很久以前,我們對北韓曾經進行到此一階段。人人都曾嘗試找出讓北韓裁減軍備的辦法,但從未成功,金正日不會放棄核武。讓這個政權放下武器的唯一辦法,就是摧毀它。中國可以用制裁的方式做到,但中國不會這樣做。美國可以用發動第二次韓戰達成,但美國也不會這樣做。
所以,我們回到威懾手段。北韓鹵莽地加入核武俱樂部,令人回想起古巴飛彈危機,美國必須迅速立起威懾標誌。布殊總統立起了兩枚標誌。
防止盟邦受攻擊
第一枚標誌相當直接,但也相當溫和,是要防止我們在該區域的盟邦受到攻擊,總統在一項全國性電視演說中表示:「我向該區域的盟邦(包括南韓與日本)重申,美國會完整達成威懾與保安的承諾。」眾所周知,美國在太平洋沿岸地區數十年來張開的核保護傘,承諾美國若攻擊北韓(可能是實質的核子報復),前提必須是因為它先攻擊我們的盟邦。
可怕的事,但在核子時代卻司空見慣。困難的部份是布殊試圖立下的第二個標誌:核擴散威懾。
我們身處的年代,遠比甘迺廸的年代複雜,因為那時的巨大危機是在恐怖主義時代來臨前發生的。一九六二年的世界,科技與意識形態層面仍然純樸:體積縮小的核武、現代化的國際恐怖主義還沒被發明。五年後,阿拉法特與巴勒斯坦解放組織才以完美的政治性劫機,給世界送上大禮。
防止北韓核擴散
自此,恐怖主義在普及性、雄心與危害程度等各方面大幅增長,其實踐者就是核武市場上的買家,除了他們外,北韓幾乎沒有別處可賣。
因此布殊企圖建立第二種形式的威懾:「北韓將核武或核武原料移轉給其他國家、或非國家的實體,會被視為對美國的巨大威脅,此種行動的後果,我們會要北韓負起完全責任。」
這第一份草案很好,但它其實可以使用一點甘迺廸式的明確性。「負完全責任」這措詞無法製造恐懼感,正如它過去曾被數任政府漫無章法地用於警告恐怖分子與流氓國家──而之後甚麼也沒做。以下是一個比較好的構想。
「基於沒有其他擁核政權如此鹵莽地違反其應守的核子義務,本國應訂定政策,將任何針對美國或其盟邦所進行的核爆,視為北韓對美國的攻擊,並採取全面報復措施回應北韓。」
確保伊朗不擁核
這才是防止金正日進行核擴散的辦法,要他了解,他能否倖存將取決於買他武器的恐怖組織的行動。任何恐怖分子引爆的核武,都會被認為上面有他的地址,美國隨後就會回郵。這樣的自動反應才能讓他提高警覺。
然而,此番政策也有障礙,它只在全球僅有一個流氓核子國家時適用。一旦這個俱樂部的會員增至兩國,這政策就會失效,因為一項核子恐怖攻擊,不再只有單一的自動回覆地址。
這就是為甚麼防止伊朗擁核如此重要的原因。北韓已不可能走回頭路,但伊朗還沒有到這個地步。一個流氓國家尚能容忍,因為它讓我們可以找到責任歸屬;兩個流氓國家無法威懾,核子恐怖主義也將無可避免。
逢周二刊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