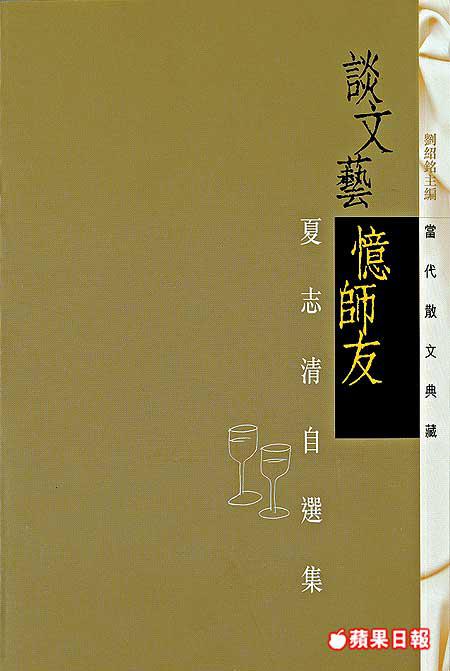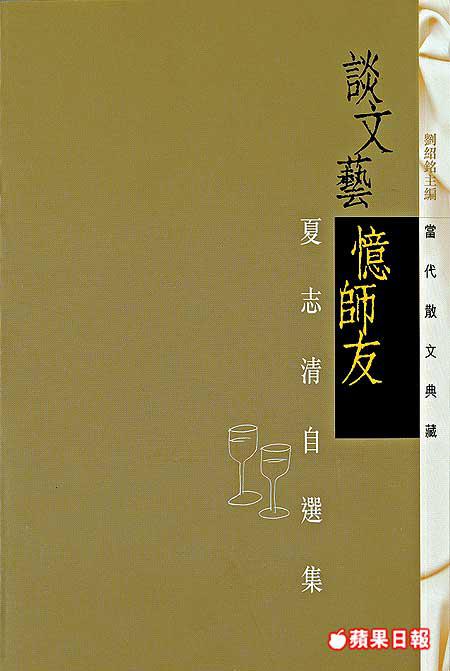
王德威 哈佛大學東亞語言及文化系EdwardC.Henderson講座教授
今年臺灣中央研究院院士選舉,夏志清教授以最高票當選人文組院士。以夏先生在國際漢學界的地位,這是項來得太遲的榮譽。院士的推選有許多機緣因素,夏先生沒有及早入列,是中研院的損失,但誠如資深歷史學者徐倬雲教授所說,有了夏先生,「大家的位子才總算坐得穩些。」
香港天地圖書公司最近推出夏志清教授的《談文藝,憶師友》,可謂此其時也。這本選集精選夏先生多年來的散文作品,很可以讓我們一睹大師的另一種才情。雖曰散文,先生下筆仍然一絲不苟。不論是記述北大、耶魯求學的經過,或是議論京劇人物、好萊塢明星,都是娓娓道來、信而有徵的文字。至於與顏元叔教授論戰的〈勸學篇〉,或是側寫話劇名家曹禺的〈曹禺訪哥大紀實〉等,則又顯示一種犀利率直的筆鋒。
初次見到夏先生時我還是博士生。聽他發表《玉梨魂》專論,明明知道題目重要,卻怎樣也弄不清為甚麼民初才子佳人要和馬龍白蘭度發生關係。夏先生學問淵博,講起話來卻連珠炮似的,天南地北,堅決與文法為敵。日後我有幸在哥倫比亞大學追隨先生十五年,對他的語言風格自然深有體會──也不免是他實驗的對象。夏先生治學嚴謹,讀他的英文著作《中國現代小說史》、《中國古典小說》等但覺議論宏偉,文采動人,道地的一家之言,然而日常談話,套用也是天地剛出的吳魯芹散文集書名,夏先生的嘉言足堪編出多冊《瞎三話四集》。
然而夏先生的散文卻顯現了與論文或談話完全不同的丰采。他論人敍事,率皆綿密周延,甚至不乏旁徵博引的片段。難得的是行文一清如水,極為可讀。夏先生每每自謙浸潤英文多年,不慣經營精緻的中文,我倒以為字字親切實在,反而是他的特色。他寫家庭和學校生活的點滴,美國和台港學術圈內的來往,親友故舊的情誼,認真而且「任真」,感情自然流露,幾乎有了口述歷史的魅力。
夏先生愛朋友,喜詼諧,真可謂有先生處即有笑聲。但我讀他的散文,每在字裏行間看出憂鬱的痕跡。像〈上海,一九三二年春〉記述他少年在上海求學、生活的片斷,乍看平淡,卻道盡並不寬裕的家庭生活,十里洋場的喧囂,還有「時代惘惘的威脅」。是在這樣的環境裏,他發展出對好萊塢電影的興趣,如醉如癡,甚至當作獨門絕學。多年以後他在紐約不斷重溫老電影,想起「故舊半為鬼」,唯有銀幕上的影像依然活色生香。逝去的「少年時代的海上繁華夢」,豈竟真是如電如影?
又如〈紅樓生活志〉、〈北平,上海,俄亥俄〉兩作,寫的是他赴北大任教,輾轉出國,最後就學耶魯的往事。從北大到耶魯,這看來一帆風順的路子其實包含太多因緣際會和意志力的挑戰。夏寫北大紅樓食宿的粗劣,南人北上的文化差距,隔了六十年,讀來竟有奇趣。而他抵美之初的曲折,不是對學問有巨大的熱情,不可能有如此克服萬難的決心。生活的不安猶其餘事,亂世的隔絕和倥傯纔是更大的考驗,然而夏先生字裏行間的重點依然是讀書寫文章。這是那一輩知識分子的本色了。
而夏先生最終的關懷還是家人朋友。因為他的推薦,錢鍾書和張愛玲得以成為現代文學的大家。一九七九年錢鍾書訪問美國,夏寫他的驚人才華,也寫他對政治的謹小慎微,閒閒數筆,感慨盡在不言之中。而他悼張的文字劈頭就是「張愛玲終於與世長辭」,一句話就點明張的「神話」意義和兩人之間的默契。但最令人動容的還是〈亡兄濟安雜憶〉一文。夏氏昆仲同好文學,而且各有所長,一九四九年後兩人寄寓海外,天各一方,反而更為親近。一九六五年夏濟安(1916-1965)猝逝,學界為之震動,對志清先生的打擊可想而知。但他對亡兄的悼念沒有涕淚交零,而是憶述往日彼此鼓勵、相互論學的點點滴滴,流露的不只是手足之情,更是一種惺惺相惜的知己之情。
談夏氏昆仲不能不談吳魯芹(1918-1983)。吳魯芹出身武漢大學,英美文學造詣絕佳,五十年代在台大外文系任教,與夏濟安等共創《文學雜誌》,之後赴美。吳雖為學者,反而因為散文雋永幽默而見知於世。他在夏濟安逝後曾寫〈記夏濟安之「趣」及其他〉一文,描寫夏的文才,習慣性的緊張害羞,還有童心趣事──包括冒名頂替為吳上小學的女兒寫作文。吳魯芹文筆生動詼諧,他筆下的夏濟安大智若愚,可敬可愛。如果我們理解時代的背景是五十年代百廢待興的臺灣,吳夏諸人的情誼和風度,就更令人懷念。
吳魯芹究竟是怎麼樣的人?夏志清先生其實曾經有長文介紹,但並未收入《談文藝,憶師友》書內,倒是天地版《瞎三話四》附錄可以得見。吳長夏先生三歲,也曾經過離亂病厄,但是他的文字輕鬆自如,寫的都是人間煙火戰火,卻絲毫不見火氣。吳善於自嘲嘲人又不失分寸,十八九世紀英美小品文的影響歷歷可見。有名的〈雞尾酒會〉寫盡洋派社交場合的造作張致,有類似經驗的讀者都要會心一笑。他的六十宏願沒有高調,而是「我已經六十歲了,不能再這樣規矩下去」,痛快痛快。
在上個世紀革命啓蒙的喧囂中,吳魯芹這樣的文字代表了一種極不同的人生觀:他是個「選抵抗力小的方向走路的人」。惟其如此,他反而能以小觀大,談俗,談懶散,談請客,談文人無行,乃至於談生死。吳的〈泰岱鴻毛只等閒〉有言:「人總歸不免一死,能俯仰俱無愧,當然很好,若略有一些愧怍,亦無大礙」,寬容灑脫,真是聞其言如睹其人。一九八三年吳先生在酒會之後突然撒手而去,走得輕鬆,竟印證了他一生行事的信念。
夏氏昆仲和吳魯芹教授都是在三、四○年代成長的學者。歷史的情境如此不利,他們卻居然造就了一身學問。他們都是西學出身,但是舉止言談,活脫是《世說新語》裏跳出來的人物。
以輩份而言,他們都是我老師的老師。濟安和魯芹先生去世得早,我無緣受教,唯有志清先生依然健朗活潑如昔。從他的學問言談裏,我可以遙想當年人物的文采風流。求諸今日,何可復得?倒是天地出版公司的兩冊文集《談文藝,憶師友》、《瞎三話四》,多少還為我們保留了一個時代文人的風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