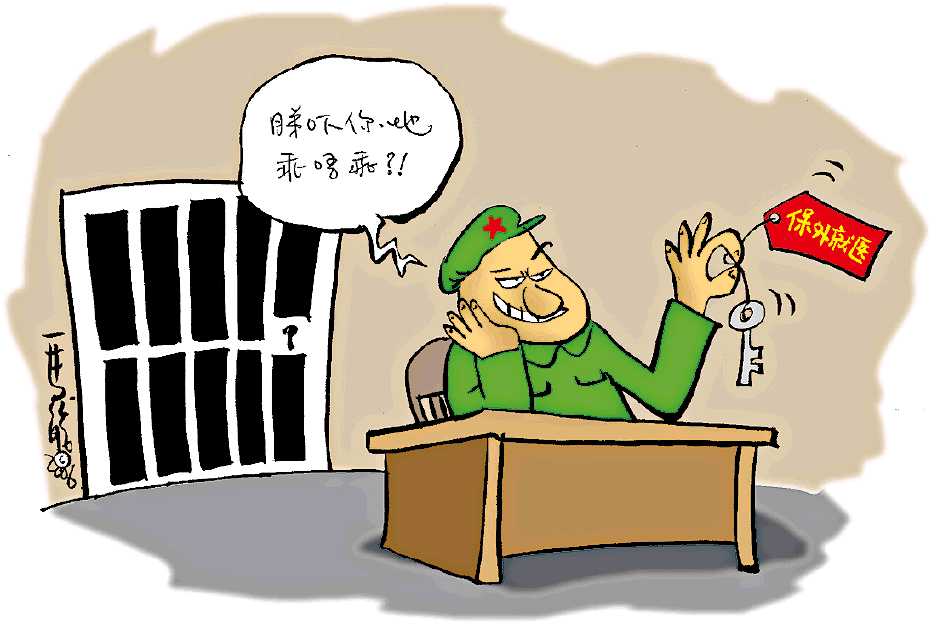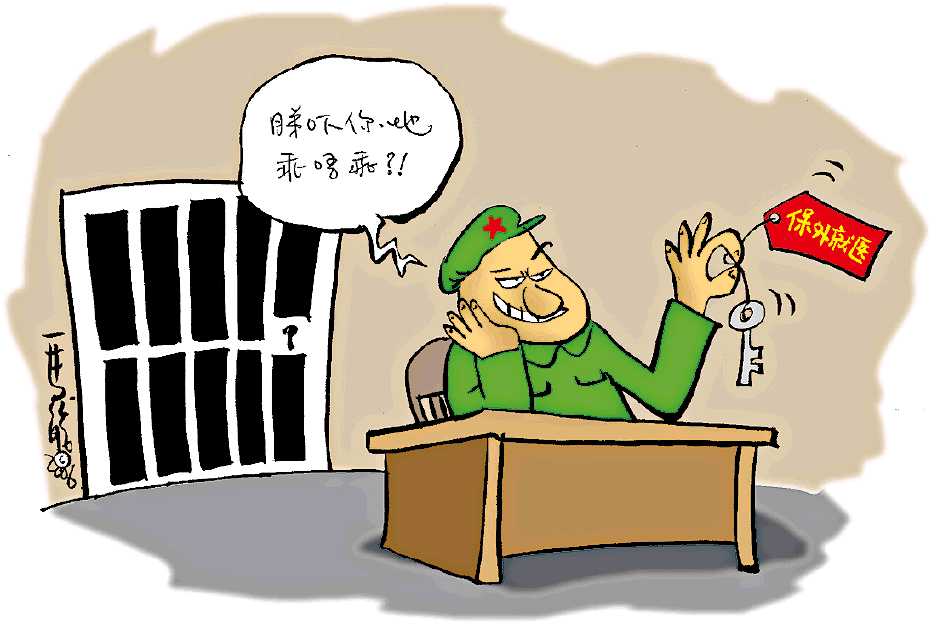
胡麗雲 香港記者協會主席
新加坡《海峽時報》首席中國特派員程翔被北京第二中級人民法院裁定有罪並被判刑五年後,新聞自由的喪鐘隨即敲起,唬嚇了新聞工作者的採訪工作,令日後的採訪更加困難。
自九七回歸,香港與大陸的關係就唇齒相依,政治、經濟以至民生問題都互相緊扣,香港新聞工作者自然愈來愈多赴國內進行採訪,可是,國內法律限制多多,定義不清,艱澀難明,與一般國際慣例要求法律必須清楚、明確的要求,南轅北轍。
以「絕密」、「機密」及「秘密」為例,若洩露會令國家安全和利益受損的消息均屬違法,所不同處,僅在於損害程度:「絕密」的損害要達致特別嚴重;「機密」則是嚴重損害,而「秘密」只是損害而已。可是,何謂「特別嚴重」、「嚴重」?「國家安全及利益」的定義又如何?在模糊不清的法律定義下,如何叫人守法?
法律條文滿布陷阱
早前《紐約時報》北京辦事處的研究員趙岩,便因披露江澤民移交軍委主席的消息,而被起訴洩漏國家機密,其後再加控詐騙罪。雖然,洩漏國家機密罪最終因證據不足,法院宣判罪名不成立;可是,是類高官榮休的新聞,在香港及海外的新聞界尋常不過,但在國內卻被視為「機密」,敢問披露有關消息後,如何對國家的安全及利益造成嚴重的損害?在一個法律條文上滿布陷阱的國度裏工作的新聞工作者,動輒遭扣上因「披露某些消息」而「對國家的安全及利益造成嚴重損害」的帽子,這究竟是新聞工作者的錯?還是建制的錯?
過去年餘,多個團體已促請國內司法部門能以「公平、公正及公開」的原則審理程翔案,可惜,這個已獲國際認同的司法原則卻未獲國內的法院認受,且對《刑事訴訟法》已訂定的訴訟程序,及賦予被告的法律保障,均被各個部門漠視。
拒絕公開審理案件
自程翔被國安局人員扣押,至案件開審,國安局人員利用《刑事訴訟法》中多處地方延長調查期,導致案件歷時年半,方獲法院審理。中國作為《公民權利及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的簽署國,不但未有在本土法例中實踐有關條文,更未有阻止各部門違反公約的規定,即凡逮捕者被捕後,應迅速及在合理時間內交由法院公開審理,且獲得足夠時間及準備,讓法律代表為自己辯護。
法院審理程翔案時,更採用叫人不安的閉門聆訊。雖然,有關案情涉及敏感資料,但是,是否所有案情均被視為國家機密?再者,現時法例對「間諜」及「國家機密」的定義均未見清晰、準確,是否就採用此叫人聯想「黑箱作業」式的審訊方法?
在一個真正講求法治,一個真正擁有司法獨立體制的司法管轄區,公開審訊是必須的,它標誌着法院絕對不會為圖方便,或有意逃避傳媒及公眾監察,而任意將案件審理。
必須拿出真憑實據
香港市民對公開審訊程翔的訴求,相信在上月十五日,藉着他們出席為支持程翔獲得「公平、公正及公開審訊」而舉行的燭光晚會,已經不言而喻。當天晚會由籌備至舉辦,前後不足二十四小時,但已有逾百名香港市民用腳支持。當中,更不乏跟筆者一樣與程翔素昧生平的人士。他們引臂高喊「公平、公正及公開」審理程翔案件的口號。
多名本地及海外學者、宗教界及新聞工作者,早前更就法院裁定程翔案罪名成立,聯署表達不滿及不安的情緒。人民的訴求,難道不值有關方面「青睞」?他們的訴求,跟我們每一名新聞工作者一模一樣:倘若說程翔真的犯事,請拿出真憑實據來吧!請在一個讓大家心服口服的「公平、公正及公開」的審訊程序之下,進行辯證,讓事理愈辯愈明,讓公眾目睹公義如何伸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