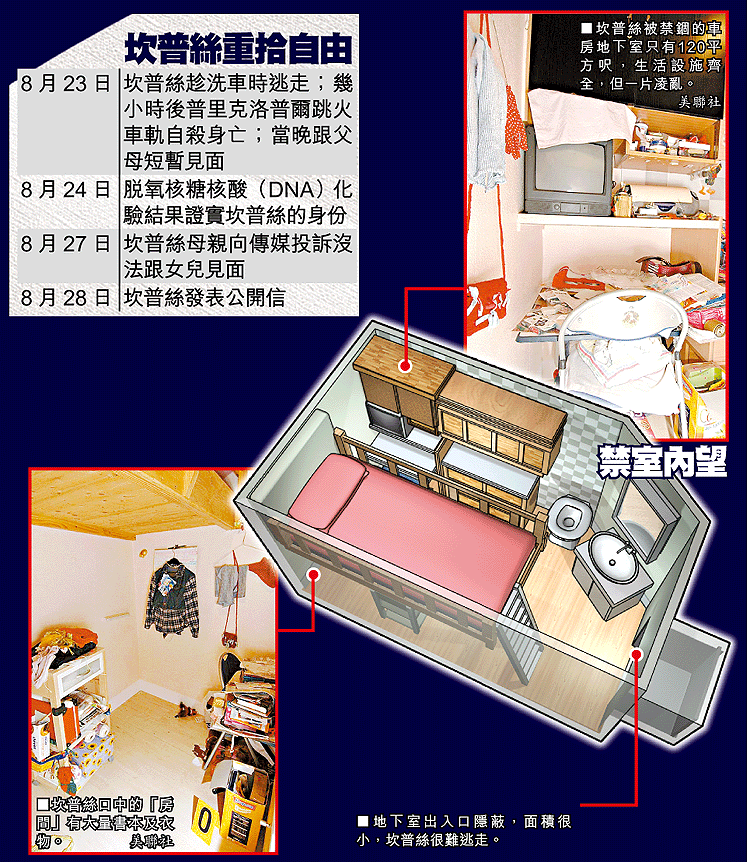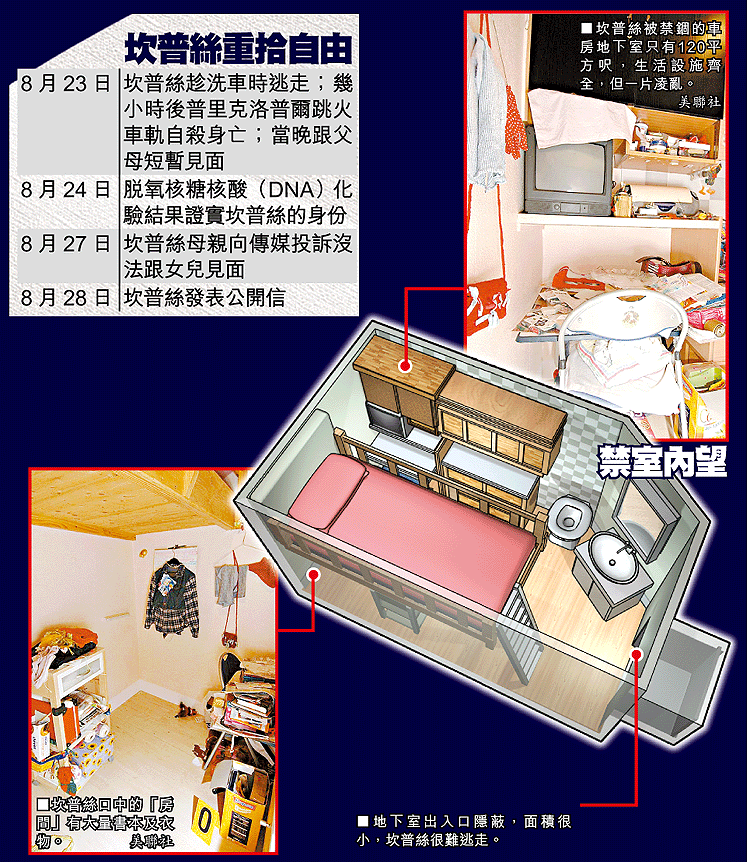
「他是我生命一部份……我為他的死而哀傷。」奧地利「禁室培慾」少女坎普絲(NataschaKampusch)重獲自由後,首次寫公開信,披露她對擄走和禁錮她八年的綁匪普里克洛普爾(WolfgangPriklopil)的情結。公開信沒有責難普里克洛普爾,坎普絲反而說為他的死哀傷,更說他佔「我生命很大部份」,他八年來對自己關懷備至,她更不覺得自己是可憐的受害人。公開信轟動奧地利全國,種種迹象更顯示她產生了「斯德哥爾摩症候群」,對擄走她的綁匪有了感情。
坎普絲現年18歲。她10歲時在維也納上學途中被擄走,警方搜遍全國,都找不到她,她八年來恍似人間蒸發。直至上周三,她在花園抹車,吸塵時他走遠一點,她抓住機會,丟下仍開動的吸塵機逃跑。她逃走後,44歲的普里克洛普爾即日跳火車軌自殺,遭高速駛來的火車輾成肉醬。
同布置房間看「戇豆先生」
坎普絲被禁錮八年,人人都以為她是可憐的受害人。但她在前天由心理醫生代她讀出的「致記者朋友和全球人士」公開信中,首次親自表白,披露了禁錮生活的點滴:普里克洛普爾想她叫自己做「主人」,但她沒有就範;他對她很關懷,兩人更一同布置房間──她被禁錮的車房地下室,有收音機電視機,他還給她看她喜歡的「戇豆先生」影帶。
點點滴滴,長大了的坎普絲要求傳媒尊重她私隱。她不滿自己的「家」的照片被全球傳媒公開,更表明絕不談論她跟普里克洛普爾是否有親密關係。兩人是否上過床,她是否如傳媒揣測懷了普里克洛普爾的身孕,她都不會揭開謎底。
自言不是可憐蟲不是受害人
她只說,她跟普通孩子有不一樣的童年,但她不是可憐蟲,不是受害人。雖然普里克洛普爾八年來會唬嚇她身上有手榴彈,睡覺時也會將手榴彈放在枕頭底,而屋中也滿是炸藥,她若逃走就引爆炸藥同歸於盡,但她仍然強調他是「自己生命的一部份」,指他不必自殺。
坎普絲人質情結很深,當局正盡力幫助她。根據奧國法例,她會獲得664,900歐元(約662萬港元)刑事傷害賠償,她的醫療和心理治療費用亦由政府負責。當局亦計劃安排特別住所,助她重過正常人生活,剛過去的周末更安排她跟年輕人見面。
以下是公開信的摘錄,「我」是坎普絲,「他」就是普里克洛普爾:
「我了解自己被禁錮的事,讓大家感受極深;對於竟然發生這種事,大家一定非常震驚。我也明白大家對我的遭遇感到好奇,想知道更多細節。我在這裏說清楚,我不會回答任何有關性的問題。
我的私人空間:「不應公諸於世」
我的房間有齊我需要的東西。那是我的地方,不應公諸於世。
我的日常生活:「我們會一起吃早餐」
非常規律,多數日子我們會一起吃早餐──他工作不多。我還要做家務、看書、看電視、聊天、做飯。就是這樣,日復日年復年,常常有孤獨的恐懼。
我們的關係:「他不是我的主人」
他不是我的主人。我跟他一樣強,不過,他將我捧上天,有時又把我當成地底泥。但他和我都知道,他選錯對象了。
當年他準備好一切後獨力綁架我。後來我和他一起布置我的房間。
我逃走後沒有哭。我沒有理由要哭。
在我看來,他的死是不必要的。坐牢並非世界末日。他在我生命中佔很重要位置,某程度上我為他哀傷。
我的青春的確跟一般人不同。但基本上我不覺得有所損失。相反,我避開了好些麻煩事,我不吸煙,不喝酒,沒交上壞朋友。
給傳媒的話:「不要對我毫不尊重」
我懇請新聞界不要再作侮辱人、扭曲事實、胡亂猜測的報道,不要對我毫不尊重。
我安於目前逗留的地方,雖然有點受人恩惠之感。我跟家人只用電話聯絡,這是我的決定;幾時接觸記者,也由我決定。
我逃走的經過和之後:「警方太好發問」
當時我在花園抹車,吸塵時他走遠一點,我抓住機會,丟下仍開動的吸塵機。
我想強調一點,我從未叫過他做「主人」,雖然他要我叫,但我相信他不是認真的。
現在我有一位律師和兩位(心理)醫生幫我,我能夠信任他們。警方探員對我很好,但他們太好發問了,那是他們的工作。
性問題:「這完全是我的事」
人人都想問,但那實在跟任何人無關。以後若我覺得有需要,可能會告訴心理醫生或某個人,也可能永遠不說。這完全是我的事。
給他的朋友:「不要內疚」
H先生不要內疚,自殺是沃爾夫岡(普里克洛普爾的名字)的決定。我很同情沃爾夫岡媽媽,對她我感同身受,我明白她。我和她都想他。
我想向所有關心我的人說謝謝。但請讓我清靜一下。請給我時間,直到我可以出來說話。
娜塔莎.坎普絲
英國《泰晤士報》/《太陽報》/天空新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