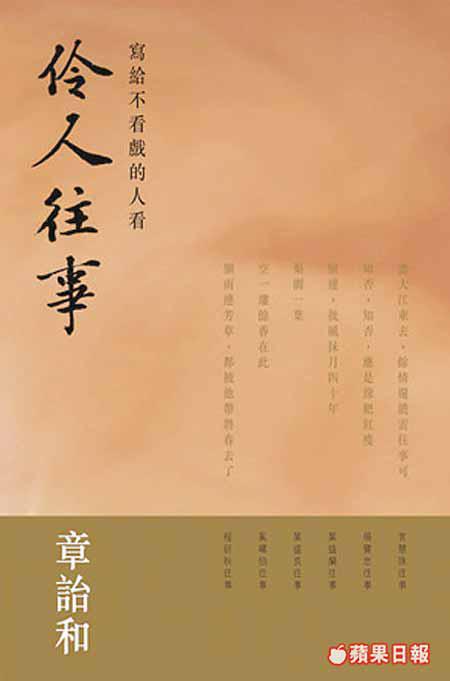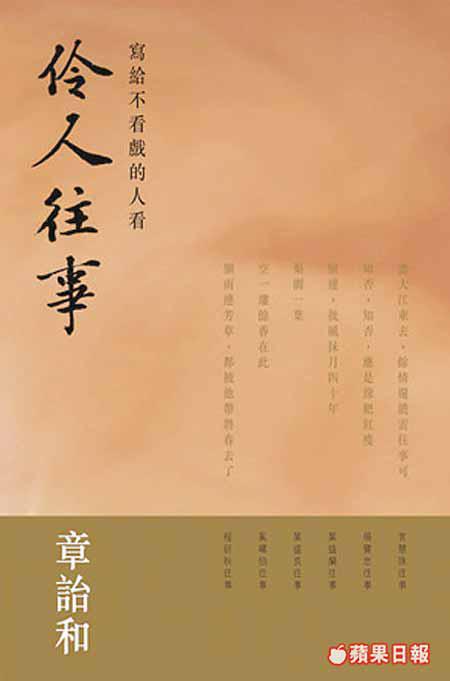
章詒和,章伯鈞的女兒,一九四二年生,安徽桐城(今樅陽)人,現為中國藝術研究院戲曲研究所研究員。著有《最後的貴族》(內地版《往事並不如煙》)、《一陣風,留下了千古絕唱》等,新著《伶人往事》由明報出版社出版。
我第一次聽京戲不是在劇場,是在楊虎家中。這是五十多年前的事了,一天上午,父親對我說:「今天爸爸、媽媽帶你去楊嘯天(楊虎字)家吃飯。」
楊家離我家不遠,也是一座四合院。那天去的客人挺多,主人也高興,拿出齊白石的兩幅新作請大家鑒賞。飯後回到客廳,重新上茶。我端着玻璃茶杯瞧,先前的茶水是綠的,怎麼又換成紅色的了?待客人坐定,楊虎笑瞇瞇地說:「現今小女在學梅派,想獻上一段……」沒等說完,大家就鼓起掌來。
楊虎的小女兒一身布衣,清秀標致:身後是她的琴師,穿着長衫。只見楊家小女兒鞠躬之後,就雙膝跪地。我對媽媽說:「京戲怎麼是跪着唱呢?」母親湊在我耳邊,悄聲道:「她演的是一個在公堂受審的女囚,當然要跪下了。」後來我才知道,這戲名叫《三堂會審》,她扮演的角色叫蘇三。只要是京劇旦角,都會唱這一齣。回到家中,我宣布:自己也要學兩段京戲!可母親告訴我,楊虎的小女兒每次學戲,繼母都坐在旁邊,一刻不離。錯了,就呵斥:再錯,就擰嘴,能擰到出血。於是,我不嚷嚷着「學兩段」了。後來,我從事戲曲文學理論的專業學習,幾乎是天天看戲了。我驚歎伶人的高超和聰穎──居然能用形式感、程式性極強的歌咏、表情、身姿和手勢,道出人類靈魂中的一切深淺不同的歡樂、憂愁、憤恨、哀傷、痛苦和惆悵來。
1957年以後,父母都劃為右派。人情冷暖、世態炎涼一時嘗盡,這時伶人的溫厚謙和,能讓你的內心在瞬間顫慄卻又難以名狀。而受牽連的葉盛蘭、葉盛長、李萬春、奚嘯伯等人在1957年以後的不幸遭遇,更令父母內心充滿自責和歉疚。
再後來,就是在川劇團被管制的日子了。受辱多年,多年受辱的同時也使自己有機會接觸到藝人生活的深處和底部。高貴與卑賤、義氣與世故的融合,萬丈光焰與灰暗慘淡的交替,台上表演與台下做派的錯位,令人驚愕不已。剛剛還精神抖擻地扮演一身正氣、渾身是膽的英雄,下場就鑽進單人化裝間給自己扎「杜冷丁」。「文革」中我被兩個武生強按住,用剪刀在頭上亂剪亂戳,身邊的一個擅長演粉戲老藝人(男旦)死死盯着我,那曾經風情萬種的眼神裏流露出恐懼和憐憫……總之,人間最美的,人性中最醜的,都聚集於此。而且生活形態的東西比藝術作品生動多了,也深刻多了。伶人扮演的角色都是藝術典型,其實最典型不過的就是他們自己。你想忘掉他們,都不可能。去年,我重返四川省川劇團,進門就打聽那個男旦。
答:他早死了。
我問:「死在了哪兒?」
「就死在劇團辦公樓的過道。」頓時,一片寂靜。
「他埋在哪裏呢?」我又問。
答:不知道。
伶人帶着他們的往事是在不知不覺中消失的,只是不知消失於何時何處?真的不知消失於何時何處嗎?
我又想:楊虎的小女兒如果還在,她一定也不再跪唱《玉堂春》。
2006年7月12日於北京守愚齋
《伶人往事──寫給不看戲的人看》自序
我在劇團被管制多年,喪失人身自由的日子也是從劇團開始,可算得嚐遍酸甜苦辣。然而,舞台和藝人始終是吸引我的,這吸引力還很強烈:看了電影《霸王別姬》,自己就想去編個「姬別霸王」;讀了小說《青衣》,也想去學着寫個中篇。連題目都想好了,叫「男旦」。
過去看戲是享受,是歡樂。而這些自以為享受過的歡樂,現已不復存在。如今所有的文化都是消費,一方面是生活走向審美;另一方面是藝術消亡。當然,我們的舞台仍有演出,演新戲,演老戲或老戲新演,但大多是期待而去,失望而歸。中國文化傳統與革新之間的斷裂,在戲曲舞台和藝人命運的身上是看得再清楚不過了。別說是京劇、昆曲,我以為自上個世紀以來,整個文化是愈來愈迷失了方向。數千年積澱而成、且從未受到根本性質疑的中國文明,在後五十年的持續批判與否定中日趨毀損。去年,北京編演了一齣有關梅蘭芳生平的新戲,僅看電視轉播,便驚駭萬狀。去聖已遠,寶變為石。晚清人士面對華夏文明即將崩塌之際,曾發出的「三千年未有之變局」的驚呼,何以如此悲絕?或許正如台灣學者(王德威)所言:「他們已經明白『現代』所帶來的衝擊是如此摧枯拉朽,遠甚於改朝換代的後果。這也間接解釋何以民國肇造,有識之士儘管承認勢之所趨卻難掩一股強烈的失落感覺。他們在民主維新的風潮之後,看到一片龐大的文化、精神廢墟。『憑弔』成為時代的氛圍。」如此看來,京劇《梅蘭芳》的演出也許是成功的,倒是個人的觀劇心理出了問題。
文化上何者為優,何者為劣,早已不堪聞問。在主流意識形態的操控下,誰都難以成為獨立蒼茫的梅蘭芳。從老宅、年畫到京劇、皮影,任何對民間文化藝術的振興、弘揚似乎都是一種憧憬或空談。東西方文化相遇,某些方面可以交融、互補,而某些方面則完全是對立、衝突。幾個回合下來,博大精深的傳統藝術,正以令人炫目的方式走向衰微。其從業者只能在背棄與承續、遺忘與記憶之間尋求折中之策、苟且之法。這大概也算得是文化現代性之兩難的生動顯現。那麼,我們還能做甚麼?還有甚麼可做?恐怕有朝一日,中國舞台真的成了「《長坂坡》裏沒有趙子龍,《空城計》裏沒有諸葛亮。」當然,繼承傳統文化的難題也非中國所獨有。
藝人,是奇特的一群,在創造燦爛的同時,也陷入卑賤。他們的種種表情和眼神都是與時代遭遇的直接反應。時代的潮汐、政治的清濁,將其托起或吞沒。但有一種專屬於他們的姿態與精神,保持並貫通始終。伶人身懷絕技,頭頂星辰,去踐履粉墨一生的意義和使命。春夏秋冬,周而復始。僅此一點,就令人動容。這書是記錄性的,是寫給不看戲的人看,故着墨之處在於人,而非藝。知道的,就寫;知道多點,就多寫點。即所謂「有話則長,無話則短」。正因為奇特,他們也就有可能成為審視二十世紀中國式人生的一個觀察點。書中的敍述與詮釋,一方面是為我的情感所左右,另一方面也是我所接觸材料使然。某種程度的偏見是有的。我喜歡偏見,以抗拒「認同」,可怕的「認同」。
書名就叫《伶人往事》吧。和耀眼的舞台相比,這書不過是一束微光,黯淡幽渺。每晚於燈下憶及藝人舊事,手起筆落間似有餘韻未盡的悵然。它和窗外的夜色一樣,揮之不去。
有人說:你寫的東西,怎麼老是「往事,往事」的?是呀,人老了,腦子裏只剩下「往事」。歷史,故事矣。故事,歷史矣。我們現在講過去的故事,要不了多久,後人也會把我們當作故事來講述。恍然憶及從前逛陶然亭公園的情景。初春的風送來胡琴聲,接着,是一個漢子的歌吟:「終日借酒消愁悶,半世悠悠困風塵……」我聽得耳熱,他唱得悲涼。 2005年11月於北京守愚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