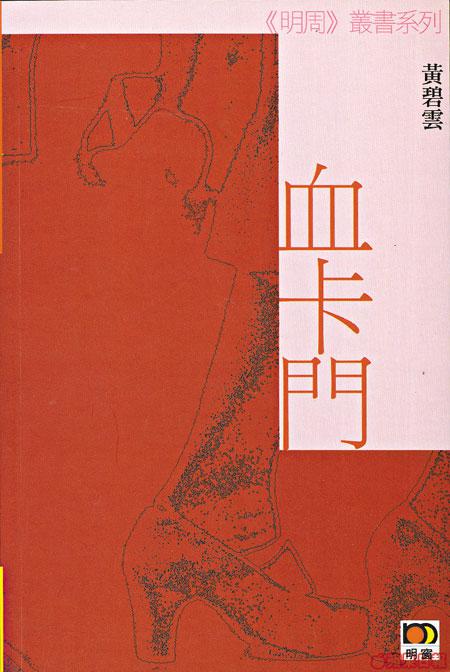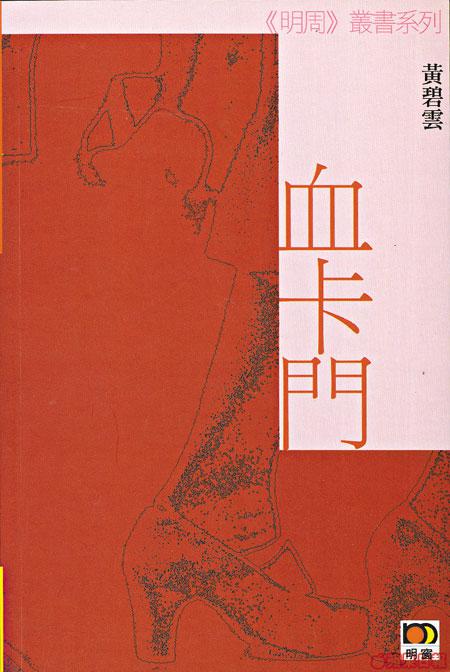
過億元的拉丁舞興訟案,令升斗市民如我感到駭然,本來都源自街頭,經過諸多文化因緣交織,變得階級壁壘分明。學跳拉丁舞就像小朋友學彈鋼琴,學拉小提琴,只是為提高身份,或者令個人的Profile更好看,以便萬一在小一派位結果不如理想,能夠作為擠進名校的武器。
十多年前在電影節上看到CarlosSaura的《卡門》,以Flamenco穿梭於虛幻與真實之間,和熱情豪放,加一點異國情調的神秘,和妙曼的舞姿,那份震撼迄今未散。我不知道黃碧雲是否也有看過這部電影,是否也像我那樣受到這麼大的衝擊,我卻佩服她當年放棄一切,到西班牙學跳舞,並寫出火熱的《血卡門》,讀者看到不只是文字,而是背後那份熱誠,那份執着。但這份執着卻不屬於如今的世代,當王家衞的《春光乍洩》替AstorPiazzolla戴上光環,連我喜歡的前衞小提琴演奏家GidonKremer也玩得不亦樂乎,便明白文化消費已成了臉上的化妝品,粉飾生活的牆紙。拉丁音樂、拉丁舞蹈、拉丁文學黃袍加身,是品味的展示,是身份的象徵,不只是一種文化,而是一盤生意。
也許,甚至不是《談談情,跳跳舞》內役所廣司無聊人生走到半途後才發現的重生意義,而是一口星巴克的咖啡,或一杯紅酒,喝到了悠閒,喝到了優雅。
章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