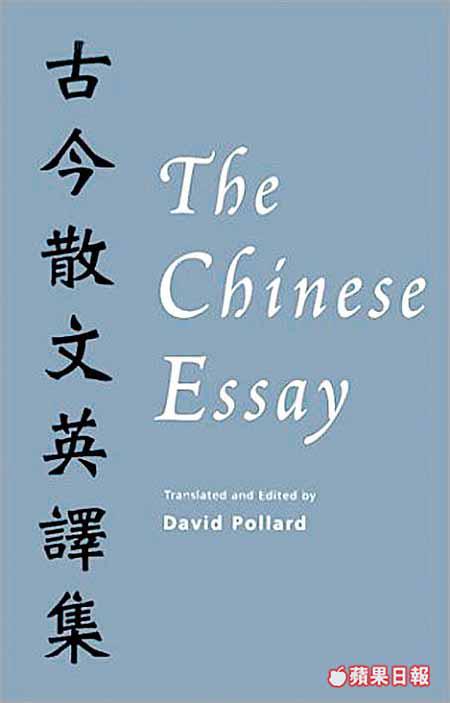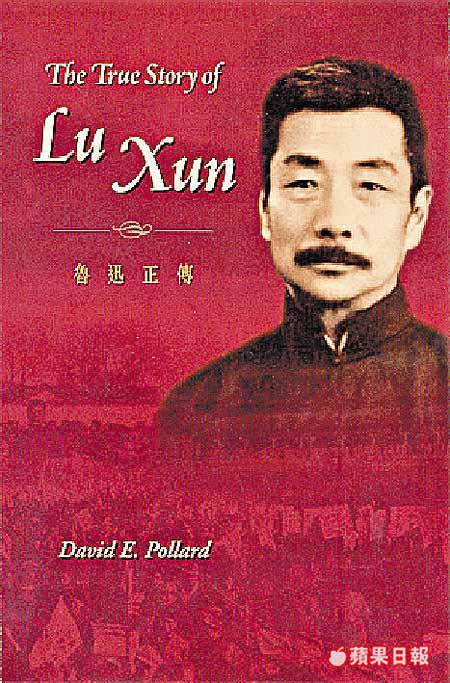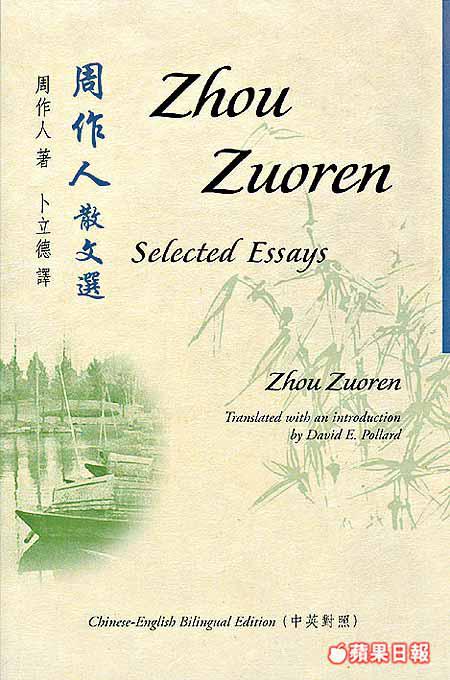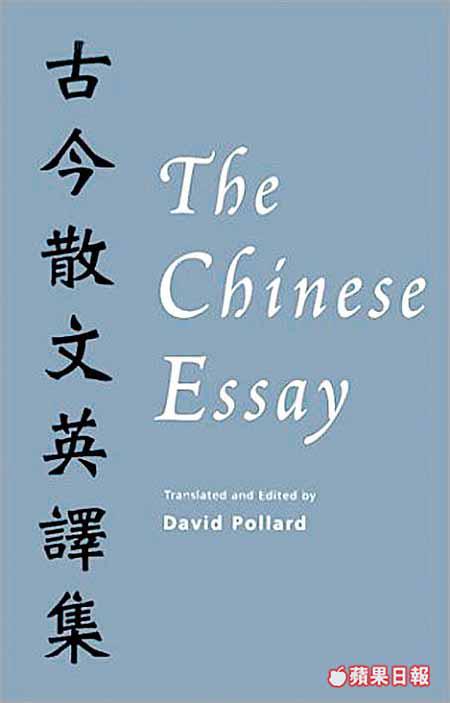
劉紹銘 嶺南大學榮休教授
卜立德(DavidE.Pollard),英國人,倫敦大學哲學博士,曾受業於知名漢學家DenisTwitchett門下。在接任中文大學翻譯系講座教授前,是倫敦大學亞非學院中文講座教授,現已退休,過着隨心所欲的生活。我前後在《蘋果日報》發表過的兩篇文章介紹卜立德的譯作,說他選譯周作人,「因得在同一時間、同一文本中盡顯漢學家、翻譯家和散文家三種不凡身手。」
〈讀翻譯.學英文〉和〈旗鼓相當〉着眼點是翻譯,沒機會涉及他作為文評家的眼光和品味。這裏打算作一補充。卜立德教授在香港結集出版的著述和譯作,我看過的有三本。最早的是TheChineseEssay(《古今散文英譯集》,一九九九)。第二本是TheTrueStoryofLuXun(《魯迅正傳》,二○○二)。最近的一本是剛出版的ZhouZuoren:SelectedEssays(《周作人散文選》)。
《古今散文英譯集》收作家三十六位。在譯文前面都有卜立德寫的小引,可藉此一覽卜立德作為文評家的風貌。現代部份所收的名家,魯迅、周作人、郁達夫、朱自清、梁實秋等人都一一上榜,連產量不多,英年早逝的梁遇春(1906-1932)也上了榜,獨不見一身雲彩的徐志摩。
卜立德給徐志摩的評價是:「他可能是民國年間最florid的一位散文家。他主要的作品是詩,散文偶有精彩的片段,但通篇教人滿意的卻不多見。」因此只好「割愛」。
我沒有把florid翻譯出來,因為這個與花草密不可分的詞兒,在中文一時難有定案。絢麗、嬌艷、華美、矯揉做作,甚至帶脂粉氣都可以說得過去。與florid相對的是familiar,語出英國散文家WilliamHazlitt(1778-1830)。在Hazlitt看來,florid的文體如七寶樓台,堆滿了彩石(pilesofpreciousstones),而familiar的書寫,則平淡自然。
卜立德的集子也沒有收林語堂的作品。他對幽默大師的散文,評價不高。一來因為格調過於西化,二來這類幽默,有時太刻意,反覺淺薄無聊(sillyandfrivolous)。卜立德對林語堂小品的看法,在這方面頗近錢鍾書。默存先生在〈談笑〉一文,不記名的給林語堂上了一課:「自從幽默文學提倡以來,賣笑變成了文人的職業。幽默當然用笑來發洩,但是笑未必表示着幽默。」
我們從卜立德對徐志摩和林語堂的評語捉摸他自己的趣味。除周氏兄弟外,他也鍾情梁實秋。魯迅的作品各家各派的英譯太多了,卜立德因此選了比較冷門的四篇:〈夏三蟲〉、〈男人的進化〉、〈阿金〉和〈在現代中國的孔夫子〉。他這麼給洋讀者介紹魯迅雜文的特色:
魯迅以「冷嘲熱諷」的風格知名。教他鶴立雞群於同輩作家中的原因當然是過人的智慧。但最能顯出他造詣的地方是他遣詞運句的能量。文字在他手上彷如千軍萬馬,任他隨意點撥。時而蓄勢待發。時而看似師老神疲。你以為他按兵不動或撥轉馬頭鳴金收兵了,說時遲、那時快,你已墮入他的天羅地網了。他這種決勝近里的招數,直像從甚麼「兵書」演繹出來。……其實魯迅用之不竭的本錢是他對中國古今文字的掌握,各家各派的「草蛇灰線」讓他一一手到擒來,讓他隨心所欲冷嘲熱諷一番。
卜立德當然看得起知堂老人,否則不會以單行本的篇幅選譯他的作品。收在《周作人散文選》的作品有二十九篇,包括論者常引用的〈苦雨〉、〈蒼蠅〉、〈入廁讀書〉、〈談過癩〉和〈自己的文章〉。書內長長的〈導論〉由葉志研譯出。我引用他的譯文:
周作人作為散文家,並不以風格技巧見長,僅依賴反語、故作輕描淡寫、佯作無知等手法修辭。他的白話文不算十分流暢,時而流於單調,時而文白混雜,但他的表達方式自成一格,讀起來便覺得他真誠、可靠。表面上周作人似乎很冬烘、枯燥,骨子裏卻隨時準備搗鬼,看準機會叫人人仰馬翻。他稱道人的說話中,「有趣」是其一,亦即是具有詼諧、好玩、出人意表的特質。正是這些特質,令周作人的散文和小品文充滿生氣,也令筆者艱難的翻譯過程變得──有趣。
依賴反語、故作輕描淡寫、佯裝無知等手法修辭,這種文風,類同乃兄。看來兄弟二人用的是同一「兵書」。也就是說,他們的文字能登上善境,是讀通了古今中外的好書和壞書。周作人散文的特色,卜立德在《古今散文英譯集》的引言中作了補充。他認為知堂老人文字與別不同的地方,是因為他巧妙地把兩種看來水火不相容的性情混為一體:thetensionbetweenrebelandrecluse,betweengentlemanandruffian。因此叛徒與隱士、君子與流氓,在他筆下相濡以沫,成為另一品種。
因為「政見」不同,魯迅與梁實秋兩派文字也勢成水火。梁實秋受的英美教育,讓他一直堅守立場:文學不是為人民服務的工具。抗日期間他主編《中央日報》副刊,採用的來稿中除了應時文章外,還有不少閒話家常的小品與雜文。卜立德以文史家的眼光篩選文章,只問作品好壞,不為政治取向左右,因此可以不分彼此的去衡量魯迅、周作人和梁實秋三家的成就。
「一個作家如果挖空心思的在日常生活中強求幽默」,卜立德說:「文章馬上失去誠真,變得無聊淺薄(silly)。梁實秋很少在這方面失過手,因為一看到自己身陷險境,他每能用幾句『花言巧語』(agoodturnofphrase)解圍。他最愛用的幽默策略是把我們不大願意承認的『沉潛意識』(sneakingfeelings)公開地抖出來。」
卜立德以〈狗〉為例。雅舍主人說「君子有三畏」,猘犬其一也。窩居重慶時,房東養了隻腦滿腸肥的狗。每次進門,房客實秋先生跟守門的因語言不通,總有點磨擦。且戰且退時,看到主人出來,以為他會念在同類仗義施予援手。誰料主人竟跟惡犬站在同一陣線,不作舉手之勞,只看着他的「狼狽而閧然噱笑,泛起一種得意之色,面帶着笑容對狗嗔罵幾聲:『小花!你昏了?連X先生你都不識認了!』」
卜立德認為此文最可圈可點的是道出了主人的「沉潛意識」:儘管他對客人連聲抱歉,私底下卻引他的狗狗為傲。可不是嗎?嚇得雅舍主人差點要撒尿(scaresthepantsoff),這條狗真是克盡厥職。因此,主人「表面上儘管對客人抱歉,內心裏是有一種愉快,覺得我的這隻狗並非是掛名差事。」
除了諧趣自然的一面外,卜立德推崇雅舍散文,還有一個原因。梁實秋活躍時期的二三十年代,中文語態,深受英文影響。試抄徐志摩〈翡冷翠山居閒話〉開頭的一句:
在這裏出門散步去,上山或下山,在一個晴好的五月的向晚,正像是去赴一個美的宴會,比如去一果子園,那邊每株樹上都是滿掛着詩情最透逸的果實,假如你單是站着看還滿意時,只要你一伸手就可以採取,可以恣嚐鮮味,足夠你性靈的迷醉。
年壽有時而盡。我們讀完這句子時,頭髮已經白了。句子短些的英式文字,讀來沒有這麼吃力,但也要「入鄉隨俗」,邊讀邊譯成英文。徐訏的小說〈賭窟裏的花魂〉是這麼開頭:「菜室裏非常零落,許多位子空着。但是我竟未佔一個空桌,無意識的被一條冷颼颼的視線吸去,坐在那視線的對面。」
梁實秋是莎士比亞全集的譯者,出過洋,一生不離歐風美雨的薰陶,落筆為文時,卻能毫不吃力的躲過了「荒謬的英法海峽」的誘惑,寫出卜立德認為是「道地」(authentic)的中文來。
難得的是卜立德有「愛」無類,他對張愛玲的才華亦推崇備至。「張愛玲並不是立志成為散文家的」,卜立德說:「她寫隨筆雜文,只為了稿費。也為了自娛。她的文章看來寫得並不用心,段落之間似有遺漏,但絕不淺薄。像她這麼一個冰雪聰明而又獨具慧眼的作家,不會寫出淺薄的文章。如果她的觀點常教人眼前一亮,理由倒簡單:她不欠誰的情,也不讓你覺得你欠她的情。她才不管她該說甚麼話(這是她同胞解不開的一個死結),或該拍誰的馬屁。她一向是本姑娘愛說甚麼就說甚麼。謝天謝地,她並沒有因此變為憤世嫉俗。她只是老實得可愛。張愛玲最值得高興的,該是有幸既不生為男兒身,也不是知識分子。男人──最少在她那時代的男人──總認定自己有角色要扮演。知識分子呢,懍懍然覺得自己有立場要捍衞。張愛玲那時輕輕的年紀,看事物不帶偏見,因此可以看到本來的面目。」
卜立德選譯的兩篇作品是〈中國人的宗教〉和〈打人〉。其實,要突顯「本姑娘愛說甚麼就說甚麼」的本色,倒可以〈詩與胡說〉為例。你看這是甚麼話:「聽說顧明道死了,我非常高興,理由很簡單,因為他的小說寫得不好。」
張愛玲並不認識顧明道。他死了她覺得非常高興,因為她再不用看他的《明日天涯》這類連載小說了。裏面一位前進青年,資助一個求學的小姑娘,每次到她家裏去,小姑娘的媽媽總要大魚大肉的請他吃飯表示謝意,「添菜的費用超過學費不知多少倍。」
小說寫得這麼糟,難怪作者去世,「本姑娘」並不傷心。此文成後,覺得若要把題目譯成英文,或可說是ThusSpakeDavidE.Pollard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