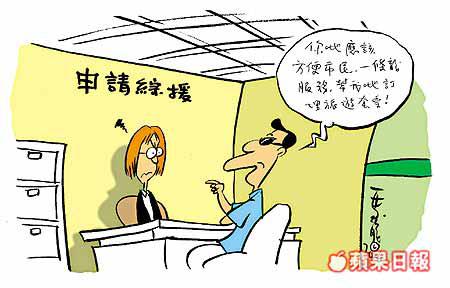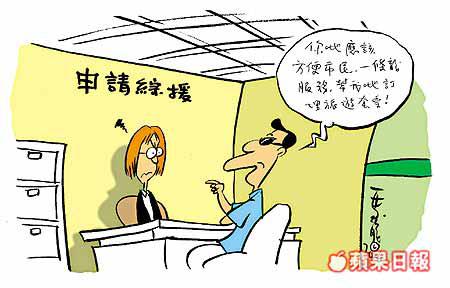
在台灣的報紙上讀到有人提及大陸一位年輕學者的文章,筆者在網頁搜尋中找到,看了之後整晚都睡不着。它真的是有如提及此文的人所說,「句句如刀」,解開了筆者幾十年來思想中的一個困惑。
作者名叫王怡,與我同名不同姓。年紀很輕,今年才三十三歲。文章是將近兩年前寫的,題目是《我成為民族主義的那天》。
文章很長,先從作者自稱不是民族主義者說起。為甚麼不是民族主義者?他說美國轟炸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那個午後,他無動於衷,因為他認為美國只是在轟炸北京政府,而不是轟炸中國,也不是轟炸中國人民,「我對死難者個人的同情,沒有理由昇華到某種能夠把死者與我捆綁於一個世俗共同體的偉大感情中去」。他說他是「徹底的個人主義者」,「一個個人主義的中國人如果得到一個機會,能在英屬殖民地的香港和毛澤東的紅色中國之間挑選,個人主義者將毫無疑問地選擇高鼻子的英國人統治,也不願被和他膚色一樣的共產黨人蹂躪。」文章到此為止,可以說與筆者多年來為文提及應擺脫民族主義情意結的想法,並無二致。
接下來作者告訴我們一個故事,是一個以反抗共產主義著稱的波蘭思想家米奇尼克的事。米奇尼克說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一日這一天,蘇軍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摧毀「布拉格之春」。蘇聯為了尋求出兵的「正當性」,也糾集了波蘭在內的五個東歐共產國家一起出兵。米奇尼克說,這一天就是他成為波蘭民族主義者的紀念日。「在一九六八年的波蘭,甚麼人才配叫做波蘭人?在民主國家,民族國家的身份認同不但和文化與血統,而且和民主政體、和一部捍衞人權的憲法密切相關。但在一個極權主義國家,一個普通人對民族國家的身份認同從哪裏來?米奇尼克給出一個迄今為止最令我動心的理由,他說,『為波蘭的罪過感到羞恥的人,就是波蘭人。』」
王怡說,「一個人的民族國家身份,取決於這個人是否為國家的罪行感到羞愧。這是一種低調但更加堅決的民族主義立場。民族主義不需要激情,也不需要調情。不需要義勇和虛驕的自負。民族主義歸根到底,需要的只是一種羞恥心。……分擔羞恥比分擔榮譽更讓一個人牢牢記起自己的群體身份,尤其是在一個極權主義國家,或在一個臭名昭著的家族、政黨和組織裏,經常性的分擔羞恥幾乎是其成員的一種命運。」
王怡把笛卡兒的「我思故我在」,改為「我羞故我在」。他寫這篇文章的這一天,是蔣彥永醫生因提出要求平反六四而被無理羈押第四十天的日子。這一天使王怡感到無比羞恥,於是也就使他不能不認同中國,使他成為了一個民族主義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