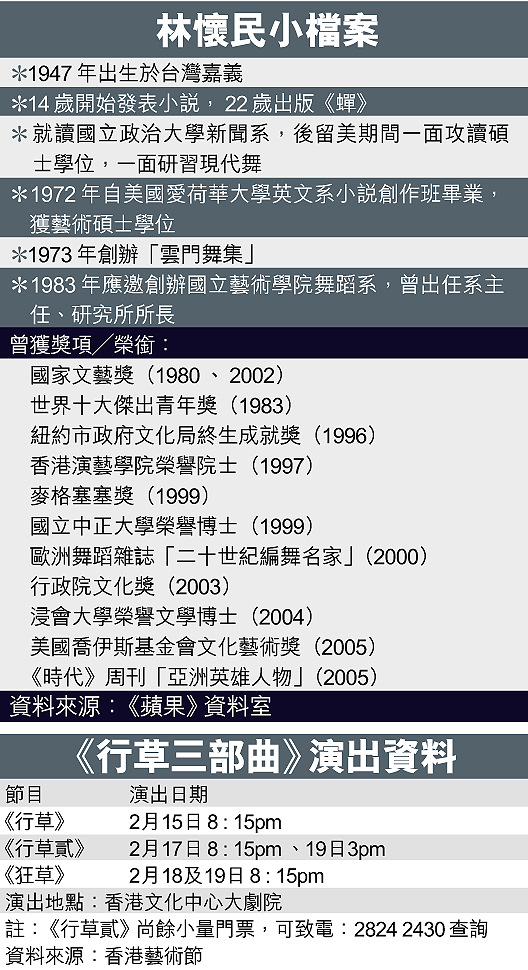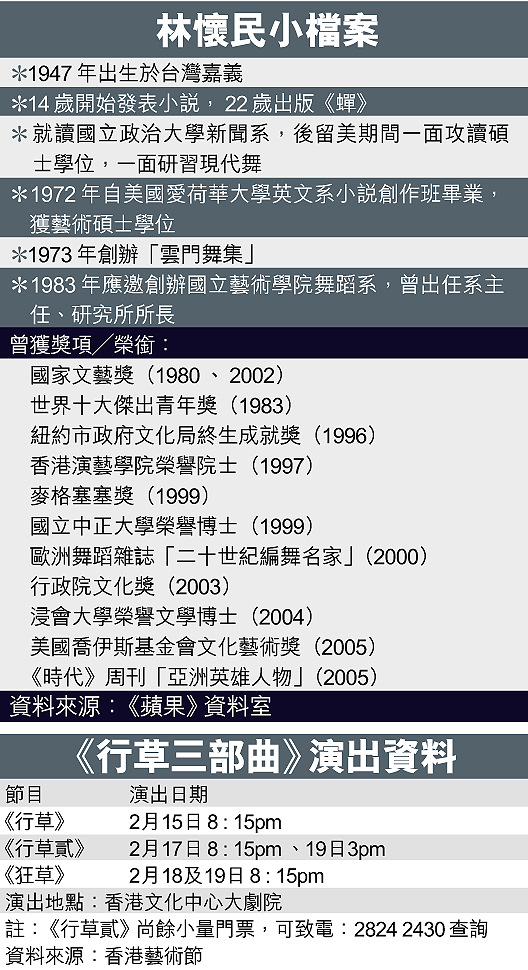
【本報訊】獲《時代》周刊選為「亞洲英雄」的著名台灣編舞家林懷民帶着他的雲門舞集來了香港,為《行草三部曲》今晚起的全球首演作準備。舞迷引頸以待的三齣力作,是今年香港藝術節的重頭節目之一,其中《行草》和壓卷的《狂草》,門票早已賣光。 記者:陳沛敏
由○一年的《行草》、○三年的《行草貳》,到最新的《狂草》,都是以書法美學貫穿其中。但林懷民說:「書法只是一個藉口,我是舞者的鏡子。」雲門的舞者九十年代開始要習氣功、打坐,二千年開始還要每星期上書法課。「看他們的能力到了哪裏,就做甚麼。」結果是《行草》之後,他欲罷不能,因發現書法美學取之不盡,舞者身體開發也無窮無盡。
曾恨死寫書法
快將六十歲的林懷民,說起成長年代的書法經驗,形容是「痛苦的磨難」。因日治時代講求修身而寫得一手好字的母親,總是督促他練字。那時物資缺乏,母親給他用報紙釘成習字簿,無論暑假寒假,天天都要寫滿十頁紙,才能放下筆墨,那時候,「我恨死寫書法」。
長大後,林懷民卻「覺得書法很美」,經常到台北故宮博物院看書帖看得入迷。「每個字後面都有一個故事,還有書法家的情感跟體溫。」王羲之的《奉橘帖》、蘇東坡的《寒食帖》,盛載了作者那時的情懷和故事,還有張旭的《肚痛帖》,節奏美妙得「像首交響樂」。但他提醒《行草三部曲》的觀眾,應以輕鬆心情入場,「把書法知識放在門口,不要對號入座」。
港有精英觀眾
來香港演出不下十多次的林懷民說,香港的雲門觀眾跟台灣的有一個共通點,就是「平時不來看現代舞的人都來,有很老的先生,很年輕的學生。」但同時「香港另外有一種非常精英的觀眾,台灣還未有培養出來。」過去二十多年藝術節和不同的演出把世界不同的東西都帶來香港,因此他們看過「全中國最好的東西」,但他們也可以很snobbish(自負),「對不喜歡的東西,尖酸惡毒香港人也是一流的」。